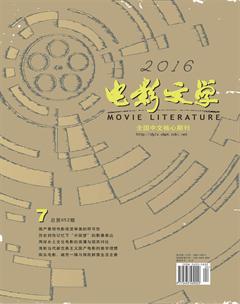非裔美國文學在電影中的審美重構
馬海艷
[摘 要] 非裔文學在美國文學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內在的藝術價值早已得到了電影人的肯定。但是文學與電影之間的差異、時代之間的差異等,勢必導致非裔美國文學在搬上大銀幕時會被進行審美重構,原作品之中的元素、風格乃至立意等組成部分都有可能被調整,從而使它們能更容易地為當代觀眾所接受。文章從審美感官上的置換重構,角色定位上的變異重構,社會意義上的轉化、深化重構三方面,分析非裔美國文學在電影中的審美重構。
[關鍵詞] 美國文學;非裔;電影;審美重構
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1]這一論斷在審美領域也是成立的。人們內心始終有著對超越的渴望,在藝術活動中也并不例外。文學具有比電影藝術更為悠久的歷史,當電影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時,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創造活動,在這一活動中,人們會根據新的語境和社會氛圍,對原作品進行審美上的超越。非裔文學在美國文學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盡管其崛起時間不長,但其內在的藝術價值早已得到了電影人的肯定。黑人作家如托妮·莫里森、格蘭·漢斯貝利等人從黑人權益、黑人苦難史的角度出發,對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處境進行了拷問與期盼。兩百多年來,黑人在美國的境遇變遷本身就擁有足夠的戲劇沖突,不僅可以給予人社會學方面的思考,同時也能在審美上給予人們精神上的滿足。但是文學與電影之間的差異、時代之間的差異以及創作者對審美超越的追求等勢必導致非裔美國文學在搬上大銀幕時會被進行審美重構(Aesthetic Reconstruction),原作品之中的元素、風格乃至立意等組成部分都有可能被調整,從而使它們能更容易地為當代觀眾所接受。
一、審美感官上的置換重構
電影與文學之間本身存在相當大的區別,這也直接導致了接受者在審美過程中對感官的啟用程度是不一樣的,甚至如英格瑪·博格曼等人直接認為電影與文學無關。[2]因為當電影以將不斷播放的畫面連綴起來這種方式作用于觀眾的感官時,這些畫面就已經凌駕于觀眾的理解之上了。換言之,觀眾在接受電影時所需要的思考要遠遠低于閱讀小說。
電影應該被視作一種視覺媒介,當電影進入到有聲電影時代之后,觀眾就可以從視覺與聽覺兩方面來對電影進行欣賞,同時臺詞、旁白等依然保留了語言文字的表意功能,可以說,電影徹底改變了文學對審美感官的刺激方式。在電影的任何一幀畫面中,它能傳遞出來的信息量都是龐大且復雜,甚至帶有互文性的,觀眾不光可以看到演員的面部表情和形體表演,可以欣賞到導演對道具、服飾、布景的選擇以及在場面調度上的能力,僅就語言文字而言,演員對于臺詞在聲調、語氣上的處理也是文學難以提供的,這正是德勒茲所提出的是電影造就了“聲音的對話”。對于非裔美國文學的電影改編來說也不例外。導演需要從語言文字中尋找出最適合畫面表示的角度,將作者想提供的情境多層次地、完整地表現給觀眾,尤其是托妮·莫里森、愛麗絲·沃克以及佐拉·尼爾·赫斯頓等在美國文壇具有一定地位的黑人作家,她們在寫作中并不僅僅試圖使用文字來喚醒同胞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是在文字中表達了她們對黑人的性別體驗、生存模式以及文化存續問題的深刻思考,以至于她們的語言往往帶有含蓄蘊藉的特征,這更給予了電影導演審美重構的余地。
例如,在根據赫斯頓同名小說改編的,由達內爾·馬丁執導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原著一般譯為“他們眼望上蒼”,2005)中,原著并沒有提及主人公簡妮·克勞福德等人各個時期衣著的具體情況,但是導演有意識地在視覺上將男性與女性進行了區分,從而強調了原著的性別主義立意。電影中的男性一般都身穿深色衣服,而女性(尤其是地位較低的女性)則穿白色裙子等。在電影的最后,當簡妮失去了最后的愛人迪凱克后,她跑過一片麥田,躺在水塘之中,半空之中仿佛傳來迪凱克問她在干什么的聲音,她回答“我在看上帝”。這一段電影畫面拍得極為唯美,簡妮身處的水塘風景宜人,岸邊綠樹成蔭,導演使用俯拍鏡頭,天空的流云映在簡妮的臉上,簡妮在陽光之下感到無比的放松。觀眾可以很直觀地感受到,簡妮獲得了徹底的自由,盡管她失去了理性的婚姻,但是她已經蛻變為一位成熟的女性,覺醒而獨立,在這融入自然、眼望上帝的一剎那她感到無比愜意。單純閱讀小說的文本并不能獲得如此直接的感受。
二、角色定位上的變異重構
人物角色是構成小說和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和電影的情節都需要人物來進行帶動、串聯,文本的戲劇沖突也必然依靠人物來展開,因此,人物角色被認為是故事的核心和靈魂是毫不夸大的。然而,小說與電影在形式上的差異勢必會影響到后者在內容上的重構。在電影中,由于時間有限,出場角色一旦太多就會讓觀眾無從記憶和分辨,影響觀眾對電影內容的理解。一般而言,成功的審美重構并不會對原有角色進行顛覆性的修改,一切仍然要服務于電影精神的傳達。
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5)。這部電影改編自愛麗絲·沃克曾經獲得普利策獎的同名小說,盡管這是斯皮爾伯格在嘗試了驚險、科幻等類型片后第一次對溫情藝術片的嘗試,但它已經體現出了后來人們熟悉的中規中矩的“斯氏電影”敘事方式,電影觸動著人們的心靈。必須指出的是,沃克的原著采用的是書信體的敘事方式,沃克使用數十封信給人們展現了女主人公西麗的人生,以一種接近心理小說的方式闡述了她提倡的“婦女主義”。斯皮爾伯格在繼承沃克婦女主義的精神時,對角色的定位進行了一些調整。在原著中存在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婦女主義者,那便是莎格。莎格是一個崇尚自由的布魯斯流浪歌手,通過唱歌獲得經濟上的獨立,但同時她也是西麗丈夫阿爾伯特的情婦,她與西麗之間本來應是敵人的關系。然而莎格卻以她大膽、樂觀、獨立的人生觀影響、幫助著西麗,兩人最終發展成為一對密友。莎格對西麗的愛,對她自己的愛,包括她對黑人文化布魯斯音樂的愛,都是沃克對婦女主義的定義中的。
在原著中,莎格的形象通過西麗對莎格的觀察建立起來,莎格是一個簡單的、人格完善的理想型角色,是作者賦予黑人女性進行反抗的一個榜樣。[3]然而斯皮爾伯格卻對這一角色進行了豐富。在電影中,莎格與自己的父親之間有著某種心結,原本看起來無牽無掛的莎格卻從小依戀著自己的父親,渴望被作為牧師,代表著某種神性權威與道德力量的父親認同。然而莎格在長大之后卻成為一個自由不羈的歌手,還做了別人的情婦,這顯然不是她的父親所能接受的。為了突出這種矛盾沖突,電影中有意安排了莎格在酒吧中給西麗獻上一首歌后馬上切換了莎格父親在教堂中嚴肅地布道的畫面。這一設定并不是毫無來由的,斯皮爾伯格安排莎格在進入夜總會唱歌之前在父親工作的教堂中的唱詩班長期唱歌,因此鍛煉出了良好的音樂素養。由此,莎格的形象顯得更為有血有肉了。她成為擺脫了男權規范束縛,大膽地享受自己生活的新一代黑人女性,但是這種角色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她同樣有她自己的痛苦。并且莎格將自己的心結告訴西麗,這進一步增強了觀眾對兩人感情親密度的理解。而在影片的最后,莎格與自己的父親達成了和解,這可以視作作為白人的斯皮爾伯格對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之間相互理解、和諧共處的一種美好意愿。盡管有人認為,這是斯皮爾伯格為了使電影能夠順利上映而對主流道德價值觀做出的妥協,但這并不影響沃克婦女主義本意的表達,也沒有削弱莎格這一形象的光彩。
三、社會意義上的轉化、深化重構
人類社會在不斷地發展,人類對于審美對象的態度也在不斷地變化,人們的審美意識與電影在表現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之間的關系是日益交錯糾纏的,故而電影在對文學進行改編時,其反映的社會意義也是處于一個變動狀態之中的。根據非裔美國文學改編的電影對于社會的結合程度尤其緊密,非裔美國文學本身就是以具體的社會事件、社會困境為基礎的,黑人多年來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早已引起了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關注,甚至一度間接導致了幾乎使美國分裂的南北戰爭。因此,美國早期的非裔文學更多的有一種捍衛膚色榮譽的態度,作家們大力強調的是對平等的爭取,而后期隨著奴隸制被廢除,美國對種族主義的警惕,黑人的地位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后期的非裔文學則更傾向于對經過歲月汰洗之后所剩無多的民族傳統文化之根的追尋。由此可見,非裔文學本身對社會意義的開掘方向也是流動的,這也就不難理解在此基礎上改編的電影會在這一方面進行微妙的重構或置換。
以改編自所羅門·瑟普自傳的《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2013)為例,如果對這部電影的解讀仍然停留在膚色之爭上,僅僅看到導演史蒂夫·麥奎因對于本種族人民的同情,那么對其審美價值的理解依然是不夠的。只要對麥奎因的電影,如《饑餓》《羞恥》等稍作了解便不難發現,麥奎因所擅長的便是借助某一情境,將人置于一種苦難、絕望的境地之中,最終實現對人類行為與社會制度、人性弱點之間復雜關系的討論。從這一點來說,《為奴十二年》之中的奴隸制背景也僅僅是麥奎因借用的敘事外殼。只是原著中關于黑人男性被欺騙,女性被強奸,黑人奴隸們不得不為白人莊園主們當牛做馬,還要時常受到鞭刑等折磨的表現在電影中都得到了一一還原,以至于觀眾的注意力很難不被電影中的種族主義主題所吸引,而忘記了麥奎因在對社會問題思考上的開掘。
在電影中,當主人公所羅門淪為奴隸,被號稱“奴隸終結者”的殘暴無比的奴隸主肆意毆打并吊起來加以折磨時,身邊的其他黑人奴隸視若平常,即使在奴隸主走之后也無人出來解救所羅門,所羅門依靠著腳尖在地上一點點著力而努力掙扎,唯一給予他幫助的一位黑人女奴做的是給了他一點水喝并去幫他喊人。麥奎因有意在這里使用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長鏡頭,通過一種減慢電影節奏的方式,將“十二年”的殘酷以及所羅門身體、精神上受到的巨大折磨展示出來。而這種冷漠是會傳染的,當所羅門獲得自由之后,他所做的也只是默默離去,而他的同胞們依然要留在這種極端狀態之中。電影中的黑人女奴在所羅門走后昏倒在地就是這種絕望的體現。電影實際上并不僅僅展現了白人奴隸主的獸性,黑人也是導演提醒觀眾反思的對象。在原著中,被奴隸主吊打,其他黑奴置若罔聞一事固然會提及,但是其在書中的地位卻不會像麥奎因那樣專門使用3分鐘的長鏡頭凸顯出來。這實際上便是身處21世紀的導演(包括觀眾)與生活在19世紀的主人公的區別所在。原著的社會意義在于通過自身的經歷來控訴血淚斑斑的奴隸制度,而電影則試圖傳達出來的是,第一,奴隸制度的根源離不開被害者自身的奴性;第二,人生似乎可以視作一座巨大的牢籠,人與人之間骯臟、殘酷且虛偽,互相傷害。
法國著名批評家艾·菲茲利埃在總結文學與電影之間的關系時指出的就是一切都可以歸結為“電影為文學帶來了什么,文學又為電影帶來了什么”[4]。從對非裔美國文學的電影改編中不難看出,文學在為電影帶來信息、經驗以及思維的同時,電影又為文學帶來了審美重構的空間。就形式而言,電影改變了文學作為傳統印刷媒介對接受者審美感官的刺激方式,在實際操作之中豐富著原著的審美層次;就內容而言,電影往往會在人物角色的設置上進行濃縮、變異,在對社會問題的挖掘程度上做進一步的深化等,這些都能給予觀眾美的享受,甚至提升原著的境界。文學與電影之間不必強分高下,但是電影能以一種傳播上的強勢力量對文學進行審美重構卻是毋庸置疑的。
[參考文獻]
[1]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2] 莫·貝哈,齊頌,桑重.電影與文學[J].世界電影,1989(06).
[3] 王成宇.《紫色》與艾麗絲·沃克的非洲中心主義[J].外國文學研究,2001(04).
[4] 孫晶.跨越文字與影像的疆界[D].長春:吉林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