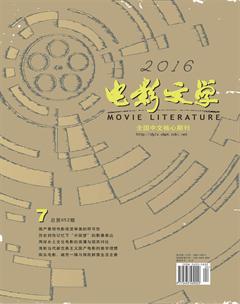從《狼圖騰》看國產(chǎn)影片的跨文化特質(zhì)
褚靜
[摘 要] 電影《狼圖騰》的出現(xiàn)對于中國電影的未來創(chuàng)作無疑是個啟示,該片改編自姜戎的同名小說,在改編和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開辟了全新的敘事角度與價值高度。電影的成功改寫為當(dāng)今的國產(chǎn)電影樹起了一面全新的旗幟,引領(lǐng)了跨文化創(chuàng)作的新潮流。本文將對《狼圖騰》這部影片進行多維度的分析,探討影片創(chuàng)作中表露出的跨文化特質(zhì),并給予這部“新”電影一種新的命名——“跨主體—地域間性”中文電影。
[關(guān)鍵詞] 跨文化特質(zhì);價值觀;范式電影
對于《狼圖騰》這部電影所衍散出來的種種意義及啟示,用時下最便捷也最流行的說法就是,如果我們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進行探索,能夠更清晰地看清其全部要義,而其中首要的便是它跨文化的性質(zhì)。
一、從小說到電影
電影《狼圖騰》以其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的精湛獲得很多好評,但是如果就敘事結(jié)構(gòu)和人物塑造來看,該片在以下四個方面存在著不完美之處。第一,人物形象的刻畫太過臉譜化,沒有立體感。在影片中,主人公陳陣以及與他同行的楊克,還有草原上的許多角色形象,這些人物塑造都過于扁平,性格過于單一,而且從始至終沒有發(fā)生變化,沒有好萊塢影片中角色塑造的豐滿感;第二,影片對于陳陣對狼的情愫交代得并不明確,陳陣為什么關(guān)注狼的生存,又為什么一定要收養(yǎng)一頭小狼,影片沒有交代清楚,讓觀眾以為陳陣只是因為對小狼的好奇才會產(chǎn)生悲憫和保護欲,削弱了影片的立意和深度;第三,有關(guān)陳陣和嘎斯邁的感情線發(fā)展鋪墊得不夠,以至于后期陳陣對嘎斯邁示愛時,觀眾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第四,整個故事發(fā)生在“文革”時期,這一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期沒有被影片表現(xiàn)出來,使得整部影片厚度不夠,顯得有些單薄。
但這些問題不應(yīng)該都?xì)w咎于導(dǎo)演讓·雅克·阿諾,因為我們回看他的其他作品,不乏在人物塑造上獲得一致好評的佳作,例如阿諾曾執(zhí)導(dǎo)的電影《兵臨城下》。因此,該片會出現(xiàn)以上問題,并非導(dǎo)演乃至主創(chuàng)團隊的藝術(shù)功力不夠,而是有其他原因。雖然該片在敘事結(jié)構(gòu)和人物塑造上存在某些缺點,但是依然得到了觀眾的認(rèn)可,成為名噪一時的佳作。我們不禁要發(fā)問,為什么一部存在問題的影片依然能夠成功?這其中必然有其內(nèi)在的原因。
電影改編自姜戎的同名小說《狼圖騰》,小說一經(jīng)上架便獲得一致好評,成為當(dāng)之無愧的暢銷書。在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過程中,導(dǎo)演阿諾及影片的主創(chuàng)團隊尊重原著的故事主線和敘事方式,沒有對原著進行大尺度的調(diào)整和改編,原著的基礎(chǔ)架構(gòu)和作品精髓都成功地留存下來。但這并不意味著阿諾完全按照原作去處理所有的細(xì)節(jié),縱觀阿諾對原作的改編和再創(chuàng)作,我們可以看出阿諾的改動不僅很恰當(dāng),而且能夠體現(xiàn)出影片創(chuàng)作的跨文化特質(zhì)。
姜戎的原作是一部故事進展十分緩慢的小說,因為小說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只講故事的小說,而是一部摻雜了許多議論和批判的作品。阿諾在電影改編的過程中,拉緊了影片的故事線,使得敘事脈絡(luò)更加清晰、情節(jié)更加跌宕起伏、矛盾沖突更加集中和緊湊。同時在阿諾的調(diào)整之下,小說體現(xiàn)的文化內(nèi)涵和價值導(dǎo)向更加純粹,也更易于被全世界不同文化地域的觀眾所接受。原著中滲透出的關(guān)于漢民族是否應(yīng)該崇尚狼性的深意被弱化,因為這一主題并不能吸引所有文化視域的觀眾。因此,阿諾淡化了這一內(nèi)涵指向,將另一個主題強化并使其變得更加銳利,讓人更加難以釋懷。在這一點的處理上,如果換作中國導(dǎo)演,可能無法拋棄來自民族的精神包袱,所以,作為法國導(dǎo)演,阿諾的身份使得這樣的改動更加輕松自然。
二、從電影到電影
為了更為深刻地了解影片,我們反觀法國導(dǎo)演阿諾之前的作品,最為經(jīng)典的便是以熊為敘事主體的影片《熊的故事》以及以虎為敘事主體的影片《虎兄虎弟》。這兩部影片的成功使得阿諾導(dǎo)演成為拍攝動物主題電影的代表性人物,正因為如此,該片的出品方中影特別邀請阿諾來執(zhí)導(dǎo)。同時作為導(dǎo)演阿諾的經(jīng)典作品,上文提到的三部作品有許多可比之處,本文將截取各自其中的三個段落進行比較。
電影《熊的故事》中兩只熊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并孕育了小熊,小熊曾經(jīng)被人類捕獲后又放回了山上;電影《虎兄虎弟》中老虎夫婦恩愛合歡,孕育了小老虎,小老虎也曾被人類捕獲后又被放回森林;電影《狼圖騰》中陳陣心系小狼崽,掏出小狼崽后和小狼崽開心地玩耍,之后小狼崽也被放回了草原。
這三部影片中都有這樣類似的段落,通過比較觀察這三個段落,我們不難看出,阿諾的作品總是貫穿著三個主題:愛、友誼和自由。影片中傳達的愛,從不僅指動物與動物之間的愛,還有人和動物之間的愛,從廣義上來看,更有人類對大自然的敬愛。電影《狼圖騰》中,陳陣對狼充滿了癡迷,他篤定自己一定要養(yǎng)大一只小狼崽,在這樣的意志驅(qū)使下,陳陣勇敢地去掏了狼窩。陳陣作為一名男性,這種掏狼窩的行為從某種角度來看,可以引申為鉆進母狼的子宮。這樣看去,小狼崽就成了陳陣這一人類與狼的結(jié)晶,事實上,之后陳陣對小狼崽的哺育也確實如同一位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在姜戎的原著中,每一章的開始都有一段講述人狼結(jié)合或者狼人的小故事,這其實是一種人與狼之間產(chǎn)生愛的寓意。三部影片中都有人和動物一起玩耍的畫面,畫面溫馨和諧,令人感動,這意味著人與動物是可以培養(yǎng)起真摯的友誼的。基于前兩部影片的鋪墊,在電影《狼圖騰》中,沒有過多地表現(xiàn)陳陣照顧小狼崽的細(xì)節(jié),而是巧妙地將重心放在表達人與動物的和平共處與友誼之上。阿諾的這三部影片結(jié)局都是大同小異的,曾經(jīng)與人類發(fā)生了特殊關(guān)系的小動物最終都被放回了大自然,這表示人類尊重動物們對自由的追求,同時也表示人類與大自然互相理解、和諧共生的概念,而拋棄了人類曾經(jīng)要主宰大自然的幻夢。姜戎的原著中,小狼崽的命運以悲劇告終,但在電影中阿諾進行了改編,給了小狼崽一個自由樂觀的未來,這符合阿諾一貫的作品風(fēng)格,也符合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大主題。
愛、友誼和自由都是建立在人類與自然的存在關(guān)系上的,是宏觀的人類生存主題,在這一個宏大主題的前提下,原著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區(qū)域性和民族性的主題、特殊歷史時期與人性的主題,都被阿諾弱化處理。縱觀阿諾的三部作品,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一個善于描繪人與自然共生的“動物導(dǎo)演”,阿諾的堅持從未改變,這樣的堅持滲透到電影的改編上,成就了與原著存在差異卻依然不失為成功的改寫。
三、從批評到電影
當(dāng)今電影領(lǐng)域有許多跨國合作的模式,例如中國人拍攝但取景地在他國、由外籍華人創(chuàng)作、外國人創(chuàng)作的華語影片等。這類影片都存在著跨文化特質(zhì),也都有其獨特的解讀理論。然而,該片雖然是由法國導(dǎo)演執(zhí)導(dǎo),部分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技術(shù)支持也都是由外籍團隊完成,但它卻是一部中國電影。因為故事素材由中國人創(chuàng)作,出品單位也是中國企業(yè),拍攝地和敘事主體都是中國人,外籍團隊只不過是聘任關(guān)系。但是,由于阿諾和外籍團隊的參加,這些外籍電影人對故事的改寫和重造,讓該片不再是一部純粹的中國電影。因而,我們需要給電影找到一個準(zhǔn)確的解讀方式。
電影學(xué)者魯曉鵬將中文電影劃分為以下幾種范式,分別為民族、跨國、華語和華語語系電影范式,這種劃分理論對時下的中文電影研究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指導(dǎo)意義。由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殊性,中文電影雖然語系相同,但不同地域以及海外華人在不同的政治體制和價值導(dǎo)向下,創(chuàng)作出的電影作品也有顯著的差異,因而,魯曉鵬的劃分方式十分科學(xué)和客觀,為電影學(xué)術(shù)界解決了難題。
然而,通過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這四種范式都無法準(zhǔn)確地定位電影《狼圖騰》。從民族的角度來看,該片并非以漢民族為主體,而是以蒙古族和狼族的角度為出發(fā)點,原著中甚至對漢民族是存在隱含的批判的。電影中出現(xiàn)過很多次對蒙古人特性的探討,而且,隨著劇情的發(fā)展,陳陣逐漸開始對蒙古族的生存環(huán)境和價值導(dǎo)向產(chǎn)生了皈依感,他的漢族特性在悄然改變,盡管蒙古人仍然認(rèn)為他始終不屬于大草原,但他自身一直在改變。漢族人卻在批判漢族,在這個基礎(chǔ)上,我們可以判定,該片并不能用民族電影范式來解讀。
同樣,該片也并不算跨國拍攝的中文影片,跨國合拍影片的基礎(chǔ)應(yīng)是資本的合作,以及因為資本合作而衍生的相互影響。而電影《狼圖騰》雖然涉及法國制作團隊,但是外籍團隊僅僅是被聘用而已,至于后期在影片即將制作完畢之時,阿諾看好它的商業(yè)價值,拉進了一些外籍資本,但這并不能算作是純粹的資本跨國合作。而且,跨國電影范式中普遍存在各不同合作方之間的互相影響和互相對抗,而阿諾并沒有與中國投資方乃至中國區(qū)域文化發(fā)生任何角力,他只是描繪了自己對中國的想法而已,所以,影片不適用跨國電影范式。
那么,是否華語電影范式適用該片呢?所謂華語電影,起初只是不同地域之間為了便于溝通,基于一種謀求合作的需求建立的一種詞語。華語電影的研究類似文化的全球化共享,忽略國界、政治體制等因素,用相同的文化視域和語言體系來進行劃分。雖然在表象上看,電影在語言上是華語電影無疑,但如果仔細(xì)考量,用華語電影來界定該片仿佛并不貼切。在這部影片中,真正的主人公應(yīng)當(dāng)是狼族,所以不應(yīng)用人類的語言體系來規(guī)劃。
至于華語語系范式電影,它本身是指不居住在中國境內(nèi)的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出的電影作品,這類作品通常都存在著去中國化的意識內(nèi)涵。但是,電影雖然具有去漢族化的引申含義,卻談不上“去中國化”。最重要的是,該片的拍攝和制作都是在中國境內(nèi)完成,從這一點看,它不能算作華語語系范式電影。
經(jīng)過以上的分析,很難將電影劃分到四種范式電影中的任何一種,那么該片究竟該如何來進行歸類呢?本文認(rèn)為,可以為《狼圖騰》規(guī)劃一種全新的類別,既“跨主體—地域間性”中文電影。
本文通過分析和探討,從如下幾個方面探索出影片的“跨主體—地域間性”特質(zhì)。電影中沒有體現(xiàn)出主體和客體的對抗情形,如果《狼圖騰》由一名中國導(dǎo)演來創(chuàng)作的話,極有可能將漢族設(shè)定為主體,而將蒙古族設(shè)定為客體,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抗必然不可避免。然而,法國籍導(dǎo)演阿諾沒有這樣安排,也沒有必要這樣做,阿諾不是中國人,不需要承擔(dān)來自精神深處的包袱,因此,影片中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立關(guān)系被悄然淡化,而不同主體之間的共生則凸顯出來。在影片中,漢族人、蒙古族人以及狼族被定義為具有同樣地位的不同主體,他們是平等的,沒有隸屬或臣服的關(guān)系。影片中對不同主體的建立,契合了主體間性的理論。主體間性并不局限于不同民族或不同物種,也會發(fā)生在不同的空間中,構(gòu)成地域間性。電影的場景設(shè)定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但影片中傳達出的關(guān)于愛和自由的主題卻適用于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這種具有普適性的主題值得整個人類去思索,這便構(gòu)成了地域間性。
四、結(jié) 語
電影《狼圖騰》的成功改寫為當(dāng)今的國產(chǎn)電影樹起了一面全新的旗幟,引領(lǐng)了跨文化創(chuàng)作的新潮流。本文經(jīng)過分析得出結(jié)論,影片應(yīng)當(dāng)屬于“跨主體—地域間性”中文電影。該片中顯示出來的“跨主體—地域間性”具有平等、交叉和共存的特點,這正是影片所要傳達出的主旨,也是電影成功的重要原因。
[課題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學(xué)語境的多元意義及其生成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3CZW005)。
[參考文獻]
[1] 韓宇宏,席格.《狼圖騰》及文化觀念轉(zhuǎn)型[J].中州學(xué)刊,2007(06).
[2] 李永東,李雅博.論中國新時期文學(xué)的西方接受——以英語視界中的《狼圖騰》為例[J].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1(04).
[3] 趙薇.生態(tài)批評視野里的《狼圖騰》[J].江漢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科學(xué)版),2005(03).
[4] 王學(xué)謙.《狼圖騰》與新世紀(jì)文學(xué)的生命敘事[J].文藝爭鳴,2005(02).
[5] 丁亞平,吳冠平,陳宇.《狼圖騰》三人談[J].當(dāng)代電影,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