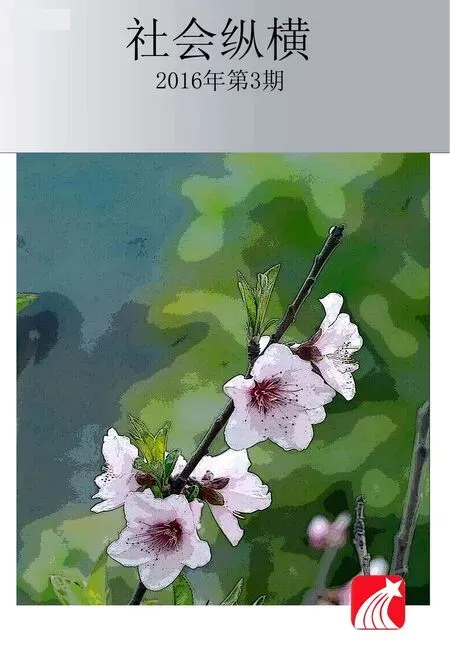嵌入式發(fā)展:文化兼容與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路徑選擇
李 明
(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20)
?
嵌入式發(fā)展:文化兼容與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路徑選擇
李明
(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內容摘要】本土化進程中的社會工作實質上是一種嵌入性的發(fā)展。即在宏觀層面體現的是一種包括制度、組織、資源等體制性嵌入;在專業(yè)發(fā)展和具體的工作領域則體現著“本土化”特點的理論與實務模式建構。而在這一進程中,文化因素是一個重要方面,涉及社會工作本土化發(fā)展的各個方面。筆者結合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家—國”理想、社會關系結構以及社會資源的動員方式等方面探討了我國本土化進程中的社會工作理想、行動策略及其資源的支持性問題。并指出嵌入式發(fā)展將是促進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中文化兼容及其本土化發(fā)展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嵌入式發(fā)展文化兼容社會工作本土化
一、中國社會工作及其本土化
(一)中西文化視角下的專業(yè)社會工作
從西方社會工作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來看,社會工作源于宗教的助人活動,其本身與西方宗教文化密切相關;從其工作理念及核心價值來看,西方社會工作更是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信仰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是西方文化核心的價值觀念。這些核心的社會價值觀念產生于新教改革、文藝復興和社會改革運動。在以此為基礎的西方社會工作,更是將人的平等、尊嚴、發(fā)展及社會的公平公正、文明進步作為其核心價值觀,并在實務工作中得到貫徹實踐。
我國專業(yè)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是于20世紀20年代引入的,其間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早期“社會工作者”也進行了大量的本土化實踐。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社會工作實踐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發(fā)展歷程。1952年我國的社會學被取消,社工教育也隨之停止;經歷了30年的計劃經濟時期,社會工作完全退出學科體系和實務領域,取而代之的是“全能政府”;80年代中期,國家教委決定在高校開辦社會工作專業(yè),社會工作又迎來一個新時期。經過了30年的發(fā)展,我國的專業(yè)社會工作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專業(yè)化、職業(yè)化、本土化的特征和發(fā)展傾向。
從中西方社會工作的起源及發(fā)展來看,社會工作與特定的歷史、文化緊密相關,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及文化基礎是形成社會工作及推動社會工作發(fā)展的基礎,也是社會工作價值理念形成的核心因素,并對社會工作理論的完善、實務的開展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二)社會工作的本土化
所謂社會工作本土化是指產生于別國(地區(qū))的社會工作進入其他國家(地區(qū))發(fā)生變化的過程。通常指社會工作較為發(fā)達的國家或地區(qū)的理論與實務經驗進入社會工作發(fā)展較晚的國家或地區(qū)所發(fā)生的現象。這些經驗可能是整體意義的,也可能是局部或者細節(jié)的。然而不管如何,這里都暗含著一種假設,即進入另一社會文化區(qū)域的社會工作在它發(fā)生和發(fā)揮作用的地方是成功的,是有經驗可循的,否則它就不大可能進入另一社會文化區(qū)域。
社會工作本土化不僅僅是指價值觀的本土化,也包括了社會工作制度、理論及實務方法經驗的本土化,是一個比較綜合的說法。可以這么認為,本土化進程中的社會工作實質上是一種嵌入性的發(fā)展。即在宏觀層面,體現的是一種包括制度、組織、資源等在內的體制性嵌入;在專業(yè)發(fā)展和具體的工作領域則體現著“本土化”特點的理論與實務模式建構。而在本土化這一進程中,外來的首先進入的是后者的社會文化區(qū)域,即應當與原有的社會制度相配合,共同支持人們共同生活的過程。其實質是進入者對后者的文化適應的過程,對“本土”來說則是文化選擇、融合與接收的過程。這是文化因素是一個重要方面,當然它在這一過程中涉及社會工作本發(fā)展的各個方面。
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中的兼容性問題
人類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創(chuàng)造出文化,同時,它又在它所涵蓋的范圍內和不同的層面發(fā)揮著主要的功能和作用。簡單來說,其影響主要來自于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以及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
當然,對于“舶來品”——社會工作的影響,同樣也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動發(fā)揮作用的。可以這么認為,文化對于社會工作的影響首先反映在制度方面,即通過其特定的文化方式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工作的制度建設產生影響。其次,在社會工作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則通過文化的具體形式,如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規(guī)范、傳統(tǒng)習俗等對人們理解和接受、接納社會工作的程度產生一個選擇性的認識。這本身包括了對社會工作價值理念、理論體系、實務方法及經驗等的判斷和選擇,實際上就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而在本土化這一進程中,社會工作自身特點與特定區(qū)域的社會文化之間的選擇性、適應性問題就是一個不可不察的現實論題。本節(jié)筆者主要結合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家—國”理想、社會關系結構以及社會資源的動員方式等幾個方面探討我國本土化進程中的社會工作理想、行動策略及其資源的支持性問題。
(一)“家—國”理想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受儒釋道三家影響,當中尤以儒家文化的影響力最為深遠,作為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在對社會管理方面,儒家文化表現的更為具體,它不僅約制了人們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同時也更加具體的勾勒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系統(tǒng)的“家—國”理想。
1.“大同”的國之理想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是《禮記·大同篇》對理想社會的一種描述。這種社會形態(tài)與社會工作的最終目標極為吻合。它從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領域的主要方面建構出了涵蓋老人、就業(yè)、婦女兒童、殘疾人等主要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障體系。同時這一社會理想所要實現的具體目標,也正是當前社會工作所致力追求的。
2.“孝道”與“家本位”的文化傳統(tǒng)
儒家認為“士有百行,孝敬為先”,“治身莫先于孝”,非常注重和推崇孝道。孝道觀在具有較強的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約束力。在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個人也并非如西方社會般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個人往往被作為集體的一部分,而在中國最小的集體便是家。個人的價值、身份和意義主要是透過“群己關系”得到充分體現的;個人的成就與家庭的成就是你密不可分的。這一點具體反映在社會工作倡導的養(yǎng)老理念和方式上,在中國,子女贍養(yǎng)、家庭養(yǎng)老一直是傳統(tǒng);西方社會的自我養(yǎng)老、機構養(yǎng)老是主流。在當前中國社會,新型養(yǎng)老模式尚未成型之前,傳統(tǒng)的養(yǎng)老方式依然要發(fā)揮其作用,這就需要重申孝道的重要性。
此外,在中西文化中關于“人”的理解上也是存在差異。西方社會倡導“個人主義”、講求“人人平等”個人只需按其擁有的認知行為和才干盡力發(fā)揮,這種“自我實現”無需有太多的情境考慮,這與中國文化“推己及人”有所不同;中國社會盛行“集體主義”,將人束于一個“網絡”之中,往往“家、家族”是其最小的網絡,也是其人際關系和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縱觀人的一生,體現在情感支持、經濟支持及其婚喪嫁娶等各個方面。這一點在社會工作的價值觀方面存在差異,同樣在個體的求助模式中“家”的影響和介入往往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這個強而有力的家庭關系和群己關系對比于社會工作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如案主自決、獨立、自主、個人的獨特性等觀念在方向上有所不同,社工必須在實踐中保持一定的文化敏感性,求同存疑、存異,尋求本土化的契入點。
(二)“面子問題”與關系社會
“面子”問題在中國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維系體面和關系的基本需要,爭臉、給面子和禮尚往來都被列入基本行為規(guī)范。據此,形成了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而又廣為普及的面子與關系社會。
在以“面子”為自我尊嚴表征下的中國人,一方面,表現的“樂于助人”慷慨大方,卻相對不愿意“求助于人”或者接受他人幫助。在社區(qū)這樣的“熟人社會”中更是恪守“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生怕自己面臨的困境成為別人特別是鄰居、“熟人”嘲諷的話題。此外,中國人也喜歡和善于拓展“關系”,在傳統(tǒng)的理解看來關系需要拓展,只有將自己處于一個穩(wěn)固的強關系網絡中才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差序格局和關系紐帶中的中國人,即使個人或者家庭遭遇困境和困難,其求助的對象一般也是遵循著關系的強弱排列的(首先大多依靠的是初級群體,其次會依賴政府)。對于政府機構特別是社會工作者及機構一般是被動接受或排斥,不到萬不得已,一般是不會主動求助社工機構,而對于服務的保密性要求也往往是嚴格甚至是苛刻的。這一點在社會工作實踐中需要社工重新認識,定義和把握。
(三)“身份社會”與社會工作實務中的資源動員
“身份”是在中國人的話語體系中常見的詞匯,一般指“人的出身、地位、資格。身份現象作為中國社會的一種傳統(tǒng)行為和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現象,今天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
首先,身份作為個體成員交往中識別個體差異的表示和象征,它能夠給予社會以秩序和結構。即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指這個社會的成員之間按照特定的社會地位或社會角色行動與互動的一種社會情境與狀態(tài),它是在特定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guī)范框架內進行社會互動的社會關系。
其次,身份是一種社會資源的鏈接和整合媒介。身份現象本身是一種與個體的某種地位、職業(yè)等相對應的身份認同標識。身份是一種資源,是一種社會資本。所以一定的身份就意味著地位、意味著他占有的資源的多寡。
在現代中國社會中,身份意識、身份情結促生了身份的社會資本屬性,并且作為一種潛在的行為規(guī)則體系長時間、持續(xù)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本土的社會工作實務開展中,這種“身份”標識下的社會秩序和社會互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在情境中”的實務切入模式,為社會工作實踐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同時在服務提供過程,“身份”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鏈接和整合媒介能夠有利于資源動員和整合,進而更好地達成服務目標,服務案主。當然,社工自身也需要注重并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有效拓展和合理運用這些有利于社會工作實務開展的寶貴資源。
三、嵌入式發(fā)展: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路徑選擇
社會工作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在本質上雖然不同,但兩者也非互相排斥。這也是社會工作進入我國并能長期存在下來的原因。同時,來自社會制度和國情,特別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促使社會工作必須選擇本土化的發(fā)展路徑。一方面,要保留社會工作中超出國界和意識形態(tài)之上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引進社會工作專業(yè)的同時,尋求其個性成分的“本土化”。
從社會工作本土化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及其行動策略來看,嵌入式的發(fā)展無疑是一種最佳路徑的選擇。所謂嵌入,簡單來說即是指一事物(固體A)卡進另一事物(固體B)的過程和結果。一般的,我們把A進入B的過程稱為嵌入,而當A已經進入B時,我們會說A已經嵌入于B。
當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fā)展總體還處于嵌入的過程中,在這一過程,包括社會工作制度、社會工作價值觀、理論體系及其實務方法等的全面對接和深度嵌入將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發(fā)展方向。在推進我國社會工作的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發(fā)展過程中,注重將社會工作的共有價值與個性部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結合,尋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資源與社會工作的有效兼容,將是首先需要考慮的,這也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內在要求。
參考文獻:
[1]梁祖彬,顏可親.權威與仁慈——中國的社會福利[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2]王思斌.試論我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學刊,2001(2).
[3]王思斌.社會工作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唐曉英,李精華.社會工作本土化中的文化對接[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5]Kim,Y.O.(1995).Cultural Pluralism and Asian-Americans:Culturally Sensitive.
[6]王力平.身份——社會學視野中的社會資本[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9).
[7]王思斌.中國社會工作的嵌入性發(fā)展[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2).
*作者簡介:李明(1976—),男,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社會工作理論及弱勢群體保護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106(2016)03-00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