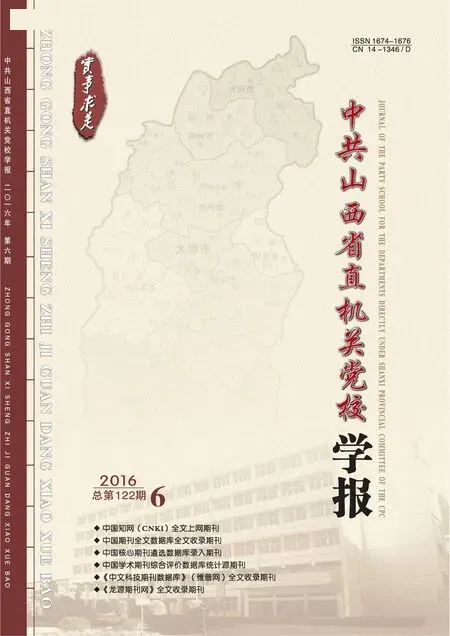國際投資仲裁的管轄權與可受理性概念辨析
張建 孟斌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088)
(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檢察院,北京100000)
國際投資仲裁的管轄權與可受理性概念辨析
張建 孟斌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088)
(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檢察院,北京100000)
國際投資仲裁庭的管轄權,以及仲裁庭對具體仲裁請求的可受理性,均為仲裁庭行使案件審理權限的先決要件。在投資爭端解決中,被申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與可受理性的質疑所具有的實踐意義是不同的,因此區分二者殊為必要。在被申請人向仲裁庭所提出的關于股東派生仲裁請求、仲裁申請人未遵守等待期的異議、以及適用拒絕授惠條款的主張這幾方面,究竟屬于管轄權異議還是可受理性異議,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在認定上或是達成了初步的共識,或是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尤其引發了投資仲裁實務界對統一標準的追求。
管轄權;可受理性;投資仲裁;遵循先例
一、引言
通常,國際裁判機構的管轄權基礎涵蓋規范層面與事實層面,其不僅存在于特定的公約、章程、規約所規定的各項條件中,而且亦體現在爭端當事方就個案所達成的爭端解決方式的合意中。相較而言,前者是相對抽象意義的管轄權根據,而后者是具體個案中的管轄權基礎,二者需同時滿足。盡管每個仲裁個案存在特殊性,但其規范基礎存在若干普遍共性。就管轄權來看,通常涉及屬物管轄權、屬人管轄權、屬地管轄權、屬時管轄權幾個方面,在這些方面,每個國際爭端解決機構或有交叉或重疊,但彼此側重點各有不同,所解釋的法律與所裁判的案件分別具有針對性。[1]就可受理性來看,各個機構也多有不同,例如2002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17條在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簡稱ICC)的可受理性問題上,主要涉及國家客觀不能或主觀不愿的問題,強調的是國際刑事法院介入相關情勢的條件,而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簡稱ICJ)的司法實踐中,可受理性問題往往圍繞著具體個案中爭端是否存在、爭端是否具有法律性、是否用盡當地救濟等而展開討論。有學者曾專門針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規范與實踐,試圖就管轄權與可受理性進行辨清,其指出:管轄權是國際刑事法院對哪些犯罪具有裁判權的問題,是從靜態的角度出發,解決管轄權存在與否的問題;而可受理性是指國際刑事法院對具體情勢或案件是否具有裁判權的問題,是從動態角度出發,解決管轄權是否應當行使的問題。[2]
就不同的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來看,其不僅在管轄權與可受理性問題的判定標準上存在差異,且對二者劃定的界限也顯然有別。一般而言,如果僅是仲裁庭行使管轄權的條件未成就,則仲裁庭將認定自身不具有管轄權。而可受理性問題則是在管轄權條件已滿足的基礎上,基于其他非管轄權的原因導致仲裁庭不予受理,例如未用盡當地救濟、涉及第三方而第三方不同意仲裁等。當然,在具體案件中,仲裁庭或爭端當事方基于仲裁策略考慮,可能會選擇將管轄權的問題包裝成可受理性的問題,相反亦然。例如,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簡稱ICSID)的某些投資仲裁庭即把仲裁的前置條件認定為可受理性的問題,繼而在裁決中稱,不滿足前置條件并不影響仲裁管轄權。
但總體來看,對管轄權與可受理性二者之間關系,目前尚且缺乏比較準確的闡釋與論證,盡管在國際投資仲裁實踐中常常引述并運用這兩個概念,但理論上的規律性總結卻相對不多。考慮到整個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的框架過于宏大,不易把握,對二者關系的深入研判仍需回歸到某項特定的投資仲裁體系。基于此,筆者擬以《能源憲章條約》(簡稱ECT)項下的國際投資仲裁程序為例,分別從規范與實證角度考察二者異同,并試圖作出規律性的總結。
二、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界限模糊的成因
《國際法院規則》第79條明確肯定了爭端當事方有權分別就法庭的管轄權與可受理性提出異議,這無疑間接認可了二者間的區分。然而,國際投資仲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程序法律規則與投資條約,對二者的關系卻緘默不言。諸如《ICSID公約》、《ICSID仲裁規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簡稱《UNCITRAL規則》)、ECT等,都不存在類似于《國際法院規則》第79條的相關規范。不過,規范的缺失本身即是個值得推敲的默示立場,這絕不表明國際投資仲裁中可將二者混為一談。事實上,恰恰相反,關于二者是否應予區分,區分的標準,以及區分的實踐意義等問題,自始即存在爭鳴。
在ICSID項下的投資仲裁案例中,不同的仲裁庭意見也并未統一。早期的代表性案件,如2004年的Enron v.Argentina案、2005年的Methanex v.USA案,仲裁庭并不認可就二者進行剝離;但在最近幾年的幾起案件中,仲裁庭卻明確承認了二者的區分,盡管具體區分的裁判標準仍有差異,例如2011年的Abaclat v.Argentina案、2011年的Hochtief AG v.Argentina案、2012年的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a案。
從成因上考察,之所以較難在兩個實踐性很強的概念間作出清晰的厘定,從仲裁本身上找原因,這至少源自兩個角度。一來,投資仲裁程序內部不存在普通法語境下“遵循先例”的傳統。[3]盡管相較于商事仲裁的保密性而言,投資仲裁更具透明度,在爭端當事方同意的基礎上,仲裁程序命令與實體裁決均可公布,但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在法律解釋與制度運用上互不牽制,亦不受彼此法律意見的拘束,在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的判定問題上,各仲裁庭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因此就相同問題的意見作出彼此殊異的結論,實為在所難免。二來,投資仲裁的管轄權與可受理性貌似兩個問題,實則千頭萬緒、爭點分散、缺乏共性,例如,就既往的仲裁判例法來看,關于當地救濟要求的用盡、仲裁前置性條件的滿足、保護傘條款的啟用、個案爭端當事方是否具備出庭資格等具體問題,究竟如何定性,定性后如何解釋和適用,幾乎堪稱“一千零一夜”個故事。有論者提出,這一投資仲裁危機與國際投資條約的解釋方法有關,如果不同仲裁庭所采用的法律解釋方法大體一致,倒可“殊途同歸”。[4]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歸因于尚未構建起普遍性的上訴機構,也就無從確保法律解釋的連貫性、一致性、統一性,繼而難免使得仲裁庭在個案中得出不同結論。
三、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的概念區分與實踐意義
(一)概念區分
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的問題之所以在投資仲裁中尤為凸顯,這并非出于純粹抽象的理論辯爭,而是由于在仲裁程序中,被申請人針對仲裁庭權限所提出的異議,以及該異議對仲裁權的實質作用力范圍。因此,國際投資仲裁中較早對這兩個概念做區分的努力也始自于仲裁庭,而非理論家的空想。在Waste Management,Inc.v.United Mexican States案中,仲裁庭提出:管轄權是仲裁庭審理案件的權力,而可受理性的爭論則圍繞著案件本身是否是有瑕疵的,以及本案是否適合由仲裁庭來審理而展開。這一最初的區分嘗試,似乎旨在強調管轄權問題針對的是仲裁庭的權限,而可受理性問題直指特定仲裁請求的適當性,其討論的中心不同。但殊不知,仲裁庭的權限與仲裁請求的適當性難以清楚地剝離開來,以《ICSID公約》第25條,其要求可予管轄的事項限于“直接因投資而產生的法律爭議”,因而若不對仲裁請求以及爭議標的所涉的投資進行分析,則無從確立管轄權。可見,這種區分未必十分精當。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區分從概念所指向的對象入手,無疑又提供了有益的啟發性思考。筆者認為,與其單純區分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的理論差異,不妨從實踐可行性角度來嘗試區分當事人針對管轄權所提的異議與針對可受理性所提的異議。通常,管轄權異議一旦成立,則仲裁庭不僅不得再繼續進行程序,且將喪失管轄權,所以可以理解為管轄權異議是針對仲裁庭。對這類異議是否成立的認定,取決于兩方面因素:其一,仲裁庭對本案的裁判權是否存在;其二,如果存在,仲裁庭裁判權的范圍究竟涵蓋哪些事項。而相比這下,對可受理性的異議,更多地針對仲裁請求(claim)本身,對這類異議的認定,取決于仲裁庭基于事實審理某項具體請求是否具有適當性。如果可受理性的異議成立,僅表明具體個案中的爭端及仲裁請求尚未成熟到可提起仲裁的程度,即請求本身是由瑕疵的,一俟該瑕疵消除,則仍然存在重新啟動仲裁程序的可能。
(二)實踐意義
對管轄權異議與可受理性異議進行區分,從整個仲裁程序的整體考慮,至少具有三方面實踐作用:其一,對審查裁決的影響,在劃清管轄權異議與可受理性異議的基礎上,仲裁庭在仲裁裁決中對管轄權的決定仍然可能被審查(例如對仲裁庭的管轄權認定不服,而提起裁決撤銷程序),但其中關于可受理性的認定則不得再被審查[5];其二,對當事人重新提起仲裁請求的影響,如果仲裁庭基于自身不享有管轄權為由駁回當事人的請求,則當事人不得再將同一請求重新提交仲裁庭,但如果仲裁庭駁回的理由是出于不具備可受理性,則當先前的瑕疵消除后,仍然可重新提交同一請求;其三,對仲裁庭能否主動作出決定產生影響,即使當事人未提出管轄權異議,但仲裁庭意識到本案爭端明顯超出自身的管轄權范圍時,理應主動拒絕審理案件,但可受理性則顯有不同,如果具體仲裁請求的可受理性雖有瑕疵,但爭端雙方均為提出異議,則此種沉默行為本身即視為當事人放棄了提異議的權利,相關違反自動得以治愈,不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
應當注意的是,以上規律性概括仍然旨在提供參考性指引,應避免對某類阻礙仲裁庭審理的行為究竟屬于管轄權還是可受理性問題作“一刀切”式的論斷。例如,在投資者的不當行為(如欺詐、賄賂、非法投資)究竟是否必然是管轄權的問題上,就有學者提出了質疑。但不可置否的是,可受理性作為一項程序性工具,其可用于篩選和過濾掉某些不適宜的投資者請求,盡管投資仲裁歷史上不乏仲裁庭直接否定了在投資條約仲裁程序中使用“可受理性”的概念,但愈來愈多的主流實踐表明,可受理性的確可以為投資仲裁庭所運用,來決定具體請求是否可以被審理。[6]通過對現有典型仲裁實踐的觀察與分析,筆者注意到,在股東提出的派生仲裁請求、仲裁申請人未遵守等待期、利益拒絕條款的適用這幾方面,可受理性的問題尤其突出,值得深入研判。
四、ECT投資仲裁對二者區分的典型實例
(一)股東提出的派生仲裁請求
ECT第1條第6款與第1條第7款分別就“投資”與“投資者”進行了定義。其中,第1條第6款b項涉及到股東所提出的派生仲裁請求,該款稱“投資”是指:各種由投資者所有,或直接或間接控制的資產,包括(b)公司或商業企業或股份、股票,或其他股份形式的公司或商業企業的債券或其他債務;“投資者”是指:(a)在涉及締約方時,投資者包括兩類,其一,根據可適用的法律,在締約國擁有永久居所的自然人公民,其二,根據在締約國適用的法律而成立的公司或其他組織;(b)在涉及第三國時,投資者是指滿足了(a)項中列明的具體條件的自然人、公司或其他組織,但須作必要的修正。
當遭受來自東道國不法行為侵害的企業的股東以自身的名義之間提起仲裁請求時,作為被申請人的東道國通常會對申請人的主體適格提出異議,對這種異議,仲裁庭主要關注的是股東所提的派生請求的屬人管轄權與屬物管轄權問題,意即,將此種異議作為管轄權的異議來加以認定。例如,在2009年的Yukos Universal Ltd.v.Russia案中,仲裁庭認定:對投資對象企業的股份所持有的法定所有權確實可作為適格投資,因此本案的仲裁申請人已經滿足了屬物管轄權的基本條件。再如,在2003年的Nykomb Synergetics Technology Holding v.Latvia案中,仲裁庭認定間接持股也構成本案條約項下的投資,因此應視為符合了屬物管轄權的要件。不過,有學者已經注意到,僅僅將股東提出的派生請求是否適格的問題視為管轄權異議并不準確,對這類請求提出的質疑同時也涉及到可受理性問題,仲裁庭尤其應當考察仲裁申請人(股東)對其所提出的仲裁請求是否擁有法定利益,即仲裁請求中是否牽扯股東所遭受的個人損失。[7]特別是,如果仲裁庭對股東所提出的不具有可受理性的仲裁請求行使了管轄權,那么很容易導致損害評估方面的結果錯誤,因為投資對象所遭受的損失與股東所遭受的損失互有關聯但又相對獨立,因此在確立管轄權的基礎上還務必需進一步分析具體仲裁請求的可受理性,兩個程序步驟均不可或缺。
(二)仲裁申請人未能遵守等待期
ECT第26條第2款規定了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8]投資爭端發生后,首先各當事方應尋求通過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如果在一方提出協商請求后的三個月內,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則投資者單方面有多種選擇。[9]其可以選擇將爭端提交至東道國的司法或行政程序,亦可選擇依當事人事先達成的關于爭端解決的特殊協議,還可以通過國際仲裁加以解決。實踐中,在當事人之間常常引發爭執的是,爭端發生后某一方并未經過三個月的協商而徑行直接提起國內訴訟或國際仲裁,此時,對方當事人則向仲裁庭提出異議,主張未經過三個月等待期則仲裁庭不得審理。對于仲裁申請人未遵守等待期的程序異議,究竟屬于管轄權異議還是可受理性的質疑?在Hochtief AG v.Argentina(2011)、Impregilo S.p.A.v.Argentina(2011)、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Argentina(2012)這幾個案件中,爭端雙方對此問題曾有過十分激烈的辯爭。而仲裁庭的認定無非歸于兩種結論:第一種,將此視為管轄權問題,其推理基礎是將對等待期的遵守視為當事人之間存在國際仲裁同意的特別條件,且未遵守等待期的異議更多是針對仲裁庭而不是針對具體的仲裁請求,因此更符合管轄權異議的特征;第二種,將此視為可受理性問題,其推理基礎是將對等待期的遵守視為執行一項已經存在的仲裁同意的條件,從異議的對象上看,這種未履行等待期的質疑仍然是對具體仲裁請求的異議,如果未經過特定的等待期,則相應仲裁請求根本無法有效形成。
就仲裁實踐而言,更為廣泛存在的是“事實驅動”的解釋方法(fact-driven approach),即以解決程序問題為必要,不硬性預先區分等待期究竟是管轄權問題還是可受理性問題。在2010年的Mohammad Ammar Al Balhoul v.Tajikistan案中,仲裁庭注意到:關于仲裁申請人遵守等待期的問題,究竟僅僅屬于一個簡單的程序條件還是一項管轄權要件,存在相互沖突的矛盾觀點。在2008年的Amto v.Ukraine案中,仲裁庭并未刻意提及管轄權與可受理性之間的辯論,而是注意到以往ICSID仲裁庭的基本觀點是,未遵守等待期的要求并不構成對仲裁管轄權的根本限制。在2005年的Petrobart Ltd.v.Kyrgyzstan案中,仲裁庭得出結論稱:申請人已經滿足了提出友好協商的程序條件,至于是否經歷以及經歷了多久的等待期,這無關緊要,不影響仲裁庭行使管轄權。在2010年的AES Summit Generation v.Hungary案中,仲裁庭將ECT第26條第2款視為一項程序性條件,并認定仲裁申請人已經滿足了這項要求。總體來看,不同的仲裁庭在等待期問題的處理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基本不去在裁決中考量其究竟是管轄權的問題還是可受理性的問題,并且均認定對等待期的違反不構成仲裁庭行使管轄權的限制。
(三)利益拒絕條款的解釋與適用
利益拒絕條款(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又稱拒絕授惠條款,其并非國際投資協定的新型條款,但是卻在近幾年內因相關投資仲裁案例的增多而受到關注。該類條款重在強調,投資者與其國籍國之間存在真實經濟聯系,是投資者享受本國投資條約保護的前提,如某國籍國的投資者并未持續地控制該國企業或者在該國境內不具有實質性的商業活動,則締約國可以保留拒絕該投資者享有條約利益的權利。[10]究其成因,締結這類條款的目的,主要在于避免無真實經濟聯系的海外投資者通過在另一國設立“郵箱公司”,以該“郵箱公司”為跳板向東道國投資,進而通過“條約選購”(Treaty Shopping)或“搭便車”的方式,利用“郵箱公司”所在國與東道國之間所締結的、含有優厚待遇的投資條約,主張享有被賦予投資利益的權利。[10]ECT第17條第1款規定了《能源憲章條約》第三部分關于投資促進與保護的條款在特定情形下不予適用,該款稱:“當法人實體由本國公民或第三國家公民擁有或控制,且該法人實體在在本締約方區域內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時,各締約方保留否認該部分優勢的權利。”
那么類似的問題是,在投資仲裁程序中,如果被訴東道國援引此類條款對國際仲裁庭的管轄權提出抗辯,此類抗辯應被視為管轄權異議抑或可受理性的異議?對此,應采取個案而論的方法,對ECT而言,眾所公認的是,ECT第三部分所涵蓋的可被締約國拒絕授予的利益并不包括仲裁的管轄權條件。但是從不同投資仲裁庭的裁判意見來看,對此所持的態度卻并不清晰。有些仲裁庭將其視為可受理性問題,并具體審查了拒絕授惠的條件,例如2008年的Plama Consortium Ltd.v.Bulgaria案,2009年的Yukos U-niversal Ltd.v.Russia案。也有些仲裁庭將其視為管轄權的問題,并具體審查拒絕授惠的條件,例如2008年的Amto v.Ukraine案,2011年的Libananco Hold-ings Co.Limited v.Turkey案。也有些仲裁庭雖然遇到了這類問題,但并未刻意提及這究竟屬于管轄權問題抑或可受理性問題,如2005年的Petrobart Ltd.v. Kyrgyzstan案。還有仲裁庭對二者的區分做了模糊化的處理,或認為二者的區分對裁判結論無關,如2010年的Liman Caspian 0il B.V.v.Kazakhstan案。
五、結語
經過本文的考察,不難發現,以雙邊投資條約為基礎的投資仲裁庭日益意識到了對管轄權與可受理性的區分。但從ECT來看,投資仲裁的實踐尚未廓清二者的界限,甚至并非所有的仲裁庭都注意到區分二者的實踐必要性。考慮到管轄權異議與可受理性異議對投資仲裁審理權限的取得及其行使所產生的影響存在不同的側重,就實務結果而言,仲裁界與國際投資法實務界應當力求達成一套連貫且一致的區分方案,進而在法律穩定性與程序實質正義間實現平衡。
[1]張建.國際投資仲裁管轄權與雙邊投資協定的解釋問題探析[J].天津法學,2016(3):77-78.
[2]馬偉陽.國際刑事法院受理制度研究:紀念國際刑事法院成
D997.4
A
1674-1676(2016)06-0083-05
國家留學基金委(留金發[2016]3100號)聯合培養博士生項目“國際投資仲裁管轄權研究”(項目編號:201607070108)。
張建(1991-),男,內蒙古赤峰人,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2015級國際法專業博士研究生,瑞士比較法研究所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國際私法與國際商事仲裁。孟斌(1990-),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檢察院駐所檢察室科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