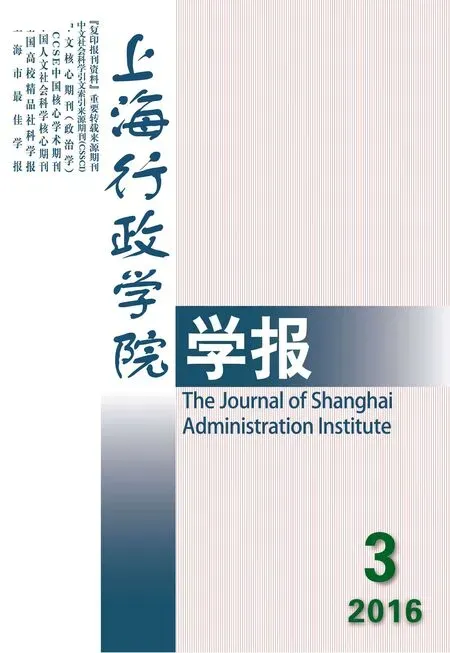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結構分析*
周定財(江蘇師范大學,徐州221116)
?
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結構分析*
周定財
(江蘇師范大學,徐州221116)
摘要:當下,我國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經歷了探索階段、建構階段并逐漸進入調整階段。結構功能主義對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研究具有較大的契合性和很強的解釋力。從結構入手來思考地方服務型政府的體制、機制及邏輯進程,對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大有裨益。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體現為宏觀上的行政體制和微觀上的機制創新;外在結構表現為地方政府與其他政治主體與社會主體的關系。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結構決定了其主體功能和核心功能是向地方民眾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需要在其內外結構的互動中得以實現,同時要在實踐中注入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公開性等價值理念。
關鍵詞:地方服務型政府;結構功能主義;內在結構;外在結構
當下,建設服務型政府已成為我國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各地方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經歷了初步探索階段、理性建構階段并進入漸進性結構調整階段[1],這是施政理念、職能組合、機構設置、結構調整、運行機制等多方面改革的聚合,是深層次、全方位的復雜系統工程。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分析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外在結構及其互動關系,對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大有裨益。
一、結構功能主義及其對地方服務型政府結構的解釋力
作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流派和研究范式,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亦稱結構功能論)是在19世紀生物學中功能主義基本原則和20世紀初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斯賓塞的社會有機論和功能需求概念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涂爾干(Emile Durkheim)、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人是積極倡導對社會問題或政治現象進行“結構功能分析”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帕森斯和默頓是該理論的集大成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20世紀中葉前后,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年)、《社會系統》(1951年)、《邁向一種一般行動理論》(1951年)和《經濟與社會》(1956年)等著作中系統、完整地闡述了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帕森斯首先將“行動”與“體系”兩個概念相聯結,提出了“行動體系”的新概念,然后又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AGIL四功能模式(或稱AGIL圖式)作為分析行動體系之結構的基本工具。其中“行動體系”由行為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四部分構成。由是觀之,社會系統是整個“行動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它之所以能夠維持并得以發展,是因為它能夠滿足四個必要的功能性條件,即適應(Adaption)、達鵠(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維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適應功能是指確保從環境中獲取足夠的資源,然后在整個系統中進行合理分配;達鵠功能是指在系統目標中建立次序級別,并調動系統的各種資源以達成這些目標;整合功能是指合作和保持系統單位之間的相互關系;維模功能主要包括模式維持和緊張調停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2]在社會系統中,上述四種功能分別由經濟組織、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與教育制度來執行,從而分化出相對應的四個子系統即經濟子系統、政治子系統、社會共同體子系統和文化(親屬)子系統。結構功能主義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在對英國人類學中功能學派所堅持的“功能統一性”“功能普遍性”和“功能不可缺少性”這三條“流行的假設”提出質疑的基礎上,將社會系統的功能需求進行了拓展,提出了“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策略以及新的功能分析范式,引入了“潛功能”(latent function)、“反功能”(dysfunction,亦稱負功能)的概念,認為并非所有的組成部分都以正功能的姿態呈現,因此要對現實社會結構的客觀后果進行功能認識,并做出功能評價,這就大大拓寬了功能分析的領域,并將結構功能主義推到一個新階段。
帕森斯和默頓等學者創立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不僅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解釋集體的秩序和規范,更為當下社會諸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性框架”[3],對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研究具有較大的契合性和很強的解釋力。該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合的大系統,每個子系統都對系統整體的均衡有序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個系統的運行狀態是否穩定,不僅取決于它是否具有滿足一般功能需求的子系統,而且還取決于這些系統之間是否存在著跨越邊界的對流式交換關系;對于一個社會系統來說,維護其內部各個子系統之間關系的最低限度的平衡是至關重要的[4]。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涉及制度、體制、機制、職能的完善和地方黨委、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社區、公民等建設主體的塑造等多個“子系統”,每一個“子系統”的優化都對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該理論還強調,結構決定功能的發揮,結構發生改變,其功能也隨之改變;結構不良,其功能也會萎縮或弱化;功能的發揮受制于結構的影響,對結構起反作用,在一個多層次系統中發生的各種功能,可以形成功能體系,表現出多層次的政治功能結構,因此任何社會制度和政治現象都可以從它們在維持更大的社會體系中發揮功能的角度進行解釋。在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中,結構是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其各項職能(或功能)的發揮也是以其內在結構和外在結構的完善為前提的,要實現地方服務型政府的主體功能和核心功能,研究分析其內外結構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和應然之需了。
二、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分析
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是包括體制和機制在內的、決定政府功能的要素的總和。具體來說,服務型政府宏觀上體現為一種具體的行政體制,微觀上反映為一系列緊密相連的機制創新;體制改革的實踐是具體的,機制創新的探索是生動的。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既不能缺乏具體的制度、體制建設目標,也不能忽略現實的各種機制創新。然而在現實的地方服務型政府構建中,機制創新往往大于、多于、重于體制改革,因此,調整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需要探索由機制創新推動體制改革的路徑,才能構成量變到質變的提升,地方服務型政府構建才將會在我國的制度變革過程中演變成現實。
1.地方服務型政府的體制結構
地方政府體制是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點。確定地方政府職能及其公共服務的范圍不僅是地方服務型政府體制創新的前提,更涉及深層次的觀念和利益問題、政府內部縱橫向關系問題以及各方面體制的綜合配套問題。地方服務型政府體制創新的現實路徑應當與政府職能轉變緊密結合,使其相互作用、相互推進。
首先,體制改革的著力點在于轉變政府職能,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無論是國務院機構改革,還是地方政府機構改革,都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5]。轉變政府職能既是政府角色的根本轉變和市場主體結構的位移,也是局部利益的調整或某種權力的失落,它具體包括管理理念的轉變、管理重點的轉變、職能關系的理順和管理方式的轉變四個方面的內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6]。也就是說,要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空間,為社會提供多主體、多層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務。要根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的自身特性,強化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收入分配、環境保護、食品藥品監管、應急救援、社會治安等方面的職能,不斷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逐步實現政府管理與社會治理的有機結合,行政手段與法律、經濟手段的有機結合,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結合[7]。通過體制改革,增強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和服務理念,從而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
其次,體制改革的重點在于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推進大部制改革。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是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有效的、可持續的公共服務必須依靠進一步的改革進行深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顧此失彼、無法接應的局面。大部制也稱大部門體制,起源于英國的政府重組改革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是將政府相同及相近的職能進行整合,歸入一個部門管理,或將一些職能相近或相關的部門整合為一個較大的部門。“職能有機統一”是大部制的精髓,“寬職能,少機構”則是其鮮明特征[8]。我國的大部制改革是總結以往改革經驗,克服長期以來政府體制中存在的機構交叉、職能重疊、政出多門、推諉扯皮、成本較高、效率低下等種種弊端的必然選擇。2008年以來,各地都在進行“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制改革的實踐,出現了“單部門突破”的成都模式、“兩集中、兩到位”的鎮江模式、“多牌同掛”的隨州模式和“黨政聯動”的順德模式等典型的實踐形態。2013年的政府機構改革圍繞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對鐵道部、食品藥品監管、衛生和計劃生育、海洋、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等6個部門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其目標在于通過理清部門間的權責關系,構建大部制內部的決策、執行、監督機制,加強部門協同,在此基礎上實現政民協同、政企協同、政社協同和政會協同。當然,大部制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實行的體制模式,結合我國實際,建立中國特色的大部門體制,還需要不斷地探索、積累和突破。
最后,體制改革的難點在于破除陳舊觀念和打破利益藩籬。每一場大的變革,總是伴隨著觀念的變革;沒有觀念的變革,政府體制改革就會顯得困難重重、步履維艱。李克強總理指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下一步改革不僅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更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9]。當前,影響體制改革深入進行的陳舊觀念,如GDP至上、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官本位”和“管本位”等,不勝枚舉。觀念問題根深蒂固,短時期內難以改變,容易造成行政體制改革的既定目標在行政人員的微觀層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換。雖然固有觀念阻礙行政體制改革,但它畢竟沒有損害改革者的利益,守舊觀念帶來的改革阻力畢竟有限。其實,體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來自政府本身,地方政府的雙重身份(既是改革的主體也是改革的對象)之間的矛盾是改革阻力的根源。行政體制改革說到底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意味著政府部門要放棄某些既得利益,這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既有的權力平衡或打破穩定利益格局。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部門和人員就會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地抵制改革;地方政府官員也會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缺陷來滿足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從而表現出“掠奪性”的行為傾向——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或是抱著“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的態度消極工作,或是對群眾反映的需要費心解決的問題應付了事,或是為了各自的局部利益,經濟建設上重復建設、重復引進,行政級別上相互競爭,互相拆臺,不擇手段爭取“升格”,等等。由是觀之,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逐步建立利益引導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利益共享機制、利益沖突化解機制、利益制約機制、利益評價機制、利益反饋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相統一的政府利益調節與整合機制,以實現個人利益、地方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平衡,這是地方服務型政府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
2.地方服務型政府的機制創新
服務型政府必須進行機制創新。“行政機制是指行政體制運行中的形式、流程、程序與技術等要素,主要涉及行政體制運行的有效性問題。其中,效率是主要變量”[10],行政機制創新主要關系到優化政府服務的形式、程序、路徑,這需要改變政府線性的責任指向,將原來單向對上負責機制轉變為互動責任機制,政府不能只對上級負責,更應該對人民負責,對社會負責。
在優化政府服務形式方面,不少地方引進工商管理技術和市場化競爭理念,構建“一站式”服務來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一些地方推行電子政務來實現公共服務的便利和高效;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與社區、社會組織、企業等的協同治理來適應公共治理的新常態;還有些地方開通政務微博和官方微信,將傳統的迂回溝通轉變為直接溝通;而有的地方仍然沿用傳統行政手段來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與數量。地方政府服務的形式不再固守原來單一、管制的方式,而是采用多元的方式,在放松規制(deregulation)的基礎上,引進民營化、憑單制、合同外包、志愿服務;在全面質量管理(TQM)的基礎上,引進目標管理(MBO)、標桿管理、績效管理;在招標投標決策上,遏制壟斷、引入競爭,注重招標過程和投標決策。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 Wilson)認為:“任何組織,不管是政府的還是私人的,一旦具有壟斷性,就會缺乏強烈刺激去提供它的服務對象所期待的服務”[11],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Pierre Calame)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國家和其他行動者的合作伙伴關系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12]優化地方政府的服務形式,就是要使政府與公民、社會、市場、企業之間,變簡單的命令與服從關系為協商與互動關系,變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單一性為多元化,建成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和供給方式的多樣化。
在優化政府服務程序方面,各地從服務價值、服務目標出發,選擇服務方式、安排服務順序、規定服務步驟、梳理服務流程、確定服務內容。最典型實例就是近年來各地紛紛建立起來的行政服務中心,地方服務型政府的面貌在行政服務中心得到全面展示。第一,表現為審批與服務的互動,在審批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整合審批。原來“碎片化”的政府部門的職能交叉、工作內容重疊現象,在服務大廳演化為相近科室歸并整合,原來審批流程中的“各自為政”演化為打通隔閡,建立跨窗口團隊,原來跑斷腿、磨破嘴的現象演化為在電子政務技術支撐下的一體化、扁平化管理。行政服務中心改進了服務程序,提升了政府服務的質量,推動了部門內部與部門之間的職能整合。第二,表現為審批公開化。行政服務中心貫徹服務行政的施政理念,采用先進的電子政務平臺、扁平化的政府組織結構和公開透明的辦事流程,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公開,服務過程全部在陽光下進行,其中內含著從官本位到民本位、權力本位到權利本位、政府本位到社會本位、管理本位到服務本位的轉變氣息,窗口內外沒有阻擋,窗口之間沒有阻礙,窗口人員和民眾“零距離”接觸,激發了民眾的參與與監督的熱情和積極性。概言之,行政服務中心旨在建構一個直接面向社會和公民、回應力更強、效率更高、服務更到位的政府,它從“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對政府的流程進行了再造和重組,充分體現了服務型政府的職能定位和價值訴求。
在優化政府服務路徑方面,各地以形成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這其中有基于眼前與長遠的考慮,也有基于效率與公平的考慮。眼前的考慮在于解決目前公共服務提供方法和形式上的具體問題,如權宜式治理、場景式治理、應急式治理等,具有應急性、時效性和短期性特點;長遠的考慮在于建立一套公共服務提供的長效機制,表現為一系列的法規或制度,主要涉及惠及范圍、提供方式、財政支持、服務標準以及定價、補貼、監管、評價等各個方面,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長效機制的建立有利于鞏固現有的公共服務形式和成果。效率的考慮在于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注重的是投入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公平的考慮主要在于擴大公共服務的范圍,使其更好地惠及所有社會群體,正如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所說:“把效率和經濟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是有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必須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理論支柱。”[13]這種公平既包括機會公平、制度公平、程序公平,也包括結果的公平。總之,服務型政府機制創新的路徑既要考慮到對當前問題的應急處理,也要著眼于構建一套穩定的長效機制,同時也要兼顧效率和公平,為此,可以采用“整體規劃—統籌協調—分步到位”的發展策略,從提升公共服務效能目標出發,分別對各個單一機制加以完善,充分發揮各個機制之間的相互促進與協調作用,實現服務型政府機制創新的協同推進。
三、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外在結構分析
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外在結構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和其他政治主體與社會主體的關系。這一結構內涵于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目的、動力、程序和邏輯進程中,涉及源與本的關系、服務主體與服務對象的關系、政府能力與實際困境的關系、政府與社會及公民人格健全的關系等。
第一,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目的:源與本的關系。這涉及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價值取向問題。美國政治家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指出,“構成一個社會或國家的人民是那個國家中一切權力的源泉”,“我不知道除了人民本身之外還有什么儲藏社會的根本權力的寶庫”[14]。服務型政府就是“以‘管理就是服務’為根本理念,以社會和大眾為主要導向,以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核心職能,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和諧發展為根本任務的現代政府”[15]。這就從基本內涵上框定了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價值取向“是在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地位不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追求,更直接的是對全能主義模式的批判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回歸”[16],最終實現“遵從民意要求、實現民意期盼”的目標。實踐表明,無論是民主、法治,還是憲政,抑或是效能型、法治型、責任型、有限型、參與型、節約型、前瞻型政府模式,服務型政府所倡導的所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核心指向必然是以人為本。因為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民,政府的發展為了人民,政府的建設依靠人民,建設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究竟是官本位還是民本位、政府本位還是社會本位、權力本位還是權利本位這三個問題的正確回答是管制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本質區別與分水嶺。很顯然,服務型政府強調的是公民本位、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的回歸,是對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的擯棄與糾正。
第二,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動力:服務主體與服務對象的關系。地方服務型政府的服務主體是各級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服務對象是社會組織與社會公眾。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成為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核心動力。地方政府作為公權力的使用者,必然要為公權力的所有者——公民——服務,但是這種服務決不能損害私權的行使,這是政府職能實施的邊界。[17]一旦跨越這一邊界就會造成權力過分集中和壟斷,就意味著政府是一個“管制政府”“無限政府”“全能政府”甚至會成為“保姆政府”“媽媽政府”,從而偏離政府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在地方服務型政府體制中,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務的唯一提供者,而變為服務規則的制定者以及公共服務的協調者、促進者與合作者,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從單一走向多元。服務型政府的本質是公民參與型的,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也需要廣大公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了解公民需要什么樣的服務、渴望得到什么樣的服務,也才能找到服務公民和社會的方式和路徑。可見,在服務型政府體制下,服務主體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系是基于對話基礎上的互動合作,其服務主體模式就是要建立起一種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公共服務的增量與優化。
第三,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進程:政府能力與實際困境的關系。在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進程中,會遭遇來自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困境,而提升地方政府的能力則是破解困境的唯一途徑,二者在實踐中表現為一種張力關系。政府能力是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所具有的能量,政府能力的強弱決定了政府職能的實現程度。建設服務型政府,不僅要轉變政府職能,更要提高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提升是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前提和保障。在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進程中,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價值定位不準確、整體推進方案不明晰等等,各地在探索具體實現形式上難免五花八門,由于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必然會遭遇來自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困境。如何化解困境、順利推進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內在地對政府能力提出了客觀要求。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社會結構轉型、體制轉換和機制轉軌的轉型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聚了大量的深層次社會矛盾和沖突,對地方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要著力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增強地方政府及其公務員的綜合素質和服務水平,提高地方政府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力和解決民眾實際問題的能力,構建一整套保證地方政府服務及時性和有效性的制度,為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保駕護航。
第四,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邏輯:多重關系的互動。服務型政府建設是當代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性目標,這就決定了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必須妥善處理好與政府職能轉變、公民社會發育、社會組織成長以及公民人格健全的關系,使之處于良性的互動狀態。一是與政府職能轉變的關系。政府職能是政府一切活動的邏輯起點與現實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必然要求和實現途徑,只有明確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確定政府職能的重心,才能順利推進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要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就應當把服務作為地方政府職能的核心,合理確定地方政府職能的范圍,推進地方政府從統治思維、控制思維轉向服務思維。戴維·奧斯本(David Osborne)等指出,“重新界定政府職能的合理適當范圍,要政府投入所有心力、資源于核心職能的發揮上,解除不必要的政務負擔”[18]。當前,地方政府的核心職能就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無論是社會管理還是公共服務,地方政府都應該合理確定職責權限,推動政府職能的歸位、正位和補位,增加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建立健全新型的公共服務體制及其運行機制,保證地方服務型政府的正確方向。二是與公民社會發育的關系。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走向文明和現代化的標志之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軟實力之所在,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有賴于一個壯大的、發育成熟的公民社會。羅爾斯(John Rawls)曾經指出,“調和規則與規則結構之間的不相稱問題,非社會自身力所能及,需要政府的主導和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才能達到動態均衡”[19]。概言之,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基礎。西方國家公民社會發達,政府與社會互動頻繁,形成“社會與政府唱對臺戲、政府不唱獨角戲”的格局,因此西方政府的改革總是回應社會需求,總是會伴隨著市場的發展而思考政府模式的邏輯變遷與范式轉換。我國的社會力量很薄弱,扮演的角色不很突出,政府仍然是社會的主角,甚至常常唱“獨角戲”。當然,“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據情況的不同,政府有時候需要比較深入地干預公民社會,有時候又必須從公民社會中退出來。”[20]因此要加快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同時加強社會的變革,實現其與政府的互動,在互動中促進社會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三是與社會組織成長的關系。各類社會組織是多元社會主體中的重要力量,是溝通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橋梁,它們與政府組織如果在互信共榮的基礎上緊密結合,將會大大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M.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指出,當前“我們正置身于一場全球性的‘結社革命’之中。歷史將證明,這場革命對20世紀后期世界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民族國家的興起對于19世紀后期世界的重要性”[21]。社會組織的內在功能,決定了任何一個服務型政府都必須有效吸納和整合社會組織的力量來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都要求善治,而善治的實質就是政府與公民的良好合作,但這種合作并不總是直接的,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中國的社會組織就是這樣一種中介。[22]社會組織能積極主動地承接地方政府的某些職能,公民可以借助社會組織來參與政府的某些決策,與政府達成共識;政府也可以通過社會組織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借助其橋梁作用,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公共服務的水平。四是與公民人格健全的關系。建設地方服務型政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健全人格的形成和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最終目標。反過來,現時代公民人格的健全也是地方服務型政府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23]因此,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必須把培育公民的獨立人格作為重要內容,應在服務型政府結構轉型、機制轉換和職能轉變的全過程中,注意培養公民“完整的人格意識”“獨立的行為能力”和“自由的社會關系”。這不僅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和法治原則是一致的,而且與服務型政府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理念是相符合的。在這樣的精神理念指引下,具有公民人格與身份的社會成員不再去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再局限于成為市場的主體,而是在此基礎上尋求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主體地位,并且在履行公民權利及承擔相應義務的同時,將自己的公民身份與社會和政治共同體相聯系,成為公民意識和公民文化的實際載體,從而大大推進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
四、地方服務型政府內外結構互動下的功能指向
結構功能主義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化的整體系統都存在一定的結構體系,而結構又決定或直接影響著該系統功能的發揮;結構處于協調狀態時,功能的協調也比較容易實現;結構一旦發生變化,就要求新的功能與之相適應。如前文所述,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即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外在結構即地方政府和其他政治主體與社會主體的關系,這二者共同構成了地方服務型政府的結構體系。這種結構體系決定和直接影響著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功能指向。
第一,地方服務型政府的主體功能和核心功能是向地方民眾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統治型政府模式下,政府代表的是統治階級利益,它將人民視為統治的對象,政府和人民處于對立狀態,政府對社會的管理主要表現為集權管理、“權治管理”和強制管理。在管理型政府模式下,地方政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表達和代表機構,其主要職能就是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在服務型政府模式下,“控制關系日漸式微”,地方政府堅持服務導向而非控制導向、公正導向而非效率導向、公民本位而非政府本位,堅持開放式行政而非封閉式行政,堅持德治和法治的有機結合。[24]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服務并沒有否定統治和管理,而是將服務貫穿于管理之中,在管理中實現服務。當前,地方服務型政府的核心職能就是為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具體體現為四個方面,即適應功能(地方政府對公民的有效回應和對社會發展前瞻性的敏銳把握)、達鵠功能(為社會和公民服務,為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保駕護航)、整合功能(整合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促進社會公平和公正的實現)、維模功能(廉潔文化和廉價文化即“雙廉”文化的塑造)。此外,也包括其他一些主要職能,如維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保護有序市場競爭、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等。
第二,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功能是在其內外結構的互動中實現的。在地方服務型政府結構中,內在結構是外在結構的基礎和支撐,為外在結構服務;外在結構是內在結構的延伸,為內在結構提供保障;二者以政府職能(功能)作為橋梁而彼此聯系、相互依存,通過良性的互動促進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功能的實現。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結構包括體制和機制兩大方面:行政體制是指行政權力結構之間的關系狀態,主要解決的是服務型政府為誰服務、服務的限度及效能問題,行政體制的運作依賴行政機制的完善;行政機制是指行政體制運行中的形式、流程、程序與技術等要素,解決的是服務型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務問題。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外在結構表現為外部四個方面的運作:源與本的關系屬于價值判斷,關注的是權力的來源與終極目標,是整個外在結構完善的起點和歸宿;服務主體和服務對象的關系屬于結構判斷,涉及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關注的是具體為誰服務的問題;政府能力與實際困境的關系屬于效能判斷,涉及服務的限度和幅度,關注的是政府到底在多大范圍內服務,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等問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多重關系交織屬于邏輯判斷,關注的是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協同邏輯。上述四個方面,面對的是在機制體制完善的基礎上,地方服務型政府如何運作的問題。它們之間的關系協調,可以為內部結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使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在政府職能轉變這一主題的指引下更好地達成一致。
第三,地方服務型政府功能的實現需要堅持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公開性的價值理念。公共性是指政府服務的內容是配置公共資源和提供公共產品,政府服務的手段是運用公共權威,政府服務的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政府服務的靈魂是承擔公共責任,并強調政府服務的公眾性和社會性。中國的孔子、范仲淹、王夫之、孫中山以及西方的洛克、盧梭、韋伯、哈貝馬斯等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政府的公共性,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杰斐遜、漢密爾頓、潘恩、麥迪遜等將政府的公共性從理念變為實踐,而優化公共職能、重塑公共制度、培育公共精神、構建整體性政府是當前強化地方服務型政府公共性的基本路徑。公平性體現在機會公平(社會中的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宗教信仰、能力高低、文化程度,都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平的發展機會,并以公正的司法體制保證上述平等的實現)、程序正義(每位公民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都能得到尊重和體現,保護弱勢群體利益,應當構成政府服務公平的起碼要求。政府應保證每位公民都能夠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結果公正(要有效地增進和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使每一個人都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獲得自己參與社會活動后應得的待遇、分配等)三個方面。公益性是指政府只能為公民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假借公利之名為個人謀取私利;政府行為不能以營利為目的,而應該以表現社會道德、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等為其社會角色。因此,公共服務中的“以權謀私”“假公濟私”等不良行為都是違背公益性要求的不良行政行為,應該得到有效的制度矯正,以集中力量為人民提供公平與公正的公共服務。公開性就是落實公民的知情權,這就要求政府將公共服務的依據、內容、過程、時限、結果和責任向社會公布,讓公民知曉。瑞典的《新聞報道自由法》(1776年)、法國的《人權宣言》(1789年)、丹麥的《信息公開法》(1964年)、美國的《情報自由法》(1967年)和《陽光下的政府法》(1976年)、加拿大的《信息獲取法》(1985年)等都作出規定,要求政府機關的決策、各種委員會的決議,除了法律規定需要保密的以外,必須向社會公開。我國2008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從法律層面上對政務公開的內容、范圍、形式、程序、答復時限和責任追究等做了詳細具體的規定。這就是說,公開性是政府工作的靈魂,是維護公眾利益的必要前提,因為一個透明的政府才能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只有被時刻監督著的政府才能糾正公共服務的隨意性。
參考文獻:
[1]沈榮華、鹿斌.我國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構與調整[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3).
[2][美]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上)[M].邱澤奇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36-37.
[3]武小龍、劉祖云.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邏輯[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4]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6.
[5]馬凱.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5).
[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J].求是,2013(2).
[7]郝正飛、文宏.創新行政管理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13(4).
[8]龔常、曾維和等.我國大部制改革述評[J].政治學研究,2008(3).
[9]李克強: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J].先鋒隊,2012(35).
[10]沈榮華、王榮慶.從機制到體制:地方政府創新邏輯——以行政服務中心為例[J].行政論壇,2012(4).
[11][美]詹姆斯·Q.威爾遜.美國官僚政治[M].張海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430.
[12][法]皮埃爾·卡藍默等.破碎的民主——試論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56.
[13][美]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張成福、劉霞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92.
[14][美]托馬斯·杰斐遜.杰斐遜選集[M].朱曾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60.
[15]周定財.服務型政府的基本內涵及其路徑選擇[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4).
[16]沈榮華、鐘偉軍.中國地方政府體制創新路徑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89.
[17]沈榮華、楊國棟.論“一站式”服務方式與行政體制改革[J].中國行政管理,2006(10).
[18][美]戴維·奧斯本等.擯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M].譚功榮、劉霞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27.
[19][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216.
[20][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M].鄭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3.
[21][美]萊斯特·M.薩拉蒙.非營利部門的崛起[J].譚靜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3).
[2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49.
[23]萬俊人."和諧社會"及其道德基礎[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1).
[24]張康之.公共行政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6-20.
(責任編輯矯海霞)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Zhou Dingcai
Abstract:At present,China's service-oriented loc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has experienced its exploration stage,construction stage and entered the stage of adjustment gradually. The research of the structure function has a great fit and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local service government. Considering the system,mechanism and logic process from the structure is of great advan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loca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ncludes the macro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of mechanism;the external structure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other political subject and social subject. The main function of loca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public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the local people,it will be realiz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nject the value idea of public,fairness,public welfare and public in practice.
Keywords:Loca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Structural Functionalism;Administration of Politics;Internal Structure;External Structure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地方服務型政府建構路徑與對策研究”(09&ZD063)和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層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協同治理研究”(13CZZ038)的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7
作者簡介:周定財 男(1979-)江蘇師范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D6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176(2016)03-0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