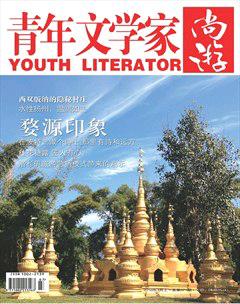桂花糖露 匠人有心
唐七

桂花糖露的清甜里帶著一絲咸,初嘗只覺不真切,如同被薄紗覆著的美人臉。久了之后,卻發現即使閉上眼,腦中也即刻能勾勒出一個清晰的輪廓來。而細細薄紗便成了柔和的光,時間愈久,愈叫人覺出那份美中藏著的含蓄與匠人心意來。
《影梅庵憶語》里曾提及董小宛制作的一種“鮮花糖露”:釀飴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時采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
若谷說,他最初從孟暉所著的《唇間的美色》里讀到這段引述時,幾乎有“恍然大悟”感。彼時,那兩大桶“桂花醬”已經在他的工作室里擺了近一年的時間。
“前年和朋友去杭州玩的時候,在滿覺隴附近偶然發現了這種用來制作糖桂花的半成品原料。覺得是好東西,就買了兩桶。一直想著要將它再加工做成糖桂花,但也沒想好具體到底要怎么弄。”
制作這桂花醬,從頭年的四、五月份采摘青梅,去核搗碎腌制做成“梅子醬”開始,到入秋桂花滿開,清洗腌制,前前后后至少要花上一年的時間。雖然對于大自然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四季的輪回,但對于如今的食品行業來說,卻是難得的人工及耐心。
若谷最初買下的那兩大桶,正是經過這層層繁復工序之后的桂花醬。不過,這還僅僅是制作糖桂花的半成品原料。用他的話說,是糖桂花的“前生”。
以前的糖桂花作坊,每家都有不同的制作方式,雖說大體都是漂洗、去鹽、晾曬、拌糖、舂搗等步驟,但其中細節的把控卻可以讓成品的滋味千差萬別。
“如今即便是杭州當地的糖桂花作坊,也已不怎么再做傳統手工的糖桂花了,而是直接將半成品的花醬賣給一些大工廠作為食品加工的原料。因為工序太復雜辛苦了,也沒什么利潤,產量也少。”
不過這些對若谷來說倒算不得什么難事。對于這種考驗耐心和意念的手工活,他自小便充滿了興趣。淘寶店在賣“桂花糖露”之前,他的主打產品是手工精油香皂。從2008年偶然開始嘗試肥皂制作,到2009年辭職轉行,完全投入自己“作坊式”的工作室運營中,他似乎也沒有過什么“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種聽起來很糾結彷徨的抉擇過程。
“就是喜歡。喜歡做手工的事情,喜歡安靜的狀態。做肥皂這個事情的過程讓我覺得喜悅。所以就一直這么做了下來。”說這話的時候,若谷一臉淡定自如,就好像其他這個年紀的人在抱怨房子貴掙錢難生活無趣時一樣理所當然。
去年五月的時候,若谷的工作室有了第一個員工,也大約是那個時候,他讀到了那段“釀飴為露,和以鹽梅”的典故。
董美人的手制花露僅僅用了八個字,便將彼時那種細膩優雅的日常滋味升華成了傳奇。這不僅成了若谷最終將自己手制的糖桂花命名為“桂花糖露”的由來,也激發了他想要將這種“古老的日常滋味”還原出來的念想。
他開始頻繁地往來于杭州和上海,頻繁地在工作室那臺小小的電磁爐上做各種嘗試。兩桶靜置了許久的桂花醬就好像是個深邃的秘密通道,連接著古和今,也連接著他和那些傳統的制醬人。
“其實那些制醬人最初對外人是抱著警覺的拒絕態度的。對于他們來說,所謂的‘傳承概念相當模糊。做了60多年桂花醬的老人,雖說如今把作坊交給了女兒打理,也不過是種討生活的方式罷了。”
邊聊天,若谷邊打開電磁爐,架起鍋、燒上水、,開始為我們演示他制作糖桂花的過程。半成品的桂花醬在經過了又一次的手工挑揀之后,被放入加了糖的鍋中進行“清洗”。除了去掉過重的咸味外,其實這也是將“桂花”從生煮到熟的方式。洗過的桂花醬濾出后,需要再煮一鍋濃厚的飴糖,將桂花醬放入,緩緩攪拌融合,待冷卻后裝瓶,才最終得以完成。
“有一次做的有些咸了,是因為那天剛好糖用完了。”他呵呵笑。“工作室的伙伴讓我記錄下每次加糖的量,忙的時候可以依樣操作。不過怎么說呢,這種東西,還是要靠每個步驟一次次嘗,才能調整到最恰當的口感。與其說是體現手工的產品,倒不如說它是反映應‘人的產品。”
他站在桌前,慢慢攪動著木勺,看起來自如又享受。工作室里開始慢慢充滿了熬煮桂花的香氣,糖的甜香和梅子的咸香也越來越濃了,空氣變得稠了一點,似乎因此而拖住了時間的飛速流動。
“我今年已經跟老師傅定了兩缸半成品的醬,說好了要金桂的。其實桂花醬要放隔年,充分發酵,味道才好。”賣花醬的老人已經和他熟絡,不再有最初的隔閡。買賣之外的嘮嗑閑扯,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還原糖桂花的滋味從“目的”的層面上漸漸隱去了,變成了一種古典的相處方式。“這東西的確沒辦法量產,但其實這也正是它美好的地方。就像我只會在秋天的時候制作‘桂花糖露,它本身應該是時令性的東西。有等待、有念想,才會有珍惜。”
最后完成的糖桂花,若谷用一枚朱紅色的封臘封存在透亮的玻璃瓶子里。所有青梅的酸、鹽鹵的咸、砂糖的甜、桂花的香,此時都隱匿在了他雙手捧著的那方天地里。
我從鍋里裝瓶剩下的糖桂花里舀出一小勺來嘗,清甜里帶著一絲咸,綿軟里透出股利如劍芒的勁道,沿著舌頭一路鋪滿整個味蕾,又漸漸收攏在喉嚨里,留下微妙極了的回味。就好像是那條一路走來,亦將一路走下去的匠人之路,個中滋味,也或許只有親歷者才能細細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