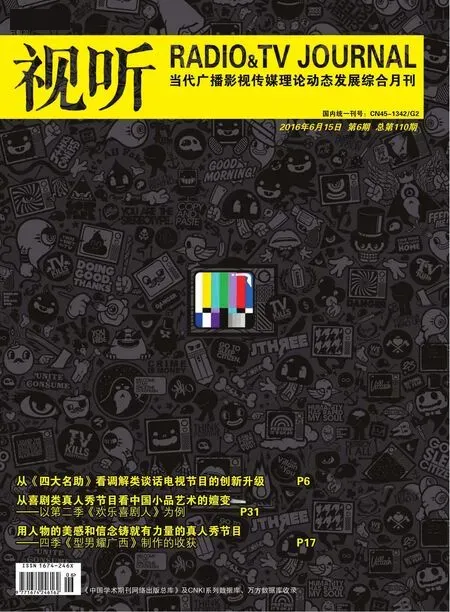試論網絡流行語在當代話語體制下的嬗變
□趙藝玲
?
試論網絡流行語在當代話語體制下的嬗變
□趙藝玲
摘要:網絡流行語以互聯(lián)網為傳播載體,是網絡世界中流行的語言話語體系。從最初的娛樂惡搞到時下對公共事件的暗諷和批判,網民對網絡流行語的生產,無不是一個流行替代另一個流行。作為一種草根敘事藝術,它明顯帶有娛樂性、調侃性、批判性以及狂歡性。本文闡釋了網絡流行語的基本分類和生產方式,探析其背后隱藏的文化意義以及可能存在的隱性收編。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類型分析;隱性收編
在互聯(lián)網日益普及的今天,中國網民已成為網絡流行語的生產主體和傳播主體。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說,“技術的本質不是技術性的”。①網絡推動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媒介奇觀。對于網民而言,尤其是草根階層,網絡已不僅僅是一種能夠獲取知識和信息、交際交流、網購的技術平臺,更是一個表達自我、爭取話語的空間場域。網民憑借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對公共議題圍觀討論,對權力話語進行抵抗,對社會現(xiàn)實針砭批判。網絡空間不是一言堂,它具有開放性、匿名性,激發(fā)了網民的表達欲望,進而為網絡流行語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溫床。
一、網絡流行語發(fā)展概況
從2007年的“很好很強大”、2008年的“打醬油”、2009年的“躲貓貓”,到2010年的“我爸是李剛”,再到2015年流行的各種網絡文體,譬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并卵”“顏值”“約嗎”“我想靜靜”“小鮮肉”等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語境中被賦予新的含義。網絡上似乎每天都會出現(xiàn)新的流行語或文體,一個流行追趕著另一個流行,網民們樂此不疲。網絡流行語的產生已經蔚然成體系,極具工業(yè)化意味,尤其是一些網絡文體,常常以一個文本為藍本,網民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般地仿造或衍生出許多版本。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或多或少地表現(xiàn)出了“全民狂歡性”,但是,“急促的底層呼吸、逼真的公共心跳、大膽的社會反思,構成了網絡造句行為最基本的旋律和節(jié)奏。”②
網絡流行語之所以興起,主要還是因為權力話語參與到了“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爭奪中。草根階層的話語空間愈加逼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將這一過程形象地描述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他的“公共領域”意指“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并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③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一場尋求“替代性話語”的起義隨之爆發(fā),勢如破竹,高歌猛進,以此來抵抗權力話語的同化或殖民,很快便在這個場域中爭得一席之地。
網絡流行語作為一種公共修辭的草根敘事藝術,所表達的意義已經大大超出了詞語本身的字面含義。從符號學的角度看,它是網民賦予了新的“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它是這個時代特有的文化景觀,是一場見證公共圍觀力量的修辭運動。它的興起,標志著公民意識的覺醒,方興未艾。
二、網絡流行語的基本分類和生產方式
“網絡流行語是網絡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不同的類型和生產機制,通過對它們的分析,能夠透視出當前中國政治和文化的若干問題。”④它之所以能有“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功能,原因在于無論它賴以存在的技術載體是什么,其本質還是語言。社會作為語言的滋生地,為語言的形成、擴展及豐富提供了養(yǎng)料;而語言作為一個表現(xiàn)手段,能夠對作為個體的人的思想、情感、交流以及對作為集體的社會的現(xiàn)象、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進程進行描述。語言和社會的關系是辯證的,對立統(tǒng)一的——它們相互依賴、相互推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變化。
按照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視角來劃分,網絡流行語大體可以分為全民狂歡娛樂型、社會現(xiàn)實批判型、公共議題指向型。需要加以強調的是,無論哪種類型,就其作為語言、作為符號的存在意義而言,它都是建立在“符號學”基礎上。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發(fā)現(xiàn),“符號本身是一個自足的微型結構,它由兩部分構成: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號的形式,表現(xiàn)為一種文字、聲音或圖像,這特定的文字、聲音、圖像能夠引發(fā)某種概念的聯(lián)想。所指則是那個被聯(lián)想到的具體事物。”⑤
(一)全民狂歡娛樂型
此類網絡流行語的關鍵詞是“狂歡”,行為主體是“全民”(這里主要指網民)。狂歡的目的是“娛樂”。蘇聯(lián)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巴赫金(M.M.Bakhtin)曾提出三種民間狂歡形式:“(1)儀式化奇觀;(2)喜劇式的語言作品——倒裝、戲仿、滑稽模仿、羞辱、褻瀆、喜劇式的加冕或廢黜;(3)各種類型的粗言俚語——罵人話、指天賭咒、發(fā)誓、民間的褒貶詩等。”⑥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全民狂歡娛樂型的網絡流行語中找到上述三種形式的影子,比如“沙發(fā)”表示第一個回帖的人,是“so fast囧”的音譯;“”被用來代表“郁悶、悲傷和無奈”,一經誕生便成為網絡聊天中使用最頻繁的字之一,被稱為“21世紀最流行的一個漢字”。
網民生產這類流行語,完全是出于娛樂和無厘頭式的惡搞,這也符合早期的網絡流行語的特征,無關政治,無關經濟,僅僅是草根階層的一種自娛自樂的話語表達,體現(xiàn)了網民的智慧與幽默,同時具有很強的流變性。也許今天流行“我也是醉了”,明天就會流行“寶寶心里苦呀,就是不說話”……在網絡中,它的傳播速度非常驚人,但是消退速度也很快。這類流行語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還體現(xiàn)了草根文化頑強的生命力。從早期草根階層“手工作坊式”的自由生產,到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商業(yè)力量介入和收編,生產這類網絡流行語的主力軍依舊是源頭分散、基數(shù)龐大、有娛樂潛質的草根階層。
第二,對立認同對立認同是基于雙方共同的對立面而達成的彼此認同。這個對立面可以是人、物或者生存環(huán)境等,這體現(xiàn)了伯克不受古典修辭學的束縛,將新修辭學與人的生存環(huán)境的哲學思考相聯(lián)系的超前思維。例如,兩個不同發(fā)展路線的國家,面對共同的對立面時,原本彼此關系生疏的雙方超越發(fā)展路線的分歧,達成共謀發(fā)展的合作認同。對立認同中的對立關系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中,這就要求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斷對周圍的環(huán)境審時度勢后做出認知判斷,再采取恰當?shù)男袆印?/p>
網民本著娛樂的態(tài)度,以“語言省力原則”為前提,借助象形、諧音、比喻等技術手段造字、造詞,或者將俗語、諺語或者廣告語中的個別句子成分進行替換,完成對網絡流行語的生產。就其內涵而言,技術含量很低,加之內容沒有特定的指向性,流行范圍極廣,更新速度極快。
(二)社會現(xiàn)實批判型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這是北大副校長吳志攀早前發(fā)布的一條微博,將矛頭直指由于接二連三的“彭宇案”而導致社會道德與良知缺失的社會現(xiàn)實,全社會對此陷入了反思和批判。網民們也發(fā)起了網絡造句運動,上百所大學結合自身“優(yōu)勢”對吳志攀的微博進行模仿和改編,規(guī)模空前,史無前例。這一網絡文體被人們稱之為“校長撐腰體”。
社會現(xiàn)實批判型網絡流行語旨在對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批判,以期完成對公眾道德缺失、良知泯滅、價值觀錯位等問題的矯正。除了對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批判外,社會現(xiàn)實批判型網絡流行語還對物質世界層面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調侃。最典型的莫過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一系列網絡流行語,黑色幽默中帶著對社會現(xiàn)實的感慨,集體調侃背后則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個中滋味,惟百姓知。
(三)公共議題指向型
“當下中國正處于轉型期,危及公共利益的社會事件頻頻發(fā)生,而這些事件的根源直指當前中國法律體系方面的制度性缺陷。”⑦毋庸置疑,公共議題關系到公共利益,它能夠促進民主和法治進程,保障公共利益,監(jiān)督公權力,規(guī)范社會秩序。盡管目前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公共議題屈指可數(shù),但是借助網絡力量,一個又一個公共議題引發(fā)的圍觀卻與日俱增。網絡流行語的流變性和公共議題的頻發(fā)導致一個圍觀總是驅趕著另一個圍觀,不免令人心生憂慮。然而,誰又能肯定圍觀就不是一種力量呢?圍觀是公民意識覺醒的表現(xiàn),是走向民主社會的一小步,公眾對公共議題的圍觀或關注,為公權力制造了輿論壓力,迫使其不得不考慮制度層面、法律層面的改進。
公共議題指向型網絡流行語暗含著一種社會動員力量,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培養(yǎng)著社會公眾對公共議題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它的流行背后涌動著公眾對于權力話語的不信任,以及對公權力的焦慮。“權力存在于話語、制度、客體以及身份的創(chuàng)造之中。”⑧權力(power)和話語(discourse)總是相伴隨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就指出——沒有話語就不存在權力關系,話語以權力關系為前提,并建構著權力關系。權力話語與草根話語是“二元對立關系”,二者對“公共空間”的爭奪導致了在一些公共議題面前,官與民在話語層面的對峙。“躲貓貓”“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網民對這類網絡流行語的生產都指向了公共議題,而公共議題又將矛頭對準了制度和法律層面的不健全、不合理。歸根到底,這是為了改造我們的社會,使之朝著民主、自由、法治的目標不斷邁進,讓公眾感受到希望,而不是活在對公權力的恐懼和焦慮當中。
三、網絡流行語的隱性收編
網絡流行語還存在被隱性收編的可能,那就是政治收編,表現(xiàn)為一種官方認可。政治收編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涉及公共議題的網絡流行語。比如在2009年的“躲貓貓”事件中,面對公眾的質疑,云南省委專門召開了協(xié)調會,提出讓網民組成民間調查團參與調查,并發(fā)布了名為《關于征集網民和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參與調查“躲貓貓”輿論事件真相的公告》。顯然官方已經采用了網民所建構的“躲貓貓”一詞,并將其納入自己的話語體系,一方面是對“躲貓貓”一詞的認可,同時也是隱性收編。
四、結語
不同的媒介時代具有不同的媒介語言,網絡流行語的特點與網絡的即時性、海量性、互動性、共享性、多媒體性等技術特性密切相關,它雜糅并蓄、博采眾長,同時又極具個性化。它是網絡時代特有的語言類型,游走于娛樂、文化、政治、商業(yè)之間,難以找到合適的歸屬,難免會陷入文化困境。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會走向消亡,恰恰相反,它的生存空間是巨大的。
在公共議題面前,如何在權力話語和草根話語之間找到一種溝通協(xié)商的方式,顯得尤為重要。話語對抗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反而會激化矛盾。網絡流行語是草根階層參與公共議題的方式,權力話語不應該只是將其看成草根階層的娛樂方式和話語反抗,應該以大度的姿態(tài),去接納和融合,讓公眾實實在在地參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從而推動社會朝著民主化、公正化、透明化的方向發(fā)展。
注釋:
①[匈]阿格尼斯·赫勒著,李瑞華譯.現(xiàn)代性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②劉濤.網絡造句:公共議題構造的社會動員與公共修辭藝術[J].江淮論壇,2012(1):186-189.
③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91.
④劉國強,袁光鋒.論網絡流行語的生產機制——以“躲貓貓”事件為例[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9 (5):54-56.
⑤陳龍.傳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23.
⑥陳龍.傳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46.
⑦劉濤.環(huán)境傳播·話語、修辭與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49.
⑧[英]阿雷恩·鮑爾溫德著,陶東風譯.文化研究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7.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影視與傳媒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