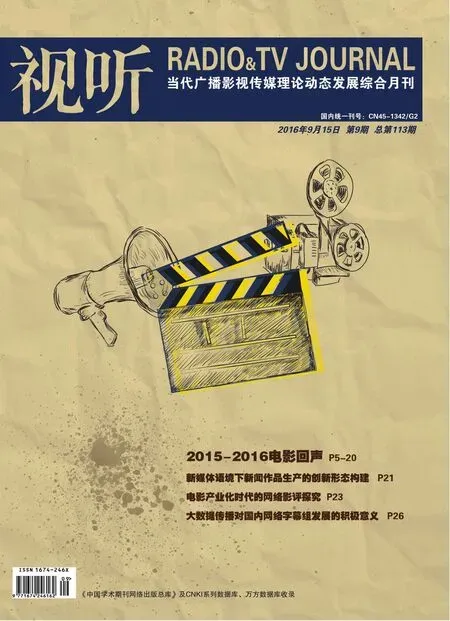臺灣青春片的銀幕書寫
——以《我的少女時代》為代表的青春影像表達
□蔡瑩瑩
臺灣青春片的銀幕書寫
——以《我的少女時代》為代表的青春影像表達
□蔡瑩瑩
2015年,小制作的《我的少女時代》化身“黑馬”,刷新臺灣地區票房記錄,在大陸也斬獲3.32億的票房。在或唯美或哀傷的臺灣青春片中,不乏導演對影像、流行音樂的運用、德呂克“上鏡頭性”的實踐以及對臺灣本土化的表達。當大陸導演還在用大量的光影來彌補劇情的缺憾時,臺灣導演正運用逐漸成熟的臺式青春藝術風格娓娓道來一部部俗套卻耐看的臺灣青春片。
我的少女時代;上鏡頭性;青春片;臺灣電影
一、獨樹一幟的臺灣青春電影時代
臺灣著名導演楊德昌曾說,臺灣只有兩類電影——青春片和非青春片。從《海角七號》到如今的《我的少女時代》,無疑都印證了這個觀點。從初具雛形到如今的日漸成熟,臺灣青春片都秉持著一如既往的風格,涵蓋了所有青春片必備的清新元素,節奏舒緩干凈,建立了獨樹一幟的臺灣青春片品牌。一直以來,臺灣電影對青春題材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迷戀。早在20世紀70年代,風靡一時的瓊瑤愛情文藝片就營造出各種形形色色男女之間烏托邦式的愛情故事。20世紀八十年代,侯孝賢的《風柜來的人》(1983)、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都是青春成長題材。導演試圖用這些慘淡的青春來揭露社會,表達自我的反思。
然而電影作為一種無形的社會力量,必須更加關注青年人的成長,擔負起傳播正能量的重任。因此,進入新世紀之后,新生代的臺灣導演們雖然繼承了青春題材的傳統,但在敘事策略、表現手法和情感路線上卻有了很大的突破。學者李道新將臺灣年輕導演電影的敘事策略和精神文化特質歸納為“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臺灣青春片通常是以某種“缺失”為故事的起點,既包括身體、父母的缺失,也涉及情感和生存空間的缺失。對于這種缺失,主人公或努力,或掙扎,或成功,或失敗。但銀幕外的觀眾不論怎樣努力或掙扎,最終“缺失”仍然得不到治愈或者補償,始終“缺席”,無法“抵擋在場”。因此這樣令人感同身受的“青春”,再輔以俊男美女的搭配、懵懂的愛情、純潔的友情等更能引發觀影者的共鳴,符合年輕化觀眾觀影的味蕾。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的主創們更是深諳其道。青春是什么,就是這些無關痛癢卻永生懷戀的林林總總。《我的少女時代》講述的是神經大條且長相平凡的女主角林真心,喜歡著一如偶像劇中溫文爾雅的風云人物歐陽非凡,而徐太宇身為學校頭號痞子,則一心想要追求冷艷的校花陶敏敏。結果陰差陽錯,林真心和徐太宇彼此相愛卻又彼此錯過。電影中,他們的青春,一身是膽、不自量力。譬如女主角林真心為了力挺男主角沒有考試作弊,在劇中與偏執的教導主任據理力爭:“分數和校規都不能定義我們,成績好的學生也會犯錯,曾經犯錯的有一天也會變好,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是誰,只有我們能決定自己的樣子。”每個人所經歷的青春都有所不同,他們或許如女主角一樣果敢,又或者想成為女主角那樣的人。正因為如此,大多數觀眾都喜歡能勾起自身回憶的青春片。
二、臺灣青春影像中的“上鏡頭性”
雖然《我的少女時代》這場關于少女初戀的青春紀實在劇情的走向上并沒有逃脫傳統意義上的臺式偶像劇,但它仍舊打動了無數影迷,刷新了臺灣票房記錄,在大陸也斬獲3.32億的票房。這說明,特效、巨星、大制造、炒作營銷并不是當今獲得高票房、高口碑的不二法門,小投資的“小清新”影像書寫也能殺出一條血路。
臺灣青春類型片的影像特點在于對鏡頭構圖、景別、用光、剪輯、節奏、演員等綜合方面有著高質量、高水準的要求,形成自成一脈的臺式“小清新”風格。這種風格的表達和體現與法國先鋒派電影理論家路易·德呂克在《上鏡頭性》一文中提出的對電影藝術特性的稱謂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上鏡頭性”的理論內涵是:電影藝術應當在自然和現實生活中發現適宜用光學透鏡表現的形象和景物,強調樸實無華,提倡使用自然光效、焦點發虛等表現手段營造電影藝術獨有的詩意,而且認為惟有處于運動中的視覺形象才最具有“上鏡頭性”。作為臺灣票房最高記錄的保持者和良好口碑的擁有者,《我的少女時代》將“上鏡頭性”所提及的“裝置”“照明”“節奏”“假面”等元素經過臺灣本土化的加工,很好地展示給了觀眾。
(一)“裝置”:臺灣地域特色的展現與表達
德呂克提出的“裝置”元素主要包括自然景和布景、鏡頭構圖和各種景別的運用。首先是自然景和布景。以《我的少女時代》為代表的臺灣青春片,都不可避免地運用到了校園這個場景。例如《我的少女時代》大部分的場景都是在臺灣新竹高商拍攝完成。臺灣青春片將臺灣一座又一座的學校搬上銀幕,《我的少女時代》的拍攝地新竹高商雖然遠不及《不能說的秘密》中淡江中學景色優美富有傳奇色彩,卻更接近我們這代人的記憶。籃球場中歐陽非凡揮汗如雨,帥氣盡顯;跑道上徐太宇被罰跑時的筋疲力盡。這兩個運動場地的選擇最為平凡卻又最能勾人回憶,吸人眼球。
(二)“節奏”:個性的視聽表達
德呂克指出,“節奏”首先指比例平衡,是在“裝置”“照明”和“假面”各元素之間起著平衡聯系和邏輯統一作用的、最具有感染力的“卓越技術現象”和創作者的激情和智慧的產物。所以,電影的節奏包含了多種元素的共同作用。亞歷山大·阿爾諾也提出,電影是一種畫面語言,它有自己的單詞、名型、修辭、語型變化、省略、規律和語法。這種語言包括鏡頭、鏡頭調度和聲畫關系。導演通過鏡頭間的合理調動和恰當的音樂使用技巧向觀影者傳達信息。
縱觀臺灣近年來的青春片,那些在新電影時期令導演們引以為傲的長鏡頭、畫面留白和象征主義被快節奏剪輯、視覺特效甚至夸張的惡搞所取代。可以發現,當代臺灣電影人的影像風格深受當今流行文化的影響。在《我的少女時代》中不乏有動畫和視覺特效元素的加入。女主角林真心在收到“幸運信”時的心理活動過程,就運用了動畫和視覺特效元素。聲音理應屬于“節奏”的一部分,在電影中作為一個獨立的形象而存在。聲音讓電影更加貼近真實、增添藝術感染力。
眾所周知,人聲、音樂、音效是電影的三大構成元素。《我的少女時代》自帶濃郁的臺灣本土氣息,電影中的人物造型、場景環境、文化觀念都透露著濃濃的臺灣味道。且因為電影的轟動而聞名的景點和音樂也不勝枚舉,青春電影之門才剛剛打開,有待創造出更多的優秀作品。田馥甄演唱的《小幸運》作為主題曲和插曲,在電影上映前,就未播先熱,占據了各大音樂排行榜的榜首。還有其中用得恰到好處的《失戀陣線聯盟》(草蜢樂隊)、《忘情水》(劉德華)等都與人物的經歷十分契合,歌詞大意也與電影的主題相關聯,與劇中人物的心情相對應。
(三)“照明”:光與影的塑造
電影是一種光影的藝術,光影在青春片電影中往往占有很多的比例。在《我的少女時代》中,導演陳玉珊也深諳光線的重要性,熟練玩轉光影的變化技巧,用光線賦予平凡的畫面以新的靈魂,增添了電影的可看性和唯美感。光線是視聽語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能渲染情感,帶動觀眾進入電影世界。光線除了為劇中場景提供基本的照明功能之外,還可以通過光影的變化賦予畫面特定的含義。《我的少女時代》中,有一場男主角徐太宇教女主角林真心溜冰的夜戲,影調偏暖。一開始依靠的光源來自于路燈,昏暗的街燈總是給人以無限的遐想。隨后將公園溜冰場燈光打開。一顆顆彩燈亮起,影子被拉長,簌簌的燈光透露著浪漫的氣息。忽明忽暗的光影變化詮釋人物的愛情。當女主角林真心從蓬蓬頭變成清新的齊耳短發時,柔和的自然光形成反差對比的強光,使畫面產生曝光過度的效果。炫目刺眼的強光給人一種虛幻不真實的感覺,同時又很夢幻,烘托出了女主角的華麗轉身,展現其青春可人的形象。
臺灣青春片對光影的運用崇尚自然清新,而中國內地的大部分青春片都有一個弊病,太過于夸大光的用處,每每在表達青春的記憶時,總是大幅度地利用白光,產生過度爆光的效果,來彌補一些故事性和演技的缺失。過分用光影堆積,導致電影少了真實生活的質感,更有甚者讓人覺得是在看音樂MV的感覺。事實證明,太過依賴于光影,反而適得其反,合理用光,才是正道。
(四)“假面”:“小清新”人物
臺灣的新青春電影大多有著簡單而又清晰的故事發展主線,情節自然流暢。正如麥茨在對于影院機制和觀影心理的討論中提到的,觀影的快感在于銀幕充當自我之幕,隨時滿足自戀的觀看。他們會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中的同班同學,也會是《我的少女時代》中犯花癡的少男少女。在這些人物塑造中,臺灣青春片的慣用手法是將人物個性中那些過于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部分省去,以簡約的鏡頭切換一帶而過,加快敘事節奏的同時緩解沖突,將“小清新”的風格貫徹始終。在這個小小的“青春”世界中,在留下最純粹的最干凈的青春印記的同時,也為觀眾帶來性格鮮明的人物群像。并且這類生活的影像敘述是自然隨意而不突兀的,不時出現的一些幽默的元素和抒情的畫面增強了影片的娛樂效果。此外,多角關系也是青春電影一大特點,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用入微的細節生動地刻畫了四個人說不清道不明的微妙關系,每個人都牽動著劇中其他三人和觀眾的心情。
臺灣地區對于“造星”有自己的秘訣。一部電影要貫徹自己的“小清新”風格,選取的演員也必須自帶“小清新”的標準。而臺灣青春片“小清新”風格的形成與青春片導演啟用的演員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縱觀《我的少女時代》演員的選取,無論是男主角王大陸,或者是女主角宋樺蕓,都是新生代90后的演員,在出演該電影前鮮有作品。也許正是這種“初出茅廬”的面孔,對比于巨星閃耀的明星大咖更有代入感,從而縮小了觀影“距離”。在演員配置上,除了有臺灣偶像劇中的一些“黃金面孔”,也有一些具有票房號召力的偶像明星的加入,比如陳喬恩、言承旭和劉德華等明星。他們的加入使得影片的表演具有更強的觀賞性。與此同時,臺灣青春片也成就了片中的演員。從陳柏霖和柯震東之類的“小清新”明星,到如今《我的少女時代》中的王大陸,他們都借助臺灣青春片的東風,順利地完成了他們銀幕形象和身份的定位,同時也豐富了臺灣青春片的文化內涵。
三、結語
青春電影,長期以來都是屬于電影類型劃分的一個較為邊緣化的類型。從《海角七號》到《我的少女時代》,每一部臺灣青春片都塑造了不同文化和身份背景下的年輕一代,青澀的愛和躁動的青春使觀眾感動。臺灣青春電影在電影美學上的表達,可謂是逐漸有了自己的特色。那些富有意味的鏡頭語言、別出心裁的光影變化、恰到好處的音樂使用和形象精辟的人物對白,使一部部臺灣青春電影都擁有了獨特的印記。現如今,臺灣新生代電影人正在用臺灣青春電影這張名片打開華語電影市場。反觀大陸的青春片,風格不一,層次參差不齊,票房高口碑但質量卻不佳。如何運用好鏡頭的語言、光影的表達,結合好自己的本土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不是一味地模仿,是大陸青春片創作者亟需反思的問題。
1.李道新.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2009年臺灣電影的情感訴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質[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0 (1).
2.陳娟.臺灣新青春電影:類型的深化與影像構建[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4(3).
3.吳麗芬.“海角派青春電影”對臺灣本土文化生態的救贖——以《海角七號》為例[J].東南傳播,2009(5).
4.鄭逸歡.21世紀青春電影的電影美學比較研究[J].電影文學,2014(12).
5.韓焜.臺灣電影青春記憶[J].世界電影之窗,2009(10).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