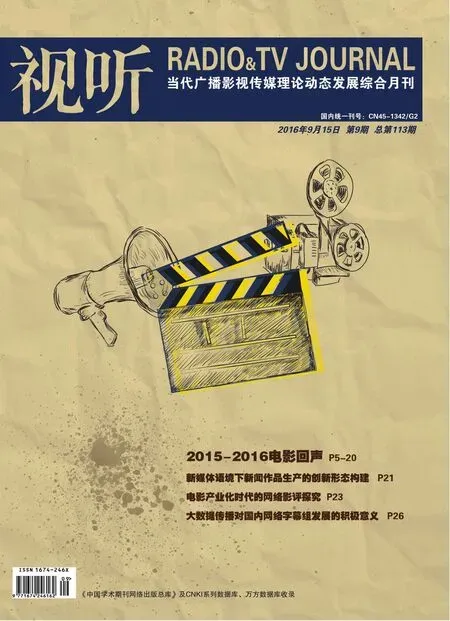微信朋友圈中“轉發”現象的生成邏輯研究
□ 余琦 陳威 康文倩
微信朋友圈中“轉發”現象的生成邏輯研究
□余琦陳威康文倩
“轉發”是微信朋友圈中經常出現的現象,但“轉發”行為背后存在復雜的生成邏輯。本文認為,微信朋友圈的“轉發”現象受制于心理接近邏輯、主客互動邏輯、營銷推廣邏輯、熱點分享邏輯等,但“轉發”現象中存在盜版、虛假信息、負能量傳播等問題,需要學界和管理部門予以重視,并采取切實可行之策規避其負面影響。
微信;朋友圈;轉發;生成邏輯
微信作為一種獨特的社交媒體,深入民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交流互動的瞬間。“轉發”是微信朋友圈中較為常見的現象,但是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發生邏輯,也有與“轉發”行為相伴的諸多問題。對這一問題研究,不僅關乎到“微信”自身的未來走向,更關乎微信使用者之間復雜而微妙的權力關系。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有著明顯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微信朋友圈“轉發”現象的生成邏輯
微信朋友圈“轉發”現象的產生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總體上看,有如下若干生成邏輯。
其一,興趣心理相近邏輯。某種意義上圈子的劃分,也就是人們不同的興趣心理的劃分,微信朋友圈的轉發邏輯也是來自于此。在朋友圈的相關轉發內容中,大多數都和我們平常的興趣和心理相近因素有關,包括生活圈、地域圈、學術交流圈、共同的音樂喜好圈等。①這些內容對圈子中的參與者都具有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這就是心理接近邏輯,每當圈子中的人采取了轉發行為,圈子中的其他人因為有相同的“傳播語言”,只要能夠接受和認可轉發的內容,相關的轉發就會不斷持續下去。
其二,主客互動邏輯。根據米德的觀點,人的“自我”是“主我”和“客我”的統一,前者是個人的主體意識,后者是自我觀察到的除了自我以外的其他人對我的評價、態度和認知等等,“客我”相關的因素往往只能夠通過與他人交換才可以顯現得出。②在微信朋友圈,轉發往往是一種在虛擬環境下“客我”的重塑與再造,這是轉發者的“狂歡”。在信息爆炸時代,微信朋友圈成為了解一個人的重要渠道,成為一個人對陌生微信好友或者沒有那么熟悉的微信好友塑造“客我”的有效途徑。微信轉發的文章內容通常帶有鮮明的觀點和個人立場,轉發代表了對這樣的立場或者觀點的認同,這就是一個他人對轉發者“客我”認知的過程,不同的轉發內容能夠從多個角度了解一個人的品味、愛好、立場等,這是樹立“客我”形象的良好途徑。
其三,營銷推廣邏輯。“微信”經過多年運營,已經擁有了龐大的用戶積累,根據騰訊2015微信用戶大數據統計,微信每月活躍用戶已達到5.49億,用戶覆蓋200多個國家、超過20種語言。此外,各品牌的微信公眾賬號總數已經超過800萬個,移動應用對接數量超過85000個,微信支付用戶則達到了4億左右,如此龐大的用戶基礎意味著龐大的市場。③與傳統的開放式社交軟件不同,微信的強關系屬性決定了微信朋友一般都是現實中有或多或少交集的真實社交關系,因此在朋友圈里的微信轉發也就能夠在“強關系”的基礎上進行,人們對微信中傳遞的信息也相對而言具有較高的信任度,也就成了微信營銷的最佳溫床。廣大的商家和個人也就因此而利用微信進行文案廣告的宣傳,微信朋友圈某種意義上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全民營銷”的大平臺。④
其四,熱點分享邏輯。虛擬化社交媒體來源于真實生活,根植于真實生活,因此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件和熱點事件經過虛擬社交軟件的解構發酵處理之后具有傳播意義上的“病毒性”,常常能夠引起瘋狂的大范圍傳播并產生巨大的影響。如人大教授驅逐學生事件、隨手轉發解救被拐賣兒童事件、8·12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和引起總理關心的毒疫苗事件等,這些事件的瘋狂轉發一方面能夠滿足公眾的求知欲和對事件動態的知曉欲望,另一方面又能夠喚起大眾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并且正確消息的轉發能夠起到引導輿論的效果。“一箭雙雕”的轉發效果刺激了轉發主體的轉發意識,從而引導轉發行為的最終實現。
二、微信朋友圈中“轉發”現象存在的問題
其一,“轉發”帶來版權問題。微信上的文章通常而言比較短小精悍,是一個快速閱讀的產物,因此隨之而來的微信文章閱讀量的競爭就異常激烈。很多微信公眾號或者微信個人,為了吸引微信用戶瀏覽,擴大知名度,提升閱讀量,而走上了抄襲的道路。例如微信知名公眾號因涉嫌“剽竊”知乎稿件而道歉,相關雜志未經原作者同意使用文章引發法律知識產權糾紛等等。微信“轉發”現象較為常見,但是如果不解決版權保護問題,微信發展則會受到限制。
其次,標題黨泛濫成災。“微信”因為其高度的隱私性和進入壁壘,成為了各種“小道消息”或者謠言、流言的滋生地,也成為各種標題黨生存的溫床。微信朋友圈中隨處可見“農村小妹轉身,驚呆了!”“勁爆視頻,刪前速看”“看哭十億中國人,不轉不是中國人”等極度夸張的標題,甚至還有一些涉及“軟色情”的標題。總的來說,微信轉發中這樣的情況非常常見,在一些相對而言年紀較大的微信使用者身上體現得也相當明顯,他們熱衷于轉發,也熱衷于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所看到的他們自認為是“絕密”“內幕”等類似的內容。另一個就是微信“軟色情”內容的泛濫,軟色情的標題直指人的動物性本性,并具有廣泛的受眾,這些標題對媒介素養較低的受眾有著巨大的負面影響,他們不但瘋狂轉發,同時還會“信以為真”,這對原本健康和諧的微信朋友圈生態環境產生了極大的不良影響。
其三,轉發“負能量”的問題。并不是轉發負面題材的新聞信息,就會產生“負能量”,而是在現實中,有些負面題材的新聞信息或資訊,不僅沒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反還在傳播一些錯誤的、落后的、不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價值觀點,這對于我們建設和諧的網絡輿論環境造成了一定的沖擊。這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有很鮮明的例子,例如ISIS組織利用美國的FACEBOOK等社交平臺來宣傳邪教組織理念,利用發達的社交平臺來招募“圣戰”戰士,并且發動所謂的“圣戰”,在這里,社交平臺成為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滋生地”。而在我國,“轉發”并不是要否定負面題材的信息傳播,而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正面角度對這些相關的“負面”題材進行規避、引導和管理,從負面內容泛濫的境況中能夠挖掘出正能量,對營造健康、和諧、穩定的網絡環境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
三、結語
微信朋友圈中的“轉發”現象,受制于心理接近邏輯、主客互動邏輯、營銷推廣邏輯、熱點分享邏輯等,這些邏輯交叉重疊,共同發揮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朋友圈中的“轉發”現象存在侵害版權、標題黨泛濫成災以及傳播“負能量”等問題。微信朋友圈的“轉發”行為,盡管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它所產生的負面問題不可低估,亟需廣大微信用戶和相關部門引起重視,共同為凈化微信朋友圈生態環境做出努力。
注釋:
①劉燕龍.社會化媒體內容的轉發動力研究——以微信朋友圈為例[J].現代視聽,2015(11).
②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72-74.
③數據來源于2015年騰訊微信用戶大數據統計。
④張爾煦.微信推廣的病毒性營銷分析[J].新聞傳播,2012(6).
1.蔣艷.微信與微博比較研究:基于SW模式視角[D].暨南大學,2014.
2.章隱玉,李武.哪些微信文章更容易被轉發——一項基于內容分析的探索性研究[J].視聽,2016(2).
3.楊延超.與微信平臺有關的著作權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15(8).
4.方興東,石現升,張笑容,張靜.微信傳播機制與治理問題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35(6).
5.盧南峰.微信朋友圈:隨手轉發的“輿論場”?[N].中文自修,2015(11).
(作者單位: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本文為江蘇省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對大學生社會化的影響研究——以南京為例”(201510298071Y)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