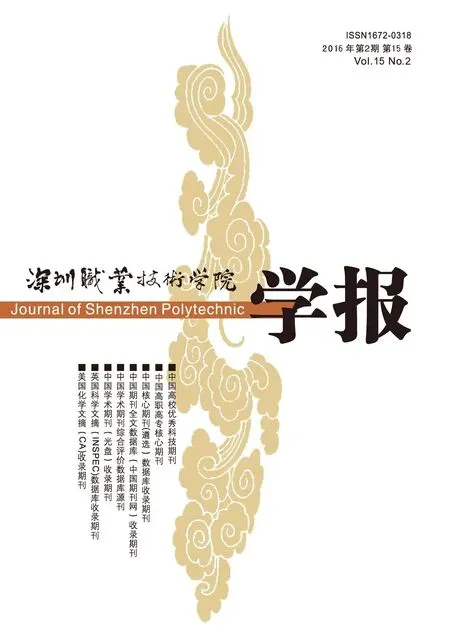政策與法律的良性互動
——以普遍二孩政策出臺為背景
劉華鈞,龐正世(河南辰中律師事務所,河南 鄭州 450000)
?
政策與法律的良性互動
——以普遍二孩政策出臺為背景
劉華鈞,龐正世
(河南辰中律師事務所,河南 鄭州 450000)
摘 要:政策與法律之間存在著良性互動的關系,這可以我國計劃生育事業的歷史進程為證。兩者的良性互動,有法政策學和行政過程論做理論基礎,但是,兩者的互動也存有功能上的障礙,為了更好的實現兩者的互動,公眾參與原則和法治思維原則,是必須堅持貫徹實施的。
關鍵詞:政策與法律;計劃生育;二孩政策;法政策學;行政過程論
2015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閉幕。全會公報指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婦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務水平。這意味著二孩政策全面的放開。這一政策的公布,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熱議。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在學界關注的學者并不多,筆者從小處入手,以普遍二孩政策出臺為背景,嘗試論證政策與法律的良性互動關系,以期有所收獲。
1 良性互動的歷史進程
我國的計劃生育事業走過一段曲折的發展歷程。自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國家以中央政策推行,隨后地方上零星地出現了一些規范性文件,但這一時期,很難稱得上是生育政策的法治化,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停滯,直至1978年憲法第53條第3款明確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才算真正開始走上了法治化的進程。隨后的1982年《憲法》第25條以及第49條第2款又做了相應的規定。在憲法明確規定之后,法律法規也隨之跟進。1998年出臺《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2001年頒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到2002年又實施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再加上各省、市為貫徹執行法律、法規而制定的規范性文件,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形式法律體系。
法律體系的運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它在不斷地接受并分析社會實踐中反饋回來的法治因子并加以處理的過程中,不斷地完善這自身。這一過程,就被稱為實質法治化的過程。隨著人權理論的發展,作為基本人權的生育權得到重視。2004年3月14日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入憲。2004年《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獲得修訂,2009年《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例》也獲得了修訂。這兩部行政法規修訂的內容中包含了重要的權益保護內容。相應地,政策也悄然發生著變化。計劃生育綜合改革試點區以及各省市也在探索實施計劃生育戶的養老保障、醫療衛生服務、失學兒童的義務教育等舉措。于是,在政策和法律的良性互動中,計劃生育事業正在經歷這一場深刻的變革。
2 良性互動的理論基礎
關于政策與法律的互動,是近幾年才開始關注的焦點問題。這一焦點問題,與法學界的兩種研究方法暗暗契合。一是法政策學,二是行政過程論。
“在當下的行政法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現實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注重把行政法學研究與公共政策相連接,并以政策為導向研究社會問題。”[1]“楊建順教授在分析現代行政特點的基礎之上,強調要從行政法政策學的角度對政策形成過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質、現代國家的利益反映機制、輿論監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問題進行探討。魯鵬宇博士認為,法政策學應當定位于法學的分支學科,并始終要以法律思維為基礎,在不斷批判和反思政策思維的基礎上實現法學與公共政策學的有機整合。就基礎概念而言,法政策學的支柱性概念包括政策目標(立法目標)、政策工具(行政手法)、規制模式(組合手法)和評價基準等。就具體的事項分析而言,法政策學需要采用過程分析模型,對立法所涉及的價值、事實和規范三要素進行循環往復的觀察和論證。”[2]
縱觀法政策學的代表觀點,我們可以看出,理論界已經開始關注并重視,政策對立法、執法的影響,并通過“循環往復”的過程論證,來達到依法行政的目的。但同時,法律的實施對政策的影響,并沒有被忽略。
2.2行政過程論的提出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日本開始將行政過程論作為其行政法學的新理論。隨著其不斷地發展和豐富,該理論進而成為日本行政法學中的主流理論。我國的一些學者開始在運用日本行政過程論的觀點來分析中國的現實問題。
“傳統行政法學理論過度地偏重于作為行政過程最終結果的行政行為,切斷了各個連續的行為形式之間的聯系,但在現實的行政中,各種行為形式常常被結合起來連續使用而形成整個動態過程。因此,行政法學必須將行政過程中的各種行為形式全盤納入視野,并加以全面、動態的考察。其中,全面考察觀點認為,應當將傳統行政法學所忽視的內部行政行為、非定型行政行為以及事實行為等納入行政法學視野;動態考察觀點認為在對行政過程中的各種行為形式進行分別的考察外,也應當注意行政過程中各種要素之間的關聯性,以此進行動態考察。”[3]全面、動態的考察,就包括了對政策的全面考察以及對政策與法律之間動態的考察。
3 良性互動的功能障礙
法律調整的范圍是有限的,比如,在一些經濟領域中,以及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都是靠政策來調整的。同時,政策的調整作用也有局限性。“從政策的形式上看,缺乏規范性調整的嚴謹性和系統性;從調整方式看,政策也缺乏規范性調整所必需的穩定性”[4]。除了法律、政策本身特點的制約外,它們之間良性互動還存在以下的功能障礙:
獨立院校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與社會適應性。因此,獨立院校英語專業視聽說教學目標為:培養英語聽力理解力與口頭表達力,培養英語文化素養及培養交際能力。
3.1政策占主導,影響實質法治的實現
在全面二孩政策出臺之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是指令性計劃。“指令性計劃以確定生育指標、配額的方式,通過層層下達,從政策制定層一直下達到處于底層的行政主體、直至家庭和個人,與之相配套的是嚴苛而缺乏彈性的生育政策——比較普遍的‘一孩政策’和針對個別地域和對象的嚴格的‘一孩半政策’或‘兩孩政策’并以(‘一票否決’等高度剛性的績效評價制度予以貫徹),以及嚴格的管制措施,包括罰款、辦學習班、‘補救措施’(即終止妊娠)乃至其他對人身、對財產的強制措施。”[5]在此政策的影響下,生育審批制度和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開始實施。
3.1.1生育審批制度
由于生育政策的指令性特點,《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了嚴格的生育審批制度。一方面,生育審批制度與現行法律相矛盾。它不僅與《憲法》中人權保障條款相沖突,還與《行政許可法》的相關條款相沖突。我國憲法規定,應尊重和保障人權。生育權是基本的人權,這早在1968年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中就予以規定。1992年,我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一次在立法中規定了生育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也指出:“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對公民來說不是強制性義務,是倡導性義務,主要采取國家指導、群眾自愿,因此必須從鼓勵和提倡入手。”在《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中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另外,自2001年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啟動以來,國務院已先后多次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禁止審批與其它不相關的條件相關聯,并嚴格限定將毫無意義的審批作為辦理審批的前置性條件[6]。另一方面,生育審批制度與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相矛盾。“傳統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目的性,即行政權力的行使,行政措施的采取,是為了達到法定目的;必要性, 即為了達到法定的行政目的,該項措施是給人民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比例性,即行政權力所采取的措施與其所達到的目的之間必須合比例或相稱。”[7]政府為了達到生育政策的目的,對違反政策、法律法規的人民采取強制性的措施,這本身就違反了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和比例性要求。
3.1.2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
對政策的貫徹,導致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出臺。自該辦法出臺以來,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制度就帶來了諸多弊端;造成了諸多黑戶,嚴重侵犯了這些孩子的上學、就業、結婚等基本權利;更有甚者,一些因交不上撫養費而自殺的悲劇也在不同地區上演;另外,社會撫養費的征收也滋生了腐敗的溫床,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應當屬于行政處罰。因為超生是違反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規定,是違法行為。國務院出臺的該條例屬于行政法規,而罰款屬于行政法規可以設定的處罰種類。但是,《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違法行為在兩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查《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并沒有像《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二條和《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條的特殊追訴時效的規定,因此,在下位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應適用上位法的規定。然而,現實中,卻出現的超過兩年追訴時效仍然予以處罰的現象卻屢見不鮮。
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要求行政機關既要遵循合法性原則又要遵循合理性原則,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連最基本的合法性原則都沒有遵守,更何談合理性原則,這與實質法治的要求更是相去甚遠。
3.2法律占優勢,構成對政策實施的阻塞
這里的“法律”即指具有安定性特點的法律,也指法律人具有的嚴格法律思維。正是由于法律的以上特點,構成了對政策實施的嚴重阻塞。
3.2.1法的安定性
德國20世紀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法哲學家和刑法學家之一的拉德布魯赫認為,法律的概念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必然涉及到價值的層面,法律就是一個有意識服務于法律價值與法律理念的現實。而法律的理念,包含正義、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三個價值。而法的安定性是置于第一位的價值,因為法的安定性象征著秩序和安寧。當正義與法的安定性之間發生沖突該如何解決時,拉德布魯赫這樣講到:“正義與法的安定性之間的沖突可能可以這樣來解決:實證的、由法令和國家權力保障的法律有優先地位,即使其在內容上是不正義或者不合目的性的,除非實證法與正義之間的矛盾達到了一個如此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作為‘不正當法’的法律則必須向正義讓步。我們不可能在法律不公正的情況與盡管內容不正當但仍然有效的法律之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確的界限;但是,對其他界限還是能夠非常清楚地進行劃分的:在所有正義從未被訴求的地方,在所有于實證法制定過程中有意否認構成正義核心之平等的地方,法律不僅是‘不正當法’,而且尤其缺乏法律本性。”[8]因此,當‘不正當法’已被大多數專業人士所認可,但由于法的安定性特點,要想廢法、修法,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犧牲的,在這一艱難博弈的過程中,良好政策實施的道路必然被阻,也是可想而知的。
3.2.2法律人思維
好的政策的實施,需要法律去貫徹。而最高決策者往往不是法律專家,因此,立法、釋法的工作大都有法律人完成。法律人的意見也往往對最高決策者影響深遠。但是,“在有的情形下,絕大多數的法律人可能處于視野較窄的境地。由于視野的障礙,法律人對法律問題的觀點可能不務實、想當然、理想化,因而對制度變遷的指導力有限,甚至還可能成為阻力。”[9]一般的法律人都具有對形式邏輯的過度偏好,對公平、正義的過度重視以及對法律工具的過度迷戀等特點。正是由于法律人思維的如此特點,在法律體系向計劃生育政策輸送指標的過程中,就有可能出現偏差。政策的制定出現了問題,政策的實施就會遭受阻礙。
4 良性互動的原則遵循
為了減弱以上功能障礙對良性互動產生的巨大阻隔,以下兩大原則是需要遵循的:
4.1公眾參與原則
政策與法律要形成良性的互動,離不開各主體的廣泛參與。在這一過程中,參與的主體主要包括:決策者、立法者、公眾和專家。決策者和立法者是最后的決定者,公眾和專家通常只是建議者。但長期的學術理論通常將公眾與專家對立,認為公眾是非理性的、經驗主義的,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是民主的最大破壞者;而專家則是理性的、精英主義的,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民主的最大維護者。筆者并不認同此種理論。一方面,我們不能神話專家,專家只是在其所擅長的領域內擁有比一般常人更有力的發言權,而一旦脫離了這一領域,這樣的建議的可采性往往就會減弱;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貶低公眾,一個多年在小企業管賬的小會計對會計報表的解釋往往比一個法學專家更有說服力。所以來說,公眾參與原則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在于通過什么方式讓什么樣的人參與的問題[10]。
另外,在當代行政活動中,存在民主赤字和管制俘獲的概念。民主赤字是指,當傳統行政權通過代議機關用“傳送帶”的方式輸送民主從而賦予其合法性的這種模式,已被當代行政的諸多新特點(例如行政活動的政治化、國家行政的社會化、行政立法的興起等)所打破,從而出現民主正當性缺乏的狀態。管制俘獲是指,在行政過程中,組織化的利益通過各種方式對管制機關施加影響。在這些影響的作用下,行政機關的政策可能表現出持續的、固執的對某些被管制利益的偏愛[11]。而在政策與法律的互動中,公眾起著溝通二者的紐帶作用,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同樣會出現上述現象,因此,公眾參與原則,應當引入公眾充權和協商民主的概念,從而使公眾參與真正達到名副其實。
4.2法治思維原則
法治思維不同于法律人思維,法治思維原則在指導政策與法律良性互動的過程中,要求:一是,政策要受到法對社會一般性調整的限制。決策機關的活動要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不得逾越之上。二是,決策內容與決策過程必須受到法的制約。黨的各級政策不得與現行的法律相沖突,一旦出現此種情況,原則上要堅決維護法律的權威,避免出現以權壓法,權大于法的現象。三是,要將法貫徹到政策實行的整個過程。將政策實行主體、政策實行權限、政策實行程序等統統納入法律體系。如若達到以上三點,必將開創政策與法良性互動的新局面。
按照法治思維原則的要求,在普遍二孩政策的出臺后,為貫徹此政策的實施,以下工作是必須的:一、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后,還應逐步廢除生育審批制度。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不變,要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年齡、性別結構,提高人口素質,以此理念貫穿《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實施。生育審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者違憲、違法的情形,鑒于當前計劃生育工作的復雜性,建議逐步廢除生育審批制度。二、廢除《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強制征收社會撫養費,不僅存在著合法性的障礙,而且對于撫養費的去向也存在監督的漏洞,對公眾也是一種負擔,隨著普遍二孩政策的落地,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家庭將會越來越少,正因該辦法與原《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配套實施的,所以在此次《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之后,逐步廢除該辦法。三、對一些亟需法律法規規制的領域,例如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專科醫師培養等盡快出臺法律法規。
參考文獻:
[1] 黃學賢,鄭哲.聚焦二維結構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制度[J].蘇州大學學報,2013(5).
[2] 李洪雷.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趨勢——兼評“新行政法”的興起[J].行政法學研究,2014(1).
[3] 江利紅.行政過程論——行政法學理論的變革與重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208-211.
[4] 范愉.論我國社會調整系統中的政策與法[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6).
[5] 湛中樂,蘇宇.計劃生育制度變革與法治化[J].清華法學,2010(2).
[6] 王克穩.我國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及其法律規制[J].法學研究,2014(2).
[7]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研究[J].法律科學,2001 (1).
[8] 白法.正義與法的安定性——告密者困境與拉德布魯赫公式[J].人民法院報,2014(6).
[9] 應飛虎.制度變遷中的法律人視野[J].法學,2004 (8).
[10]章志遠.價格聽證困境的解決之道[J].法商研究,2005 (2).
[11] 王錫鋅.參與失衡與管制俘獲的解決:分散利益組織化[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8(6).
中圖分類號:D9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318(2016)02-0065-05
DOI:10.13899/j.cnki.szptxb.2016.02.011
收稿日期:2015-12-19
作者簡介:劉華鈞(1988-),男,河南社旗人,法學碩士,律師,現主要從事行政法學研究。龐正世(1981-),男,河南鞏義人,法學學士,律師,現主要從事行政法學研究。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Law and Policy —with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s the Background
LIU Huajun, PANG Zhengshi
(Henan Chenzhong Law Firm,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ina)
Abstract: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witnesse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y and law. Law policy study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ory be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till has some barriers.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intera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
Key words:policy and law; family planning; two-child policy; law policy study;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