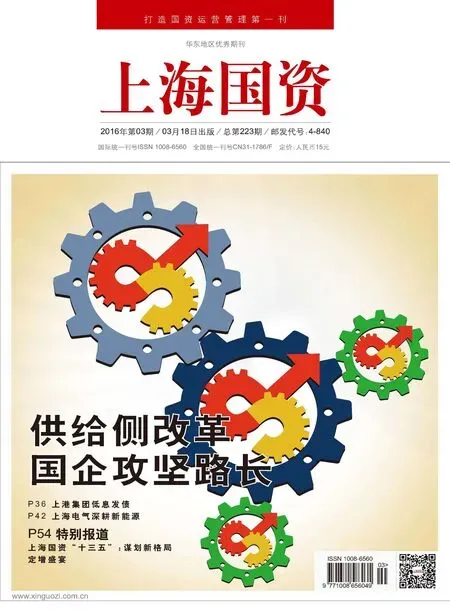事業合伙人制:新三角平衡術
事業合伙人制:新三角平衡術
沒有人會用心擦拭一輛租來的車,合伙人機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創造擁有感
2016年2月,萬科“事業合伙人制”傳出消息:將進一步推動組織架構變革,將集團的部分經營管理實權下放至各個大區,進一步推動和激活事業合伙人制度中的“責權利”落地,推動過去的“大集團大平臺小事業部”架構向當前的“小集團大事業部平臺服務化”轉型。
無獨有偶,2016年年初,復星集團亦宣布將實行“事業合伙人”計劃,并發布了首批多層次的合伙人名單和相應的股權激勵計劃。
在他們之前,已有不少傳統企業進行了事業合伙人嘗試。典型的是海爾。早在幾年前,張瑞敏已徹底地將這個制造型企業變身為創業孵化器平臺,將員工打造成為一個個的創客和小微主。
傳統企業正在組織結構上全面擁抱互聯網,利用事業合伙人制進行深度轉型。
助力組織變革
實際上,傳統企業早就開始擁抱互聯網。但在利用互聯網轉型的過程中,很多企業的轉型陷入“戰略方向與執行策略變形”“說一套卻又做一套”“市場轉型與管理轉型不協調”等一系列困境之中。原因在于受到傳統組織架構和管理體系的制約:大量傳統企業的轉型只是外部市場經營業務和品牌宣傳推廣等層面,而涉及經營管理團隊在企業內部的運營模式、管理手段和主動創造性等方面,均未實現根本性轉變。
專家表示,由事業合伙人取代職業經理人,正是解決傳統企業過去幾十年以來,一直推動和實施的以KPI業績考核為導向的內部經營轉型和組織創新等一系列矛盾的突破口。這不只是解決員工激勵機制、激活團隊整體活力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以“事業合伙人”計劃為突破口,帶動整個傳統企業在組織架構、管理體系和發展新動力等問題上的持續突破。
從表面上看,事業合伙人制度的推出和實施,主要是解決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和定位。不僅解決企業經營者在企業具體的經營管理和轉型變革過程中“責權利”對等和協同的關系,真正賦予經營者具體的經營權限,還要享受到經營增值帶來的回報,真正實現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協同和一致。
但在實際操作中,事業合伙人制度不只是解決了經營者在企業的地位和權限等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牢牢抓住企業經營過程中人的問題,改變過去由“企業所有者一個人驅動”為“企業經營團隊一個團隊驅動”的新驅動體系。同時還激活經營管理層的活力、激情與斗志,解決傳統企業發展活力和動力的問題。然后通過人這一抓手,徹底解決傳統企業體制和機制在互聯網時代的一系列矛盾與沖突。
改變股東與管理層關系
傳統企業中,公司是股東的,管理層很多時候是打工者,不像股東那樣承擔投資風險。職業經理人與事業合伙人最大的區別,就是是否與股東共擔風險。
通過事業合伙人制,管理層的身份從職業經理人轉變為事業合伙人。通過持股計劃和項目跟投等,骨干團隊變成跟股東一樣的公司投資者。
萬科總裁郁亮認為,事業合伙人制解決了股東和員工應該誰擺在前面的問題,職業經理人的身份搖身一變,既為股東打工也為自己打工,從利益基礎上變成了一致。萬科還在持股計劃和項目跟投中引入了杠桿,使得事業合伙人團隊承受比股東更大的投資風險。
同時,事業合伙人制可以某種程度上加大管理層對公司的控制權。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的合伙人并不享有公司大部分股權,但可提名阿里大多數的董事,是否通過委任,則由股東會投票表決。若股東否決合伙人提名董事人選,合伙人可再另行提名人選。
不過,與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咨詢公司等獨立性較強的非上市公司的合伙人制不同,也與阿里巴巴、小米等互聯網公司層面的“合伙人”制度不同,萬科的事業合伙人制度不是公司層面,而主要是項目層面的。按照當前中國公司法規定,萬科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變更為合伙制企業存在困難,除非公司退市;而在項目層面,通過項目跟投等,更容易實行事業合伙人制度。
郁亮表示:“事業合伙人有四個特點: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要形成背靠背的信任;我們要做大我們的事業;我們來分享我們的成就。”換言之,不是大換血或發股票,而是在原有職業經理人基礎上,身份角色的進化。“我們能不能把現在管理層和股東的打工與老板的關系,轉變為合伙人的關系?雙方能不能更加信任與被信任?”接近萬科的觀察人士稱,萬科可能借鑒阿里的經驗,賦予合伙人更多的公司事務決策權和董事會席位,而非單純的股權激勵。
重塑公司與員工關系
事業合伙人制度可重新界定公司與員工的關系,防止優秀人才的過度流失。
這是許多傳統企業探索事業合伙人制度的目的。萬科即是如此。2010-2012年間,萬科高管大量出走,三年間大約有一半執行副總裁以及很多的中層管理人員離開,這引發了萬科“中年危機”的大討論。“我們需要搭建更大的舞臺,通過事業合伙人的機制吸引并保有更多優秀的人才。”
傳統企業在看待人力資本時,很多時候想的是如何更好地激勵員工,更好地提高員工人均效益。“員工”二字反映出企業仍然是主體,人從屬于企業,并沒有實現人與組織、資本的真正對等關系。
但把合伙人作為激勵新機制,重塑了公司與員工關系。
把合伙人機制作為激勵新手段,對企業有著很多積極作用。如:可創造擁有感,凝聚合作伙伴。沒有人會用心擦拭一輛租來的車,合伙人機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創造擁有感。當然這個擁有感不是法律上的擁有概念,即與資本享有同等的股權、決策權、分紅權。這種擁有感主要是參與企業經營的權利,在企業內部為人才創造創業的條件,變“為別人打工”為“為自己打工”。當人才參與公司經營決策、融入創業合伙人團隊時,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創業的感覺。就如同小米員工對加班的評論:“如果你找一份工作,天天加班當然是不行的,但如果是創業就不同了,創業是一種生活方式,你在為自己而活。”
一句話,事業合伙人制可以盤活人力資本,打破壁壘,發揮人才價值。合伙人機制其實是給核心人才職位之外的一個組織角色,這個角色可以讓人超越自身的職位發揮影響力。比如一個分公司的總經理成為合伙人以后可能會打破分公司之間的壁壘,從公司整體角度思考業務發展,支持其他分公司的業務;部門中層成為合作人后會更有大局觀,打破部門墻,有利于促進合作等,合伙人角色會賦予人一個組織的視角、一個超越自身崗位的視角。有效的人力資本盤活,可以用人所長,有利于人才價值的發揮。
亂中取勝
互聯網時代,流程化和管控型組織已死、平臺化和生態化組織誕生。流程森嚴、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公司,正在失去快速反應能力。野蠻生長、靈活機動、放手人才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公司,卻可能亂中取勝。在智力勞動領域,這種趨勢已經看得很明白了,比如互聯網創業、IT行業、投行投資資管領域、律師會計師設計師等,不按事業合伙人的理念、不搞平臺化和生態化組織,幾乎做不大。
事業合伙人制可解決大公司部門的責權利劃分不清的問題。比如,萬科探索了“事件合伙人”的形式。這是萬科“事業合伙人”的第三個部分。
郁亮表示,萬科事件合伙人可以更有效地解決部門之間的問題。
“一件事情,比如說給客戶省成本這件事情,臨時組織事件合伙人參與到工作任務里面去,事情解決就解散,回到各自部門。這樣我們就發現有很多東西可以改造,有很多東西可以瓦解,以前都是職位最高的人擔任組長,現在可以推選出最有發言權的那個人來做組長,這樣的話他對這個事情最有研究,最有發言權,他做組長才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
(本刊記者孫玉敏根據相關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