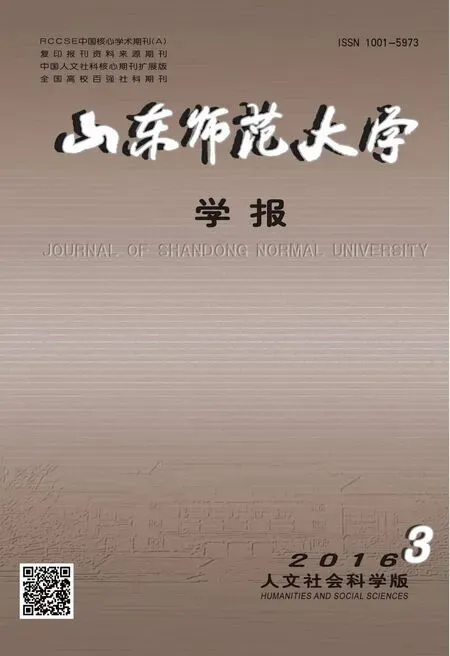論“文學是情學”*
殷國明
(華東師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上海,200241)
?
論“文學是情學”*
殷國明
(華東師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上海,200241)
“文學是情學”提供了探求文學與人、與人生和人性之間隱秘關系的通幽小徑。情最貼近人類生命本原,直接源自于人類的本能和原始欲望狀態,也最能反映潛藏在人們潛意識中的能量和能力,激發人們的想象和創造力。情之回歸,不單是對于壓制和束縛人性的各種傳統制度與觀念的挑戰,也是文學回歸人性、回歸大眾、尤其是回歸人類日常生活之路。“情學”也許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問題,而人類對于情的認識,也不僅僅止于對文學藝術的探討,實際上這是一個重新反思人類精神史和思想史,繼而更加深入認識人類自我的時機和轉折點。
文學是“情學”;人學;心學;情理相通;紅樓夢;焦循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1
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整體反映和表現,更作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本包含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層面,其中不僅有歷史、哲學、倫理和道德,也涉及人類理性、思想、感情、感覺等內容。所以,文學不僅是人學,也可以是“心學”、美學和感性學,文學研究更是可以從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及思想和道德等各個方面進行,從文學中獲取啟示。不過,從文學本身來說,從各個不同角度和層面來理解和研究,確實能夠促進對于文學的認識,甚至豐富文學的想象和建構,帶來文學自身的突破和創新,但是如果過度強調和闡釋,也會消解、甚至取消文學自身賴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更難以真切體驗和觸及文學之所以魅力長存的緣由。
正是在這種疑慮和困惑中,“文學是情學”開始引人注目,人們試圖在種種人類學說和精神構成中找到文學的根脈,在“人學”的框架和語境中更深一步,進入人類尚未能夠完全把握和認知的領域,探求文學與人、與人生和人性之間的隱秘關系。這或許不能稱之為一種“學”,但確實是一條探尋和理解文學存在和價值之秘境的通幽小徑,值得人們穿越附加在文學身上的種種外在理論和觀念,回到文學本身,細讀、細看和細解文學的奧秘。
一、“情學”:并不突兀的命題
從歷史淵源來說,“文學是情學”之義源遠流長,早就有人不斷提及和論述,但是作為一個命題明確提出者,則要感謝王世德先生。1989年,王世德*王世德(1930—),當代美學家、文藝評論家,編著出版中國大陸第一部《美學辭典》,出版《文藝美學論集》《蘇軾文藝美學思想研究》《美的欣賞與欣賞》等多部文集和專著。在《探索》第2期發表《探析“文學是情學”》一文,開宗明義提出“情學”命題,并在文中指出:
既然文藝要動人以情,要使觀賞者激引起美感,那么它怎么可能不表現感情呢?不表現感情,不充滿感情,就不可能動人以情;要起給人美感的作用,就必須具有審美感情這一本質特征。*王世德:《探析“文學是情學”》,《探索》1988年第2期。
他還如此解說了“人學”與“情學”的關系:
人們常說文學是人學,其特指意義是文學要寫人,寫人的情感,這主要是指作者的情感。為了表現作者的情感,就要派生出著力表現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在敘事文藝作品中就要著力寫人的命運。……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學是人的情感,是情學,是表現人情的審美對象。中外文藝反映的生活原型可以變形,但仍感動人心者,靠的就是其中充滿人們相通的情理,情的背后有理。如果違背了人間情理,即使反映生活形貌毫厘不差,真實到極點,也只是假象,也不可能感動人。*王世德:《探析“文學是情學”》,《探索》1988年第2期。
如果在這里論者不突然求助于“理”(“情的背后是理”),那么,關于“情學”一說幾乎要落地生根了。盡管如此,王世德的觀點依然給人一種頓開茅塞之感。而他在文中對于“文學激起審美情感的四個層面”的分析和論述,對“文學是情學”的闡釋更有獨到之處。
當時,中國新時期思想解放處于高潮階段,文學不僅迎來了藝術思潮和流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也觸動了人們的歷史文化心理,在情感深處掀起了波瀾。“文學是情學”命題的提出,還昭示了中國文化變革這樣一個事實,即洶涌澎湃的思想解放運動的背后,必然涌動著蓄勢待發的情感要求,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相互激發和促進的。而就一場有效的、能夠持久的思想解放運動來說,必然要有情感、甚至激情作為基礎,作為一種被長期壓抑的情感噴發,也無不期待思想和理論的支撐與正名。
這種情形也為“情”在文學理論和批評領域再次崛起提供了時機和語境。例如,朱德發*朱德發(1934—),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著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五四文學新論》《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等專著。就在梳理和研究中國情愛文學基礎時,提出了“愛情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的看法。他指出:
情愛之所以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在文學領域具有如此不可取代的地位,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卻是它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它不僅與個體人生密不可分,而且在整個人類生活中也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從特定意義上講,毀滅了情愛就意味著毀滅了人類。文學是人類生存方式和自由意志的表現,當然它要主動地密切關注著人類情愛生活或性愛意識的發展與變化。*朱德發、譚貽楚、張清華:《愛河溯舟——中國情愛文學史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頁。
當然,關于“文學是情學”觀念的來源,還可以追溯得更早。*殷國明:《“情學”:文學探尋的歸根之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例如,清人焦循就認為:“詩本于情”,他在論及“詩何以必弦誦”時還如此說到“情”之重要意義:“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嘆,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己于言,又有言之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焦循:《與歐陽制美論詩書》,王云五編:《雕菰集》卷十四,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36年,第235頁。由此,他對于寫詩提出了如下要求:
詩本于情,止于禮義。被于管弦。能動蕩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為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媢嫉之心,不可以為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偏頗怪癖之心,不可以為詩;有矜能斗勝之心,不可以為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為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于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于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于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即而取之無有也,至于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后郁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縟,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者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焦循:《與歐陽制美論詩書》,王云五編:《雕菰集》卷十四,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36頁。
在這里,說“文學是情學”的發明權屬于焦循未嘗不可,問題在于焦循尚不能盡情言之,仍然在傳統的詩教框架內有所顧忌。不過,正是由于他發現并認定了這個“本”,所以也被吾恩師錢谷融先生引之為圭臬,并在論述《藝術的魅力》一文中進行了細致解讀。錢先生認為,焦循用以下三句話來解釋“詩教”是頗有見地的,即:“不質直言之而以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實際上,這三句話都是講情的,正如錢先生所說:“焦循這三句話,如果用科學的眼光來看,當然是未必精當的,我們不能把它絕對化。但這三句話卻的確抓住了文學藝術的一個根本特點,那就是‘文學藝術主要是從感情上去打動人的’。”*錢谷融:《錢谷融論文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9-180頁。
錢先生還在自己的文章中寫下了如此話語:
藝術作品之所以具有打動我們的力量,不正是因為在藝術形象中滲透著作者的強烈而真摯的思想感情嗎?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把他從生活中得來的思想感情,凝鑄到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時,便也接觸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經歷到的激動,他所嘗味的歡喜和悲哀。*錢谷融:《錢谷融論文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頁。
而就文學與情學密切關聯來說,西方豐厚的文化資源也不容忽視。同樣,在西方文學的源頭就流淌著愛情、激情和浪漫之情的瓊漿玉液,以至于人們確信情是人類最古老藝術的精魂所在。這一看法,甚至在蘇格拉底時代就十分流行。柏拉圖在自己的《斐德羅篇》和《會飲篇》中,就記錄了一場事關此后人類思想史發展的爭論,其極大影響了日后文藝理論發展的方向;可惜,以往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場討論在文化思想史上的意義。
這場爭議的命題是愛情,而焦點就是“情學”是否能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持續扮演重要角色、能否被新的藝術標準和價值觀念所接收的問題。這也正是斐德羅要提出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的意味所在:
為什么所有頌神詩和贊美詩都獻給其他神靈,但就是沒有一個詩人愿意創作一首贊美如此古老、如此強大的愛神,這豈不是太離奇了嗎?*[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頁。
顯然,斐德羅的抱怨是針對當時希臘學術狀態的,抱怨的對象并不是當時的詩人和戲劇家,而是新出現的一些博學的文化人,其中自然包括蘇格拉底這樣的哲學家。*這在下文中有明確所指,比如提到的普羅狄科寫的散文,還有所列舉的介紹食鹽和一些日常用品用法的著作等。這也說明,在希臘時代,所謂詩的領域是廣泛的。他們代表了當時希臘新的思想潮流和學派,顯示出那個時代在歷史建構和文化觀念上的巨大轉變。
二、 “情”路漫漫:在人文沖突中時隱時現
顯然,這是一次早有定論的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轉折。因為正是由于這次轉折,確立了“管理國家的藝術和能力”在西方乃至人類文化和思想學術中的軸心地位,其核心價值如同中國儒家學說中的“王道”一樣,就是政治與權力。就此來說,所謂哲學、藝術、道德等人文思想的設置,都不能不受到這種集體、或群體價值和意志的規范和要求,并在合乎國家管理目標的秩序中獲得相應的位置和話語權。
這也是當年蘇格拉底迷醉于情但又不能不懷疑情、質疑情、設置否定情的原因,也是人類思想文化在其奠基期難以避免的局限性。也許正因為如此,在傳統思想體系中,文學藝術始終難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終極的價值取向,總是要依賴諸如宗教、道德、哲學等其他思想的支撐和認定,甚至連美及其美學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也難免招人詬病。所以,從蘇格拉底到黑格爾,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終極價值取向一如既往,就是給藝術套上理性的枷鎖,使之服從權力話語和理性邏輯的規訓。這無異于為一匹充滿野性活力的馬套上轡頭。從柏拉圖的理想到黑格爾的“藝術哲學”,再到如今無處不在的爭奪話語權的“政治詩學”,西方理論范式與話語似乎已經越來越脫離其生命之源,瀕臨“終結”的困境。
鐘情于情,但是有不能不可之情、限制情、甚至否定情,這似乎是人性不能不承受的悖論和宿命,這并非意味人類沒有意識到情感的價值和魅力,而是因為人類為了整體的、群體或集體的生存發展,不能不付出的人性代價。這也正是人類在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文化領域關注、構建和倡揚普遍性原則的淵藪。這種普遍性所關注的不僅是人類自我的確定性和穩定性,而且不能不對人性中過于個人化、個性化的、不穩定的因素加以防范和規避。
這無疑為情、特別是文學藝術中的“情”設置了種種限制,使其理論之路漫長。在中國,盡管自古到今不難發現一條情本主義文學觀的線索,從《毛詩序》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易經》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到陸機《文賦》中的“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劉勰《文心雕龍》中強調“為情而造文”,都莫不把情放在首要或重要地位來進行論述;但是說到精深細微之處,總會透出某種悲愴和蒼涼之感。
例如,魏晉嵇康寫了《聲無哀樂論》,從哀與樂角度探討了藝術魅力的來源,處處流露出對于情感本身的戀眷之感。下面摘錄三則:
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后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
此為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于疑似也。
然人情不同,各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嵇康:《聲無哀樂論》,《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5-150頁。
可以說,不僅在藝術創作中,而且在人生中,嵇康都是一個主情論者。正是由于這一點,他使自己置身于一種險惡的生活環境之中,成為政治、禮教壓制和剿滅的對象,最后難逃厄運。
更為引人注意的是,嵇康在藝術主體(哀樂)與本體(聲)關系的論說,涉及到情感美學與形式美學之間的種種界限,不僅揭示了藝術創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且也為形式的藝術實現和美學意蘊提供了人學基礎。這一點,直到20世紀蘇珊·朗格提出“藝術是情感的形式”*[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才有比較明確的觀念表達。
可見,在人類文化史上,盡管一度對于情有種種誤解和防范,卻不能完全禁絕它在文學創作中存在,也難以將它永遠關在理論和觀念大門之外。相反,由于人類各種理性學說和文化規則的打壓和排斥,文學藝術似乎成了情的唯一棲息之地。人們唯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找到自己情感的鏡像,獲得心靈的慰藉,在幻想和想象中獲得情感的宣泄和滿足。這種情景不僅為藝術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活和生命資源,而且促使藝術理論和批評不斷反省自我,突破原有的局限和框架,在藝術理論和觀念上不斷創新。
在中國文論上,也一直持續著這種突破和創新。例如,在詩歌創作繁茂的唐代,就形成了一種以情為本、緣事入情的詩學方法,即在解讀和欣賞詩歌的過程中,務必追溯其情感的發生過程,究其來源,并視之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孟棨的《本事詩》是珍貴的典范,其卷首云:
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于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觸詩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咨、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
不難看出,在這里,以情為本不僅是一種觀念,而且已經滲透到了具體文學批評活動之中,形成了自己的門類和路徑。這里不妨摘錄其“情感第一”中之一欣賞之:
陳太之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頁。
在這里,似乎毫無理論和理念而言,卻表現了“情”作為貫穿于藝術創作、傳播和欣賞整個過程的意味。這或許也說明,情學才是理解和闡釋文藝活動的真正鑰匙,并不一定要依據純粹理性和理論進行演繹,而是以具體的生命和生活為底蘊,洞察其人性情采,揭示其藝術真諦。通過這種對于具體的“事”之追尋和有所感悟,不僅令讀者為其中閃爍的人性之光所感動和感染,而且很自然地觸及到詩之本源,意識到詩意和詩情原本就來自人生,尤其是人豐富多彩的情感生活。
這似乎完全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學的詩學傳統理念,以情為本,以事為鏡,以一種具體的、活生生的敘述方式,展示了文學的本相和魅力。顯然,就情之風韻來說,中國文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追尋和呈現。如果說,《莊子》道法自然,重在追尋情之精誠,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契合中感悟人生和藝術,奠定了情學的自然之本;《世說新語》在“越名教,任自然”語境中,盡興展示了人之性情之美,拓展了人之性情的多樣性;那么,到了唐代,則迎來了一個以情論詩的新時代。在這一時期,個性的張揚、文學的自覺和情感的放浪形骸,它們互為因果,合為一體,在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方面,都留下了難以復制的精品和極品,深刻影響了中國日后文學的發展,也為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傳統奠定了論說基礎。
由此,如果重回西方希臘哲學現場,就不難發現,中西文藝理論在對待情的問題上,有很多相通、相近的境遇。在那場事關情學命運的討論中,蘇格拉底之所以忽略情的終極價值,繼而一定要給情戴上理性的鐐銬,是有其人類文化發展的內在原因的,也顯示了蘇格拉底在人類群體利益和智慧方面的高尚追求——因為此時的蘇格拉底思考的出發點不再是個人的喜怒哀樂,而是整個城邦和國家的利益,所以連他本人也不否認“我還不能做到德爾斐神諭所告誡的‘認識你自己’”*[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頁。,而只能去關注如何去做一個符合社會理想和理性規范的人——這一點與中國的孔子非常相似。在這里,如果我們希望在他們之間、甚至在中西傳統哲學之間,尋找一個相通的價值和觀念基礎的話,那不妨借用蘇格拉底說過的一句話,“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智慧是統治社會的智慧,也就是所謂的正義和中庸。”*[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2頁。在討論愛情的價值時,這段話是通過狄奧提瑪之口說出的。顯然,這是蘇格拉底認同的。
即便如此,在這場辯論中,蘇格拉底所表現出的對于情的戀戀不舍依然動人,因為情不僅是人類生命意識中最早覺醒和意識到的元素,也是人類生活中最難以忘懷的記憶,要完全回避、遮蔽和否定其意義和魅力并非易事,需要苦口婆心的文化建構。或許這是連蘇格拉底也感到棘手的問題。所以,在進入辯論場所之前,他就表現得十分猶豫,在外面徘徊了很久,遲遲不愿、也許不敢面對眾多的對手;而進入辯論之后,他開始也是含糊其辭,并且不是正面迎辯,而是采取了借他人之口的方式來申述自己的觀點。好在后來記述這場辯論的是他的學生柏拉圖(這一點與《論語》的成書過程頗為相似),所以最終自然把最后的勝算歸于蘇格拉底。
也許在此時,我們突然會對王國維當年對西方哲學生厭有新的感悟。所謂“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說的正是哲學和藝術的關系。哲學因為依仗的是理性和邏輯,面面俱到,但是未必能給人帶來心靈的慰藉;藝術是以情動人,盡管不足以以理服人,但是會令人流連忘返。從《紅樓夢評論》到《人間詞話》,也正反映了王國維從“可信”的西方哲學,折返回“可愛”的中國文學的心路歷程。
這種藝術與哲學、情與理之間的矛盾,也曾給蘇格拉底帶來過困惑。作為一個經常借助神靈立言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在關鍵時刻甚至也會忽略神話的意義,申言“只要我還處于對自己無知的狀態,要去研究那些不相關的事情那就太可笑了”。同時,對于自己的知識和價值取向,他已經表現出了遠離自然的傾向。當斐德羅把他帶到城外一棵茂密的梧桐樹下的時候,他馬上說:“你必須原諒我,親愛的朋友,我愛好學習,樹木和舊園不會教我任何事情,而城里的人可以教我。但你好像發現了一種魔法,能吸引我出城。”*[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頁。
盡管如此,柏拉圖還是記下了蘇格拉底很多值得后人銘記和回味的名言。例如:
愛本身如此神圣,使得一名詩人可以用詩歌之火照亮其他人的靈魂。無論我們以前對做詩有多么外行,但只要我們處于愛情之中,那么每個人都是詩人。*[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5頁。
三、“情學”:如何沖破二元對立結構的限定
顯然,盡管在文學創作中情之作用幾乎可以視為一種常識,但是作為一種理論命題、或者作為一種學說,卻不能不面對種種質疑和挑戰。例如,何以從人類文學史乃至精神文化史中,尋求和獲取其歷史和美學的根基和內涵?如何應對來自既定的、傳統的理論范式和思維方式的質疑和挑戰?其原因不僅來自情自身的特質和人性狀態,而且還出自人類自古以來所建構的人文和理論狀態和框架。就文藝理論而言,通過數千年的文化建構,已經形成了自己既定的理性規范和思維方式,其以哲學之思和道德之辯為思想經緯,以相關的知識譜系和概念系統為支撐,各種觀念、范疇和范式自有定數,秩序井然,加上近代以來的學院派的專業化、學科化的精致打造,儼然是一座話語等級森嚴、論說邏輯嚴謹的精神城堡。由于情一開始就被視為神性、理性和德性的對立面,被排除在思想理論的邊緣,所以很難改變自己在整個文化和意識形態格局中的地位,因此也很難在理論上獲得自己的話語權——除非人類文化體系和思維方式發生顛覆性的重大變局,人類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重構自己的精神家園。
所以,在人類文化和精神史上,盡管情不可或缺、甚至有時會咄咄逼人,不時向人類既定的道德規范和理論體系發出挑戰,但依然不能被視為一種“學”,有自己獨立存在的精神領地。
當然,反過來說,情在文學中不可或缺,是藝術活動中的靈魂所在,也并不意味著情擁有一切,決定一切,占據無可爭辯的強勢地位。相反,正因為情在文化中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一直難以與強勢的理性規則和道德話語相抗衡,才更貼近和靠近文學世界,在藝術的廣闊天地獲得庇護。人類的情感體驗和記憶,或許唯獨只有通過藝術創作才得以保管和留存。
這也是人類至今最感人至深的藝術作品多半是悲劇的緣由之一。就“文學是情學”的命題,也并非意味著文學中只有情,或者情在文學創作中能夠統治一切,決定一切。恰恰相反,情一直被排除在理和理性世界之外,甚至不斷被各種各樣其他理論學說打上“獸性”、“非理性”、“不健康”等烙印,因而使之一直處于文化爭奪、爭論和爭議的渦流之中,或者說,被卷入到了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的博弈之中,不斷被打上各種標簽,唯獨沒有自己發聲的機會。
這種被標簽、被定義、被作為對立面的現象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即便是對情有所偏愛也難免此劫。例如,《文心雕龍》中就突顯了“情與理”相互角力的情景。劉勰一方面不斷呈現情在文學中的張力和魅力,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情動而言形”、“莫不因情立體”,認為“故情者文之經”;另一方面,又擔憂“情數詭雜”,不斷強調“理之緯”的作用。為此,他甚至在《神思》篇中,把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藝術想象也歸結于“思理之致”,以“思理為妙,神通物游”為結。*張光年:《駢體語譯文心雕龍》,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
這種情與理的沖突和張力,一直貫穿于中國文學理論和創作中。顯然,在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之中,情與理的地位和狀態既不平等也不匹配,而是存在著強與弱、乾與坤、天與地、陰與陽之間的差別。情猶如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既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也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而理則處于精神引領的主體地位,體現著絕對理念和終極價值的一端。正是在這種整體性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語境中,情與理的關系失衡了,情不能不受到理、理性的制約,在理與法的規范中寄人籬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中顯得弱勢和孤立無援;而理則能夠借助政治、歷史、哲學、宗教等各種資源和方式,對脾性古怪的情進行引導、矯正和約束,使之能夠在既定的社會制度框架中安分守己,或者在合乎政治、權力、經濟和意識形態需求和利益前提下發揮作用。
情理原本是相通的。有情、順情和尊重情,才能“達理”;而“理”能夠站住腳,服人心,也只有建立在通人性、知人情的基礎之上。由于種種原因,人類社會會出現種種情理不通的狀況。人們或迫于某種利害關系,或由于某種文化規范的要求,不能不壓制內心的要求,不能隨情所愿,反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而正是在這種時候,社會往往就會滋生文化變革的要求,出現思想解放思潮。
可見,情理之間的對峙,也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結果,并非文學藝術本身的情之所愿。而很多藝術家的創作,在很多充滿情感表達的文藝作品中,最終所想達到的就是情之理,或者為天下之情爭一份“理”。
其實,即便在最為激動人心的藝術創作中,情也不能完全離開理。或者說,情與理也不可能完全分離。單就藝術思維活動,或者就人的心理世界而言,情也只是其中一種要素,一個環節,而且在人類現實活動中,很可能是最脆弱、最無力的要素和環節。劉勰對于“立文之本源”的論說,不能不說更為接近藝術文學創作活動的整體狀態:“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劉勰:《文心雕龍》之“情采”篇,張光年:《駢體語譯文心雕龍》,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58頁。而所謂“情學”所面對的問題是:何以在文學理論中,一定要設置這種情與理二元對立的結構?這種對立的二元結構是否真正反映了藝術創作的內在張力?
所謂“文學是情學”,并不是要否定文學中有“理”,甚至討論“情”與“理”的關系如何,而是要打破情與理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在一個情、欲、道、理等多種因素并存的文學世界中,找尋被理、理性和理論壓抑已久的人性元素,使情擁有自己的主體性。
就此而言,情,盡管最貼近人類生命本原,直接源自于人類的本能和原始欲望狀態,也最能反映潛藏在人們潛意識中的能量和能力,激發人們的想象和創造力,但是,由此也注定其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受到種種自然和現實生活的限制,甚至受到壓制和壓抑,難以得到完全和完整的自我實現。這種實現往往只有通過特定對象化、形式化的途徑和方式呈現和展演——而這正是人類文明規范和人文精神源起的張力和悖論所在。文明和文化,一方面會為人類欲望和情感的實現和宣泄提供日新月異的途徑和空間,同時又會不斷以現實的方式規范它,馴化它,試圖把它關在標準、制度、紀律和觀念的籠子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以情動于中”的文學,自然不僅會最先感受到情之驅動力和生命魅力,而且也是最敏感于“籠子”的約束、最早試圖沖破“籠子”的人類活動。
“理”作為人類建構的精神支柱,其文化境遇、待遇和遭遇自然與“情”不同。在人類心理世界和思維活動中,理或許是人類文明規范和規則的體現之一。尤其在中國,理不僅有西方文化中“邏輯”之意,而且擁有合乎道理、規則、制度和權力的近乎天人合一的話語權。因為它是中國古老“禮文化”的抽象化和觀念化升華,集理性、理智、邏輯和道德規范于一身,貫穿于人文歷史的各個領域和環節,自然也成為擁有權力意志和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因素和環節。所以,即便在文學中的理,也是一種更具有廣延性和普泛性的觀念存在,其不可避免體現著整個文化和意識形態、甚至政治和權力話語的意志,對于情及其存在狀態實施監督、規范、修改和統制功能,盡力使個性的、自由的、靈性的文學,為社會的、規范的、集群的功利目的所用。
因此,與“人”一樣,理不僅不孤獨,會出現在不同的文化領域,諸如宗教、歷史、哲學、邏輯、倫理、社會學等,甚至表現在物理、化學、數學等各個自然科學領域,而且一直被尊崇為人文和科學研究中最不可動搖的品質和原則,被認為是達到真理彼岸的最可靠的船艦。這在精神文化領域也從來如此。例如,就西方基督教而言,“信仰上帝以及知曉他是純理性的事情,理性不僅不會與信仰有任何的沖突,而且還會為它提供支持”*[美]所羅門:《大問題:簡明哲學導論》,張卜天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而對于中國傳統道德倫理來說,道德就是一種“理”,只有遵循“理”才能到達至善的境界。而唯獨在文學藝術領域,理遇到了自己難以完全征服的對象。也許在人的生命諸種元素中,猶如其中最頑皮、最不愿被馴化和控制的孩子,最容易惹禍生非,也總是沖破和破壞社會既定的文明規范和社會規則,所以會招致更多的理的警告的規訓,甚至加強理和理性在文學活動中的建構。而在中國,知識理性和宗教理性薄弱,道德理性對于文學的制約和管控就顯得格外突出。
無需論證,人生和人性本身就充滿沖突和困惑。盡管為了重獲平衡和解惑,人類創造和建構了很多理論和學說,但還是無法滿足人們對于情感的向往和迷戀,無時不感受到情感力量的執著和強大。它們時而如萬馬奔騰,時而使人感到萬箭穿心,使人喜,使人憂,使人興高采烈,使人無法入眠。情到深處、烈處、綿延不斷處,人們可以放棄一切世俗偏見,沖破所有既定的現實規范和規則。這時候,任何學說、理論和道理,盡管宏大深刻,面面俱到,似乎也失去了效力,也顯得蒼白,唯獨在藝術作品中方能得到一些共鳴和慰藉。而情學將會在這種人類日益增長的尋求中獲得自己的豐華和新生。
(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周文波作了許多工作,特此感謝)
責任編輯:李宗剛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Yin Guo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s literature may be interpreted and studi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on different levels itself, it therefore provides a curved path for exploring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n, literature and life, and literature and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For, emotion is closest to the life origin of man, and is directly derived from human instinct and, the state of man’s original desire, whereas it reflects most fully the energy and ability hidden in people’s subconsciousness, thus stimulating ma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return of emotion is therefore not only a challenge to the various traditional systems and concepts, but a path for literature to return to human nature and to the masses, especially to the everyday life of man as well. Consequently, the “study of emotion” is not merely an issue in literature, and ma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too, is not merely an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or,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he very opportunity and turning-point to introspect once more the history of human spirit and thought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ore deeply man himself.
literature as a study on emotion;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motion and reason;ADreamOftheRedMansions; Jiao Xun
2016-05-04
殷國明(1956—),男,江蘇常州人,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I02-02
A
1001-5973(2016)03-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