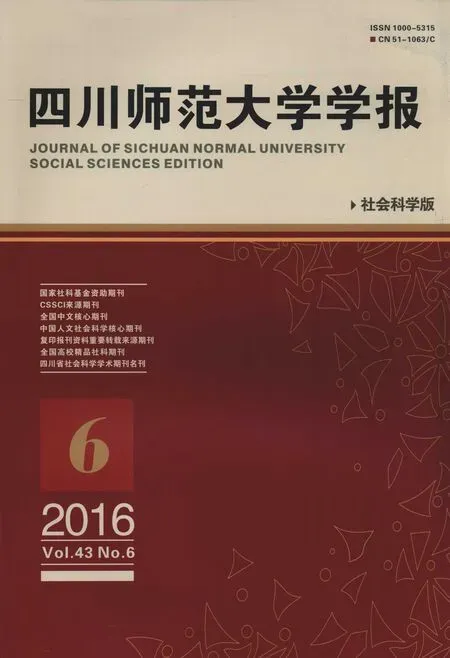黑格爾和“自我意識”的循環性問題
武 瀟 潔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
黑格爾和“自我意識”的循環性問題
武 瀟 潔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當代自我意識理論的首要問題是主觀自我和客觀自我的同一性問題,關于該問題的討論通常認為,反思理論容易導致主體的自我關系的循環性,而這種循環性正是建立自我意識理論的主要威脅。但這僅僅是在主觀意識的層面上討論自我意識。在黑格爾這里,為了表明思維和存在的內在同一性,自我意識被提高到“精神”的層面。精神是存在之唯一的、具體的總體性,在其完全發展的規定中實現自身。存在作為一個整體,表現為精神的自我規定和自我認識,思維最內在的規定性同時就是存在的規定性。精神的自我意識就是精神在其最豐富的內容中與自身的同一。在此意義上,自我意識必然是循環的,因為它是絕對的總體性的自我同一性。
黑格爾;自我意識;精神;絕對;統一性
自我意識問題一直是近代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自亨利希復興了當代對“自我意識”或主體性問題的興趣之后,學界相關的研究汗牛充棟。稍加留意便可發現,目前關于“自我意識”的討論基本上是圍繞主體性問題展開的,因此其意圖也多集中在試圖說明:(個體)自我意識何以可能。這些研究往往把自我意識作為一種意識現象,尤其強調主體如何能夠反思到自身,即通過向內自省來獲得自我意識是否可能。這里就涉及到自我意識的循環性或無限后退的問題。亨利希最早明確提出該問題,并試圖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尋找解決它的思想資源[1]15-54[2]3-28;也有研究者對這種按照反思理論的模式來說明自我意識之可能性的路向不滿,他們把自我意識和主體間性聯系起來,以自我意識為社會交往的產物[3]1-17,但是這個思路并沒有擺脫該問題與主體性的直接關聯,自我意識仍然被視為是在主體性領域中實現的東西。
與此相關,被許多學者所忽略的是,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實際上為解決自我意識問題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理論資源。但黑格爾對該問題的思考并不是直接從“自我意識”概念出發的,而是與他的哲學的基本旨趣相關。在康德通過確定先驗主體的權威而否定思維和“絕對”之間有概念性的聯系之后,黑格爾看到,純粹主觀性具有形式主義的問題,他要在“精神”而非單純主體性的層面重建真正的客觀思維,即在概念中恢復作為存在整體的“絕對”。對黑格爾來說,自我意識在其最基礎的層面上不是任何個體的自我意識,而是“精神”的自我意識或“絕對”的自我意識,它意味著存在在其充分發展了的內容中仍然在其自身之中,存在在客觀概念的層面上就是自我完成的總體。在這個意義上,自我意識必然是循環的,它表示純思維或純概念的具體的、發展了的總體性。
一 問題的緣起
克勞斯·杜辛在其專門研究自我意識的諸種模式的著作中稱,在當代對自我意識的討論中最為流行的一種進路是,對主體的自我表象或自我意識會導致的循環或無限重復的批評,仿佛這是主體性理論的最大敵人[4]97。這個頗具影響力的討論模式就是由迪特·亨利希及其所代表的“海德堡學派”所奠定的,亨利希試圖在當代一片反對傳統哲學主體主義的聲浪中重建主體性,即主體對自身的某種認識關系(das wissende Selbstverh?ltnis)[5]33-34。他認為這個目標的主要敵人就是反思的自我意識,在反思理論的模式下,自我意識會陷入循環,這會使得主體的自我認識不能實現。
首先,亨利希揭示出反思模式下的自我意識理論的困難。在反思理論中,自我通過返回自身,把自身作為對象,建立起一種直接的自我關系,從而獲得自我意識或自我知識。亨利希指出,這種方案必然是循環的,它實際上預設了它只能通過這個返回才能達到的東西,如果自我沒有預先知道自身,它就無法做這個返回,即在這個返回之前,它已經返回自身了[1]20-21。但是如果為了避免循環,聲稱進行反思的主體與反思所達到的那個主體不是同一個東西,那意識的統一就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反思所獲得也就不可能是它自己所期許的關于“自我”的意識,反思本身也失去了意義。
其次,亨利希指出,費希特第一個意識到反思理論的這種循環性,并通過不斷的自我修正試圖建立一個完善的自我意識理論。費希特并不滿足于僅僅停留在把自我意識作為一個奠基性的原則,而是要研究自我意識本身的性質和結構。在亨利希看來,自我意識理論中的關鍵問題是“主體自我”和“客體自我”的同一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費希特把自我理解為設定自身的行動,自我既是它自身,又是設定它自身的行動,即自我既與自身明確地相區別,又與自身相同一,由此,主體既能達到自身同一,又不必預先設定一個自我在那里[1]26。
無論費希特的方案是否解決了反思循環,亨利希所延續的仍然是笛卡爾主義式的“我思”傳統。自我意識還是以主體性的實現為依歸的,這種自我意識往往仍然局限為一種單純的意識現象,就此而言,與反思模式并無區別,都屬于認識論的范疇,反思的自我意識模式不過是一種心理學的錯誤。哈貝馬斯指出:“亨利希所依據的還是他的對手所立足的意識哲學模式,根據這個模式,主體不論是在思考還是在行動,都用一種客觀主義的立場對待對象或事態。而認識論的自我意識對于這樣與客體發生關系的主體的主體性來說具有決定性作用”[6]376。
圖根哈特也對亨利希的策略提出了相似的批評。他認為,在傳統自我意識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就是一種認識論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依賴的就是主客模式,亨利希對該問題的論述正是對這個傳統的延續。他的困難在于,既把主客關系理解為一種知識,即認識與被認識者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堅持關系雙方為同一個東西,這就出現了一個兩難。圖根哈特認為,知識是命題性的(propositional),某一主體的對象并不是另一個實體,不是一般的空間對象,而是一個命題,這是意識關系之所以是意識和對象的關系,而非兩個對象之間關系的本質特征[3]10-12。這就意味著,在一個有內容的意識關系中,一方是一個實體(人),另一方是一個事態或經驗,二者具有根本差別。就自我意識而言,如果自我以其自身為對象,就不能形成任何知識,而要獲得知識,自我和對象就不可能是同一的。這是亨利希堅持自我意識中主客同一所必然導致的悖論。
與此相應,圖根哈特指出,自我意識不是意識關系,而是主體間的社會性關系。但是,圖根哈特擺脫了意識形式,卻并沒有擺脫、也并不試圖擺脫對重建主體性的堅持,無論是社會性的還是主體間性的,都是主體實現自身的活動,不同的只是這個實現領域的范圍的大小,它的立足點仍然是個體自我。
二 黑格爾和自我意識問題的兩個傳統
黑格爾對自我意識的態度和當代討論自我意識這兩種方式都相當異質,但也極易引起誤解。黑格爾并不否認自我意識與主體性的關系,也不否認在主體的意識行動中自我對自身有意向或知識,但是對黑格爾來說,這種意識如何產生、具有什么內容、到底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即自我意識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都不是能夠在單純的意識層面得到直接解決的問題。對黑格爾來說,“自我意識”的真正意義在于“精神”、“理念”、“絕對”這些表示絕對的整全存在具有“自我意識”或最終達到“自我認識”。換言之,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自我意識”在根本上或從廣義上說并不是與其他概念相并列的另一個概念,它只處在其邏輯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相反,黑格爾要恢復被二元論所割裂的世界的統一性,“精神”、“理念”或“絕對”就必須是自我意識的,即實現自身或自我完成的總體性。“自我意識”不是一個主詞,而是一個謂詞,是整體的、精神性的實在的一個謂詞。黑格爾在1807年《精神現象學》最后一章“絕對知識”中明確指出,真正的自我意識是對“精神”的認識,并且“不僅僅是對神的直觀,還是神的自我直觀”[7]426。這就意味著,自我意識必須成為超越了個別自我意識主觀性的普遍反思,它不僅僅是意識的真理,更是絕對的精神和理性的真理,它不是局限在一種意識現象上的東西,而是絕對精神向自身的返回。
黑格爾這樣處理自我意識問題,是建立在對他之前兩個傳統的深刻反省之上的。當時,他關于這個問題至少有兩種現成的選擇:一種是笛卡爾式的,一種是康德式的。
在笛卡爾那里,只有作為思維者的自我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而一切意識都是自我意識的一種。他在“第二沉思”中就明確指出,“自我”對對象的知覺不僅僅是與對象相關的,它同時也是意識到我在進行知覺活動,即對我的主觀心理狀態有明確意識,一切對外部對象的知覺都只能更有效地證明我自己的心靈的性質,而且我對自己的精神比對其它事物具有更清晰的知覺,人類精神的性質比其它事物更容易被認識。由此可以看出,笛卡爾的自我意識是對純粹思維自我的反思或內省,在一些語境下是主體對其自身心理活動的反觀,是把意識本身作為意識的對象,自我意識完全是在主觀意識內部發生的活動。
在關于“自我意識”以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上,康德遠遠超越了笛卡爾。康德認為,進入意識的一切內容都是表象,即便是談到“自我”,也是關于自我的一個表象。它的內容不是關于主體自身的,而是關于進入到經驗中的直觀對象的。這個自我除了一種形式性的邏輯意義之外,并不意味著對作為一個持存實體的經驗主體的知覺。因為無論內部表象還是外部表象都必須借助于同一種直觀,我們不具備另外的直觀可以把對主體的知覺與對其他對象的知覺區別開來,從而能直接把它表象為一個持存的實體。范疇層面上的先驗主體本身是空洞的,只有通過把表象的雜多統一在一個意識中的功能,才能設想自我意識本身的同一性。就此而言,康德的觀念論是相當徹底的,思維規定雖然有其主觀的根源,但它在效用上卻超出了主觀性,因為作為思維駐地的主體是先驗主體,它是一種普遍自我,是邏輯上的形式同一性,經驗中的主體和客體作為對象都在這種先天思維諸規則的約束之下。
這樣一來,笛卡爾所謂的自我意識就瓦解了,由經驗反思獲得的對主體的知覺根本不是自我意識,而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對象意識,因為能夠成為意識對象的主體只能是經驗主體。在康德看來,經驗主體是偶然可變的,它與其它對象沒有什么區別,主體以意向一個對象的方式來對待自身,這與它轉向自身之外的它物具有完全相同的意義,要服從同一套概念規定,這樣的主體毫無絕對性可言。因此,笛卡爾雖然提出了主體性的原則,但是實際上沒有完成對主體之為主體的任何有效規定,主體仍然是物性的。
因此,對康德來說,“我思”、“自我”或“自我意識”等所代表的并不是與“對象”并舉意義上的主體,不是可計數的任何個別存在,而是主體的普遍的形式統一性,是一個懸擬的可能性條件。只有這種主體才能擺脫經驗主體的偶然可變的心理學活動,建立起對象世界普遍必然的可理解性。只有以自我意識的這種形式統一性作為起點,才能證明主體的統一性同時也是關于對象的客觀統一性。
康德雖然仍是從主體一側進入自我意識,但是他以“我思”或自我意識的先驗統一為范疇客觀性的先天來源。他用先驗而非經驗的方式指出,主體之為主體的合法性并不僅僅在其自身,而且在它與對象的關系上,因為沒有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經驗,單純依靠反思就不能獲得對自我的經驗。
在黑格爾看來,康德比笛卡爾規定了更高的哲學任務。笛卡爾只是提出了純粹主觀性的原則,以及抽象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對他來說,確定性比真理更重要,只有思維與外部世界相關聯,才會出現欺騙性的問題,而單純的思維本身則無真假可言,所以思維應當從它自身開始,并從這個思維來推出存在。但是,這樣的“我思”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由此推出的存在也不過就是思維的直接的“自身關聯”[8]73。
康德則要使本身是主觀的東西具有客觀性,即要使思維具有普遍必然的對象相關性。康德不僅僅意識到,思維必須與存在相同一,而不是把存在視為懷疑論的對象,更重要的是,他試圖用概念來規定實在,認為除了這種概念規定之外,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的知識。在康德這里,概念和一般經驗表象的差別不再僅僅是清晰程度上的差別,概念也不僅僅是對觀念的簡單復合,相反,二者具有根本的區別。概念的真正本質在于其統一性功能,它是統覺的綜合統一,概念的統一性是內在于“我思”自身的本源的統一性,是自我意識的先驗統一。
正是這樣一種源自抽象主體(先驗統覺)的邏輯行動為主客統一奠定了新的基礎,正是對主體的這種理解從根本上塑造了之后的整個德國觀念論。在《邏輯學》中,黑格爾就反復贊揚康德在范疇的先驗演繹中已經開始探討純粹概念的本性,“這個統覺的原始綜合對思辨的發展來說是最深刻的原則之一,它包含了對概念的本性進行真正把握的開始,并且與那種自身中沒有綜合的空洞的同一性或者抽象的普遍性對立”[9]22。黑格爾認為,只有概念才能夠真正達到思維和存在的同一,這一點康德已經看到了,并為說明這一點進行了最初的嘗試。
所以,在康德這里,主體的權威實際上是概念的權威,除了先天概念的判斷活動之外,主體不是任何別的東西。而康德之所以把概念放置在先驗的自我意識或“我思”之中,是為了強調那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絕對不是從知覺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它不受感性刺激的左右,而是先天地處在主體之中,自我意識而非經驗才是其來源。只有具有先天來源的概念,才能在經驗中自發地起作用。在康德這里,概念本身高于任何經驗主體的知覺活動,它能夠進行先天綜合判斷,這個判斷不來自經驗,卻能有效地處理經驗。
理性自發地產生出概念,我們借助于這些概念來與世界發生關聯,這是康德為德國觀念論提供的一條基本洞見。把主體和世界關聯起來,個體追求自身與大全的統一,這也是德國哲學由來已久的傳統[10]。然而,康德的概念或范疇仍然是空洞的、無內容的,他雖然要求范疇的經驗運用,試圖為概念獲得內容,但是由于他把整個感性世界看作是和理性(無論是思辨理性還是實踐理性)相反對的東西,是否定主體之自由的東西,所以,世界的同一性僅僅是人的理性綜合的結果,世界的秩序是被知性所規定出來的秩序,是主觀秩序,不是世界自身的秩序,世界僅僅對我們才是可理解的,就其自身而言,我們則無權斷言其合理性或統一性。就此而言,康德只不過證明了主觀性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世界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則不得而知。所以,在康德這里,概念的內容不是概念本有的內容,而是外來的,是由經驗提供的,概念就其自身而言,仍然是空洞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并沒有真正實現,二元論依然存在。
黑格爾并不否認人是在主觀理性的層面上有限地看待世界的,但更重要的是,黑格爾要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有限性是內在于一個整體性的、無限的世界視域中的。所以,我們作為有限的個體,之所以具有合乎理性的經驗,是因為世界本身或存在作為一個整體即是合乎理性的,黑格爾稱這種合理性為概念的形式。世界的可理解性不是主體賦予的(即便這個主體是先驗主體或普遍主體),相反,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這個世界,恰恰在于世界本身就是可理解的,我們主觀經驗的合理性與世界本身的合理性完全是內在一致的。因此,黑格爾必須證明,概念自身就是有內容的,世界的統一性是概念的統一性,思維和存在在概念的總體性中才是內在同一的。
三 精神和自我意識
黑格爾認為,真正的哲學必須以“絕對”為其唯一對象,而康德否認我們對絕對的無條件者具有任何具體的知識,這是黑格爾不能滿意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黑格爾要把主體性發展到極致,似乎黑格爾認為主體理性能夠超出經驗直觀的限制,達到對物自體的認識。這種理解不僅不能消除二元論,還會使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對立更加牢固。對黑格爾來說,“絕對”不是處在某種抽象的主體性對面的東西,而是自己規定自己的。因為存在作為一個概念的整體本身就是思在同一的,存在的統一性是事物擺脫其直接性和有限性,從而被提高到純粹思維的形式中的本性。就此而言,一切真正的哲學都是觀念論[11]142。
但是,存在在思維層面上的統一性,并不是說,存在只有在我們對它的主觀理解中才是統一的,而就其自身而言,則仍然有可能是雜亂無章的個別事物的堆積,這是近代以來主客分立之后才出現的觀點。黑格爾把自在的事情本身視為“純思想”或“純概念”,不是要把存在造成為主觀的東西。相反,世界正是在思維或概念中才是真正客觀的,因為世界只有作為純思想,才能夠發現自身完整的統一性,思想中的統一性是內在于存在整體本身的統一性。如果世界總是在感性經驗遭遇到的雜多中流轉跳躍,那就只會有無限多的有限者,而不會有就其自身而言的存在本身,也就沒有“絕對”。
在黑格爾看來,一切個別的、有限的東西都是世界作為一個絕對的總體中的一個環節,這些環節就其自身而言沒有現實性,不是絕對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都是觀念的。同樣,存在整體在觀念上而不是在經驗現實性中包含著這些環節,這個整體性并不直接呈現給經驗,卻是最實在的東西,因為它揭示了存在的本性,在這個意義上存在是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12]308-309。所以,存在與思維的同一,不是我們的認識與事物本身相符合,而是存在呈現在其內在統一性中,是存在成為一個總體,是存在真正回到自身或與其自身相符合。
黑格爾引入“自我意識”正是要表達思維和存在的這種內在同一性。只存在著一個“絕對”,它既可以被稱為“存在”,也可以被稱為“思維”。但是,這個唯一的“絕對”不是斯賓諾莎意義上的實體,即不是一個可以直接設定出來的絕對的完滿性。如果“絕對”是一個可以現成拿來用的詞匯,那么它和一個空洞的主觀理念就沒有什么區別。因為直接的抽象統一性處在一切多樣性的對面,一切具體的東西仍然在它之外存在著,這種所謂的統一性就是虛假的,本身還是一個有限的東西,不是絕對。
黑格爾反復強調,“絕對”必須是具體的統一,“哲學當然是和一般的統一性相關的,但是不是和抽象的、單純的同一性以及和空洞的絕對相關,而是和具體的統一性(概念)相關,并且在其整個進程中完全只和具體的統一性相關,——它的進展的每個階段都是這個具體的統一性的獨特規定,并且這個統一性的諸規定中最深刻和最終的規定就是絕對精神的規定”[13]459。那么,“絕對”作為一個具體的統一性,就必須經歷一個自身規定了的過程,“絕對”是作為這個過程的結果才出現的。這個過程就是概念的總體。
所以,為了重建世界的統一性,就必須使“絕對”成為一個自身具體的東西,而非抽象的理智設定,于是黑格爾引入了“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意味著理性或精神的普遍內容是完全內在于世界之中的東西。世界的合理性是精神對其自身的揭示和表達,而非主觀理性對外在質料賦予形式。“精神是完全自知并將自身完全表達出來的東西”[7]277。因為,概念或理性在黑格爾這里是純粹思維的總體,是思維對自身進行思維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內容的全體,這個內容是合乎概念形式的內容,而不是經驗內容,“絕對”是一個概念的具體,而非經驗的具體。在這個意義上,形式與內容達到了真正的統一。在概念的總體的層面上,思維和存在本來就是同一個結構,它們沒有主觀和客觀之分,或者說,它們都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
精神就是以概念的運動為其內在要素的絕對的大全,它不是靜止的,而是活動的,它必須在其完全發展了的規定性中實現自身。“精神的發展就是自身超出、自身分離,并且同時是自身回復的過程。……舉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發生的——永恒地發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時間之內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認識其自身,使自己成為自己的對象,發現自己,達到自為,自己與自己相結合”[14]28。所以,存在作為一個整體,是精神性的,是屬于普遍理性的,存在整體的一切內容都表現為精神對其自身的關系,是精神的自我意識或自我認識。只有在精神的層面上,二元論才能得到克服。
這樣一來,世界的無條件的總體性就不再是主客體的外在相合,而是絕對精神的自身統一性。真正的絕對是“精神”,精神是具有自我意識的概念總體,它在其外化中也都是在其自身之中,世界的全部豐富性都是精神的豐富性。只有把自我意識提高到精神,黑格爾才能證明,沒有對立的雙方,只有一個唯一的存在,就是理念,這個理念是實在的。
所以,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序言”中提出關于實體和主體關系的著名論斷時,表面上看,他是從實體出發,而非從主體出發,實體最終會表明自己是主體,是“履行著絕對精神的生活的”主體。但是,從根本上說,黑格爾要解決康德的問題,要超越一切形式的斯賓諾莎主義,他就既不能從主體出發,也不能從實體出發,既不能從主觀性出發,也不能從客觀性出發,唯一有效的立足點只能是那個絕對的總體性。這個總體性不是在一開始就完成了的,而是一個漫長的概念運動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能夠表明,思維和存在其實是同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具有“概念”和“實在”兩類名稱。
至此,可以說,黑格爾并不是要用“自我意識”概念來重塑主體性的絕對權威,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近代哲學尤其是康德的先驗學說那里看到了主觀性的根本局限。如果范疇只是經驗的形式規定,也即我們理解世界的工具(即使這個工具是思維先天從而普遍地具有的),那么世界永遠也不可能被把握為一個整體。知性要么在脫離外部世界的抽象理念中打轉,要么必須借助于直觀來達到對象從而受制于這個直觀。黑格爾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總是糾纏于思維到底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而是必須首先考察純粹思維的內容本身,這個內容會向我們表明,純粹的思維或概念自身就是思在同一的。在思維最內在的意義上,它必然和存在是一致的,存在在其最徹底的整體性上必然是概念的總體,而非感性經驗的總體。
所以,黑格爾通過把自我意識賦予作為最高實在的“精神”,使精神成為理念與實體相統一的真正方式。一開始,精神將自身表現在意識中,這是精神要獲得現實性的必經階段。但是,在這些對象性的意識中,意識和自我意識或者實體與主體是分裂的,精神最終要實現自身為唯一的實在,就必須揚棄這種差別。它要證明,意識的任何形態都具有自我意識的形式,換言之,意識與其對象的關系都是精神與其自身的關系。可見,只有通過將自身實現為這樣一種自我意識的關系,“絕對”才能消除自身的彼岸性,成為哲學的唯一對象,黑格爾對康德二元論的克服才有可能實現。
由此可見,在精神的層面上,自我意識才是可談論的,而且恰恰是在精神的層面上,自我意識必然是循環的。因為“絕對”、“概念”或者“精神”都是無限的整體,只有整體才是最充分的自身同一性,是在最普遍的意義上回到自身的東西,是最徹底的直接性。在這個意義上,精神當然是循環的,它的循環性不僅不是一個問題,還是必要的,因為精神是那個唯一的具體的總體,它不僅是一,還是一切。而自我意識就是指“絕對”從一個抽象的直接性向最終完成的總體性的前進,這種前進表現為一種返回,是從抽象的形式同一向具體的總體的返回。所以,在黑格爾把自我意識提升到精神的層面上之后,反思理論的循環性問題就無法進入我們的討論視野了,因為它還是主體意識范圍內的循環性,把該理論作為自我意識問題的最大敵人只能是對該問題的貶低。
[1]Dieter Henrich. Fichte’s original insight[C]//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vol.1.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2.
[2]Dieter Henrich. Self-consciousnes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J]. Man and World, Feb.1971,vol.4.
[3]Ernst Tugendha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M]. Translated by Paul Ster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6.
[4]Klaus Düsing. Selbstbewusstseinsmodelle: Moderne Kritiken und systematische Entwürfe zur konkreten Subjektivit?t[M]. München:Fink, 1997.
[5]Dieter Freundlieb. Dieter Henrich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he return to subjectivity[M]. Hants:Ashgate, 2003.
[6]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M].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G.W.F.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M]. Hamburg:Meiner, 1999.
[8]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9]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Zweiten Band). Die Subjektive Logik (1816)[M]. Hamburg: Meiner, 1981.
[10]布爾喬亞.德國古典哲學[M].鄧剛譯,高宣揚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Erster Band). Die Lehre vom Sein(1832)[M]. Hamburg: Meiner, 1999.
[12]G.W.F.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Mit den mündlichen Zus?tz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13]G.W.F.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M]. hg. F.Nicolin u. O.P?ggeler.Hamburg:Felix Meiner, 1959.
[14]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責任編輯:帥 巍]
Hegel and the Circle of Self-consciousness
WU Xiao-jie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primary issue of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identity of subjective ego and objective ego.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take the circle of subject’s self-relation caused by reflection theory as a main threa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ory. Self-consciousness is in this way discussed only on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or Hegel, in order to solve the immanent unity of thought and being, self-consciousness is lifted to the level of spirit, which is the only concrete totality of being and realizes itself in its fully developed determinations. Being as a whole shows itself as 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knowledge of spirit, the deepest determinations of thought is also the ones of be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spirit is the self-identity of spirit in its richest content. In this sense, self-consciousness is bound to be circulate, for it is the self-identity of absolute totality.
Hegel; self-consciousness; spirit; absolute; unity
2016-07-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2015年度項目“承認的政治與法的形而上學:黑格爾早期法哲學思想研究(1788-1807)”(15YJC720017)。
武瀟潔(1987—),女,山東濟寧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外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德國古典哲學。
B516.35
A
1000-5315(2016)06-0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