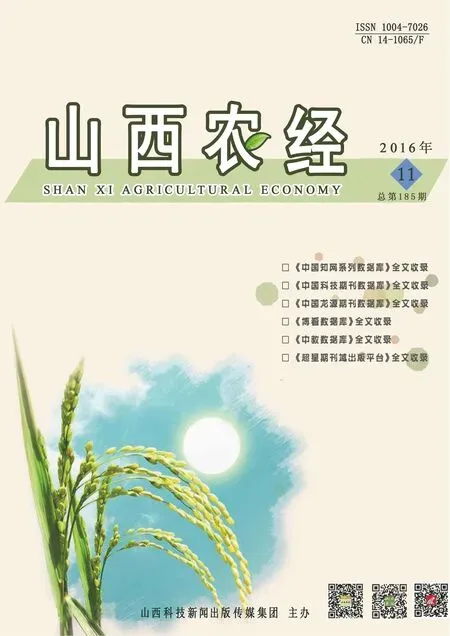農地征收中集體角色之轉變
□喻晶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西南昌330038)
農地征收中集體角色之轉變
□喻晶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西南昌330038)
主體“虛位”、村委會意志與集體意志的背離導致了集體在當前農地征收中處于弱勢地位。在“經營性征收”中,集體這種角色定位難言正當,“經營性征收”的目的是將土地用于商業開發,其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和豐厚的土地財政收入,卻犧牲了集體和農民的利益。當前,“經營性征收”已獲得相關政策承認,當務之急是對其進行改革。通過施行“征補分離”改革,賦予集體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讓集體獲得公平的補償。同時,政府采取出售被征土地的發展權保障土地財政收益,實現多方共贏。
征收;經營性征收;集體;征收補償
農地征收是當前改革的熱點,土地征收為城市經濟騰飛帶來了充足的燃料,政府、用地單位以及城市居民分享了征地的巨額紅利,但是農民的利益卻被嚴重漠視。土地作為農民最重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被低價征收后,必然導致農民生活和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勢必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引發社會的不穩定。征地補償,尤其是基于商業開發的征地補償過低,已經成為當前農村社會矛盾頻發的根源之一。我國農村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所有,在征收中集體應當是與征收者利益博弈的重要一極,而現實情形卻是集體在征收中沒有發揮出其應有之地位和作用,使得集體和農民的利益落空。集體在當前的農地征收中處于何種地位,這種地位是否具有正當性,當征收的目的不再具有純粹的公益性時,集體的角色應當如何轉變,成為本文思考的重點。
1 農地征收中集體角色之現狀
1.1征收中集體處于弱勢地位
我國尚未制定專門的土地征收法律,有關土地征收的規定散見于《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根據這些法律的規定,土地征收程序由政府主導,土地征收過程中集體處于弱勢地位,缺乏意思自治能力,其表現為:
1.1.1集體不享有征收同意權。《土地管理法》第46條明確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即是否征收以及征收土地的范圍由政府單方面決定,征收不是契約關系,集體不享有征收同意權,政府采取行政強制的辦法剝奪了集體意思自治的權利。1.1.2征收補償協商機制缺失。《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征地補償與安置方案由政府批準、擬定和實施。國土資源部頒布的《關于開展制訂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區應當制定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區片綜合地價。實踐中的做法為:地方政府綜合考慮被征收耕地的類型、質量、農民對土地的投入、農產品價格等因素,將農地劃分為不同區域,不同區域統一補償標準。在土地尚未決定是否被征收前,其補償標準已經確定。政府繞過市場機制,通過行政手段給土地定價,無需與集體協商。
1.1.3征收補償異議機制缺乏保障。法律雖然規定政府公告征收補償方案后,集體有權對公告表達意見,但是未規定如果雙方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集體享有終止征收的權力或者通過司法程序獲得救濟的權利。同時《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即便對征地補償方案有異議也不影響征地方案的實施,無疑導致征收補償異議機制喪失約束力。
綜上所述,農地征收具有強制性,在農地征收中,集體和政府不是平等的交易主體,而是一種行政管理和服從的隸屬關系。這種角色定位和我國學界的一種觀點相輔相成,即征收是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力,是典型的行政權行使行為,征收雙方屬于行政法律關系。
1.2集體弱勢地位生成之原因解讀
1.2.1主體“虛位”是集體弱勢的重要原因。我國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法律沒有明確定義何為“集體”。依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民事權利性質,所有權主體“集體”理應屬于民事主體的一種,但系何種民事主體卻缺乏定論,通說認為集體既不是自然人,也非法人和其他組織。性質的模糊致使“集體”這一概念在現實中難以找到對應的載體,因而“集體”在土地征收中無法發揮所有權人的職能,從而喪失與政府進行博弈的能力。
1.2.2村委會意志與集體意志的背離致使集體喪失了話語權。由于集體的“虛位”,為了經營管理集體土地,法律規定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鄉鎮集體經濟組織作為集體土地的經營管理者。這些經營管理者不是“集體”的“代表機構”,而是“代理機關”,他們在代行所有權時是否遵循以及如何遵循“集體”的意志不無疑問。村委會成員的選舉是在地方政府指導、協調、監督下進行的,地方黨委能夠直接任免村委會干部,村委會仍然受到政府行政行為的強力干預和控制。在土地征收時,村委會往往以貫徹執行政府的意圖為責任,難以和政府發生博弈,集體在征收中必然喪失話語權。
1.3集體處于弱勢地位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征收是國家對私人財產權利的合法侵犯,根據現代所有權理論,所有權受到社會福祉的限制,土地所有權的社會義務意味著土地所有權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征收正是基于公共利益對土地所有權的剝奪。這種具有行政強制性的財產轉移,必然致使集體處于弱勢地位。
同時,在土地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土地所有人可能通過壟斷性標價而獲取“租金”,并可能將交易成本抬高到難以接受的程度。在此情形下,國家通過征收防止私人“漫天要價”,從而克服自愿交易的障礙,防止土地所有權人壟斷,以免延誤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阻礙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在征收中限制集體的意思自治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將集體角色定位為弱勢的行政相對人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
但是,征收中集體處于弱勢地位之正當性的前提為公共利益。當征收的目的不具有純粹的公益性時,這種正當性必然受到挑戰。我國的征收實踐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征收制度——“經營性征收”,這種基于商業目的而進行的征收是否具有公益性,其中集體角色應當如何定位,無疑值得我們思考。
2 “經營性征收”的非公益性與集體角色的轉變
2.1“經營性征收”是法律對土地嚴格管制下的產物
“經營性征收”,又稱為商業征收,是指基于商業目的而征收土地。“經營性征收”是實踐中的特殊產物,其產生源自法律對土地的嚴格管控。現行法律規定農村土地除用于農業、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以及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外,不得用于商業開發。這致使城市工商業用地只能使用國有土地,而現有國有土地存量難以滿足經濟迅速發展的需求。征收集體土地成為解決上述矛盾的鑰匙,這導致大量的集體土地通過征收轉變為國有土地,然后進入土地流通市場用于商業性項目,潘多拉的魔盒由此打開。國家對土地嚴格管控的初衷,在工商業發展對土地極度渴求下,在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經濟利益驅動下被逐漸扭曲。“經營性征收”系變相的土地買賣,以犧牲集體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無疑是一種畸形的制度產物。
2.2“經營性征收”與征收目的之齟齬
法律明確規定征收的目的是公共利益,但何為公共利益卻沒有明確的規定,學界也存在爭議。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2011年出臺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一次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界定,即將公共利益明確界定為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利益,并將其類型化:國防和外交需要;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公共事業需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需要;舊城區改建需要。
比照上述規定,我們發現相當數量的土地征收非基于公益。從客觀上看,“經營性征收”具有一定公益性,因為工商業項目的建設,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實現了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但是它所實現的公益過于泛化,對公益的實現過于間接,較之國防、公用事業體現的公益標準太低。而農村土地是集體成員生存的基本保障,承載著全體國民的糧食安全利益,就利益衡量的觀點來看,農地自身的公益遠遠高于商業項目帶來的微薄的公益。就主觀目的而言,用地單位進行土地商業開發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用地單位自身之利益,促進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發展僅僅是附帶客觀效應。同時農地的城市化也不等同于農民的市民化,城市化的根本目標是解放農民身份的束縛,使之得享城市的紅利。“經營性征收”的目的不具有純粹的公益性。
2.3重新定位“經營性征收”中集體之角色迫在眉睫
“經營性征收”以征收之名,行土地買賣之實,在“經營性征收”中用地單位獲得巨額利益,而集體和農民卻被徹底排斥于土地增值收益之外,僅僅獲得征地前三年土地平均年產值一定倍數的補償,這些補償就土地增值紅利而言可謂是九牛一毛。農地是農民生產和生活最基本的保障,當農地被征收后,農民的就業問題、社保問題、生存問題接踵而至,同時“經營性征收”的非公益性也為民眾所詬病。
但是徹底禁止“經營性征收”也難言合理,因為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急需大量土地作為助推燃料,禁止“經營性征收”,必然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極大阻力。同時,“經營性征收”為地方政法提供了財政資金,是舊城改造、土地整治、耕地保護等公益資金的重要來源。如果禁止“經營性征收”,地方政府難以支撐公共和公益事業所需的巨額資金。
這導致問題的解決陷入死循環,一方面其違反征收的目的,農民難以接受,另一方面“經營性征收”有社會所需求的正效應。因此改革“經營性征收”,重新定位集體角色,提高征地補償數額,讓集體和農民也分享“經營性征收”的巨額紅利,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3 “經營性征收”中集體角色轉變的改革路徑
重新定位集體角色的目的在于尊重集體所享有的財產權,使集體和農民在征收中得到合理的補償。在“經營性征收”中,有必要賦予集體平等的法律地位,使集體獲得一定的話語權,從而成為征收中博弈的重要力量。結合各地征收之試點改革,筆者構想了一種“征補分離”的改革模式,即延續政府對土地進行征收的傳統模式,但是補償由用地單位與集體直接協商談判,法律不限定最高補償額。
3.1“征補分離”模式的具體制度設計
3.1.1改革征收程序。對征收程序進行改革,實現征收主體和征收補償主體的分離。筆者設計的土地征收流程為:由政府做出征收決定,將相關土地的土地發展權拍賣給用地單位,然后用地單位與集體進行補償談判,再由政府進行土地征收,將土地使用權移轉給用地單位。政府不再介入征收補償的具體事務,僅僅對征地補償方案進行監督和審查,用地單位直接承擔補償義務。這種征收模式與現行的土地征收模式不同在于:現行的土地征收模式中的征收人和補償人都是政府;已廢止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規定的拆遷人和補償人皆為開發商;筆者提出的征補分離模式,實現了征收人和補償人的分離,征收仍然由政府施行,補償改由用地單位施行,防止了違法征收的發生。同時,政府通過出售土地發展權,保障了土地財政收益,實現了政府、開發商、農民集體的共贏。
3.1.2改革補償協商機制。實現征收補償的自由談判,并將征收補償協議作為征收的前提。征收中,集體仍然不享有征收同意權,征收的決定和征收的實施由政府強制執行。但是賦予集體在征收補償談判中意思自治的權利,征收補償方案由集體與用地單位共同協商達成,沒有達成補償方案,政府不得先行征收土地。如果雙方分歧較大,難以達成補償協議,可以通過仲裁、訴訟等方式確定征收補償的數額,直到征收補償數額確定,并且賠付到位后,政府才能進行土地征收,最大限度地維護集體和農民的利益。
3.1.3修改法律對補償限額的規定。我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這為用地單位和政府合法剝奪集體和農民的土地權益提供了制度依據。該補償僅僅是對土地收益的補償,而且限制為不超過土地年產值的30倍,對土地本身價值的補償沒有提及。如果不取消法律對補償最高限額的規定,集體和農民始終難以得到合理補償。同時應當就“經營性征收”補償的最低限額加以規定,防止暗箱操作或者某些用地單位利用強勢地位,產生新的不公平。
3.1.4改革征收補償方式。實踐中土地征收補償方式已經實現了多元化,大致形成了貨幣補償、留地補償、用地單位安置補償、社會保險安置補償等多元補償機制,但是仍然沒有擺脫以貨幣補償為主的模式。貨幣補償乃一次性發放,著重考慮了被征地農民眼前的生活安排,難以滿足失地農民可持續性發展的需求。應實行土地入股補償為主輔之以貨幣補償的補償方式,在以被征收土地入股后,用地單位利用土地所獲得的收益,農民也得以分享。而且這種收益并非一次性獲得,而是一種長效的補償機制,防止了通貨膨脹或者部分失地農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就業技能,失去土地后難以就業,生活無法保障的困境。
3.2“征補分離”模式的優勢
“征補分離”模式是在不改變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對征收制度進行帕累托改進,它具有如下優點:首先,由政府向用地單位出售土地發展權,地方財政利益受到的沖擊較小,防止了地方政府對改革的抵觸。其次,由政府進行征收,能有效監管土地的用途,防止耕地被濫占為建設用地。最重要的是,實現了集體角色的轉變,集體在征收補償談判中獲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能有效地保護集體和農民的合法權益,讓失地農民也能分享土地發展之收益。
結束語
實施征地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失地農民的利益,讓農村和農民也能分享改革之成果,提高土地補償金成為解決問題的思路之一。而土地補償金應增加多少,其增加的程度能否跟上當前社會發展之步伐,甚至有可能新的補償標準出臺沒多久,就由于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物價的提高,而致補償價款之相對值嚴重縮水。既然如此,何不賦權于集體,轉變集體角色,在“經營性征收”中讓集體進入市場與開發商自由談判,通過博弈獲得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價格,而政府也可通過出售土地發展權獲得財政收入,真正實現征收改革之初衷。
[1]劉勇.物權法草案第49條應當取消[J].政治與法律, 2006(4):129.
[2]高飛.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2:116.
[3]邵彥敏.“主體”的虛擬與“權利”的缺失——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7(4):34.
[4]李一平.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利益受損的制度分析與對策[J].中州學刊,2004(2):146.
[5]陳小君.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現實考察與研究:中國十省調研報告書[M].法律出版社,2010:5.
[6]房紹坤,王洪平.論我國征地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規范模式[J].當代法學,2006(1):70.
1004-7026(2016)11-0010-03中國圖書分類號:F301.2
A
本文10.16675/j.cnki.cn14-1065/f.2016.11.008
江西省社科基金項目“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視域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法律制度研究”(10FX29);江西科技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科研計劃項目“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農民合作社的理論探索與制度設計”(2014XJZD011)。
喻晶(1982—),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師范大學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