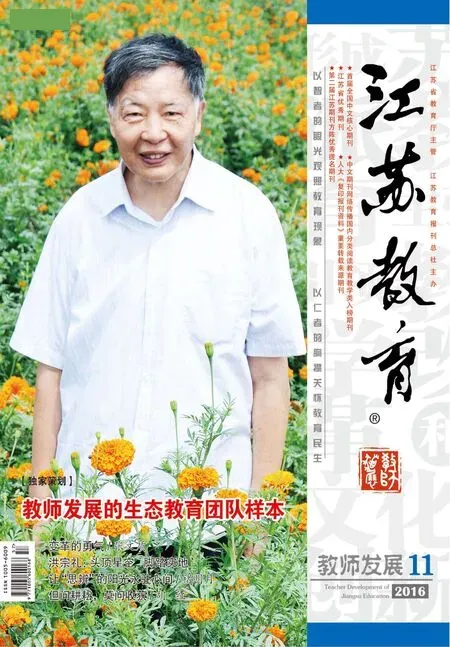改變教師:讓學習看得見
林曉斌
改變教師:讓學習看得見
林曉斌
在“促進有效學習”的新一輪課堂改革中,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一線教師的教育理念與行為,一直是學校教學管理者的難題。溫州市繡山中學嘗試推出“讓學習看得見”的課堂變革,以“青春合伙人”的形式,通過建構開放的課堂組織形式,建立平等信任的師生、生生關系,借助呈現學生思維的媒介,推進多元的評價機制等四個角度的變革,引導教師在可見的課堂學習過程中,重新認識科學的教育理念,進而重構理念與教學行為。
課堂改革;青春合伙人;讓學習看得見
“幫助所有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習慣和能力”成為新一輪課堂改革的目標,教育界人士紛紛從關注“教的方式”轉向關注“學的方式”,從運用學習科學理論、推行合作學習、推進多元評價等角度,為“促進有效學習”做出指引。但不同于專家、學校行政人員,一線教師因繁重的教學任務,往往習慣于既有的教學思維,懶于接受新理念。因此,教學理念的改變和重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約翰·哈蒂教授(John Hattie)在《可見的學習》中指出 “在學校中為了幫助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結果,我們需要可見的學習。”“可見”具有兩層含義:一是讓教師看得見學生的“學”,教師始終知道自己的作用;二是讓學生看得見教師的“教”,學生逐漸成為自己的老師。
為此,我校提出“讓學習看得見”的課堂改革嘗試,試圖從以下四個角度改變教學模式,促成教師從理念到行為的改變。
一、建構開放的課堂組織形式,讓學習看得見
學生看得見教師的 “教”,教師看得見學生的“學”,其關鍵在于建構課堂開放的組織形式。這種開放的模式,不只是師生互動,還在于生生互動。
傳統的課桌椅面向講臺的方式,有其先天的優勢:教師與學生都可以看到對方的面部表情,互相了解當下的學習情緒及狀況。但對于需要自主學習與合作解決問題的學生而言,其排位單一,生生無互動。為此我校采納了更合適的課堂模式:按照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均衡地將4至6人分為一個小組,面朝講臺,三面圍坐,每位學生編上了ABCDEF或123456的代號。課堂在進行教學或學習活動時,每位學生充分進行自主的思辨學習后,以不同的身份、學習任務、評價要求進行小組合作交流,同時向全班同學進行成果展示。
這種組織形式的實施動搖了教師的課堂主導地位。事實上,原來的排位方式無法讓教師關注到班級的每一位學生,更不能關注到學生的學習狀態與心理反應,并及時調整相應的課堂教學。如今各個小組自主合作學習,學生之間互相交流,進行思維碰撞,教師則以“干預者”的身份出現,在課堂巡視中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在小組展示時給出指導與評價。在應運而生的學習小團隊中,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學”的過程清晰可見。
與此同時,我們撤了講臺,在教室左前方設置一張與學生桌同高度的教師書桌,放置電腦及投影儀。此舉從形式和心理上消除了師生之間的藩籬,讓教師真正走到學生中去。開放的課堂組織形式,優化了學生的學習過程,讓學習看得見。
二、建立平等信任的師生、生生關系,讓學習看得見
在小組合作學習的課堂中,為了體現小組合作的功效,教師會根據不同的學習能力給學生編號。在展示環節中,學生A的準確回答得分是1分,以此類推學生D和學生F的回答分別是4分和6分,此舉最大效益地發揮“小教師”的作用。
在觀察山東省泰安市實驗學校、天津市普育學校的小組學習時發現,雖然組員間的指導、交流非常頻繁,但是學生A對全組成員特別是學生F的管理與指導,不難看出帶有“居高臨下”的態度。同時,每個小組的回答展示,都會成為一節課的量化分數。那么為了小組榮譽,是否會讓學生陷入分數泥淖不可自拔?小組與小組之間,是否會少了很多的分享?組員與組員之間,是否會多了標簽意識?
為此,課堂組織形式的變革,教師地位的變化,對師生與生生關系提出了嚴峻挑戰。《可見的學習》中,哈蒂教授認為課堂應該是“允許錯誤發生的安全環境”。于是我校推出了“青春合伙人”的小組合作模式,強調組員在平等基礎上進行不同的分工。只有在班集體中建立平等、信任、安全的人際關系,才能讓每位學生、每個小組在接受學習任務的挑戰時,愿意將自己的思維呈現與分享,使學習看得見。
三、借助媒介呈現學生思維,讓學習看得見
國內課改初期,我們的目光曾集中在杜郎口、東廬的“學業紙”“導學案”教學模式,當時人教版的初中語文教材也配備了“學案”,從預習到練習,從背景資料到遷移拓展,教材中都有詳細的編寫。然而“學案”與紛繁的同步作業本、課時特訓等內容大同小異,給學生增加了思維干擾與學習負擔,已被一線教師棄用。
英美國家課堂的“A paper”、香港的“學業紙”學案形式的自編教材,引起了我們的關注。在研究山東省泰安市實驗學校的“學習單”、天津市普育學校的“任務單”時發現,在理念的改變下,這張“紙”變得真實有效。“學業紙”不同于統一的“學案”,而是每位教師根據學情與教學目標,對統一的教學內容做出“適切的教”的呈現。教師借此將自己的教學重點、難點以及教學內容,通過挑戰性任務(問題、活動設計)及成功標準(要求)等呈現在學業紙上,通過學生的先行學習、小組互助交流、展示討論結果等環節,完成教學目標。
同時,“學業紙”也是學生“學”的呈現。沒有“學業紙”的背景下,教師難以了解學生先行學習的狀況,也難以掌握學情,更難以開啟課堂“學生已經掌握的不教,學生自己學習或互助學習可以掌握的不教”的旅程。而對于學生而言,獨立完成“學業紙”的第一輪自主思考與學習,并將之訴諸筆端,既是一種思維的呈現,也是對教師教學行為的一種反饋。
于是,我校推出的“學業紙”包含助學資料、預習提綱、課堂內容及活動設計、課后練習等,改變原來“教”做先導的學習模式,使學生的“學”完全看得見。
四、推進多元的評價機制,讓學習看得見
最終實現“讓學習看得見”,除了以上三個“支架”,還需要一種能夠體現“先行學習”的多元理念,體現教育本原與長遠目標的評價體系。
把學生的“學”呈現出來,就需要教師在鼓勵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的同時,具備組織與領導能力。把教師的“教”呈現出來,需要教師真正改變教育理念。教師在備課環節下足功夫,不僅編寫出科學的“學業紙”,保證“學習挑戰”的適切性,還要激發學生對“學習挑戰”的積極性;同時教師在課堂中要關注學生呈現的思維,隨時了解學生學習,并給予準確、及時的評價。
因此,我校嘗試在學生評價中,以學科素養的形式,增加日常學習活動中“青春合伙人”小組展示的量化分數占比,鼓勵學生提升各種能力;在教師評價中,以過程性評價替代“問責制”,根據測驗結果來表揚、懲罰或獎勵教師,鼓勵教師為學生營造一個安全透明、充滿信任的學習氛圍,等等。
以上四個方面,無論是顯性的課堂組織形式、學習媒介,還是隱性的人際關系、評價體系,都滲透著“認知加速”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形式的改變(教師的行為)最終促進了內容的改變(教師的理念),教師在“讓學習看得見”的課堂改革中,感受到學困生在團隊互助下學習主動性的明顯提高。
對于教育均衡背景下的義務教育學校,相較于生源的不可控變量,教師屬于可控變量,因此推進課堂改革,實現輕負高質,關鍵在于重構教師的理念與行為。“讓學習看得見”的課堂改革,改變了教師,進而成就“促進有效學習”。
[1]約翰·哈蒂.可見的學習——最大程度地促進學習(教師版)[M].金鶯蓮,洪超,裴新寧,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5.
[2]李明尚.小先生制,讓課堂更高效[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
G451.6
B
1005-6009(2016)57-0037-02
林曉斌,浙江省溫州市繡山中學(浙江溫州,325000)校長,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