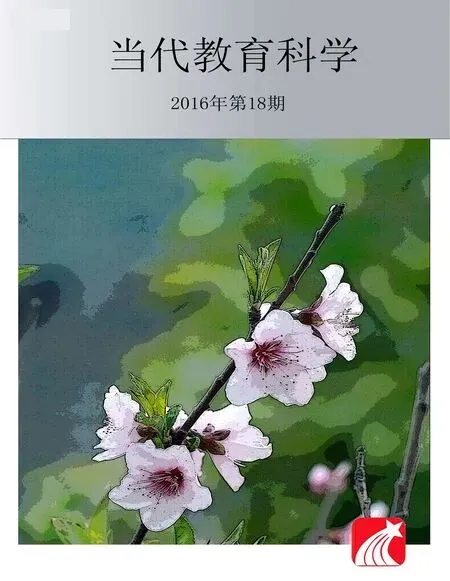愛與規訓:圖畫書中的兒童教育省察
● 杜傳坤
愛與規訓:圖畫書中的兒童教育省察
●杜傳坤
提供給兒童閱讀的圖畫書中隱含著成人的童年假設與教育觀念。圖畫書中兒童因違規受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聽話”而非“無知”,兒童規訓的實質亦在于此。故事中的懲罰從嚴厲到溫情,并不意味著對兒童野性馴化的節制。愛的手段化降低了兒童的抵抗意識和反抗能力,提高了規訓的有效性,童年越來越標準化。愛不應成為規訓兒童的另一副枷鎖,愛應該是將兒童從規訓中解放出來的偉大力量。
愛;規訓;愛的手段化;兒童教育;違規與懲罰
作為一種成人給兒童講述故事的方式,圖畫書典型地反映了成人的童年假設與教育觀念。作為近現代童年閱讀的重要藝術形式,兒童圖畫故事文本提供了童年研究的新路徑。本文選取了19世紀中期前后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風靡全球的部分兒童圖畫書,其中有榮獲德國“最知名兒童讀物”的《蓬頭彼得》、《馬克斯和莫里茨》、《邋遢麗澤》,以及當代屢獲圖畫書大獎的三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英國佩特·哈金森的“比利”系列之一《比利得到三顆星》,美國大衛·香農的“大衛”系列《大衛,不可以》、《大衛上學去》、《大衛惹麻煩》,英國約翰·伯寧罕的《愛德華——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之所以選擇這類重在講述調皮兒童“違規”與“受罰”的圖畫故事,因其蘊含著近現代以來孩子的野性與成人文明秩序之間對抗沖突又相互妥協的深刻關系。考察兒童的違規行為和成人對待違規的態度及應對方式,意在分梳和反思其中的童年觀念和兒童教育方式的嬗變與機理。
一、兒童的違規與懲罰
通過對頗具世界影響力的圖畫書的歷史考察可以發現,兒童的違規從“惡作劇”逐漸變為“小淘氣”,違規的嚴重程度明顯降低。“惡作劇”意指戲弄或捉弄別人,故意使他人陷入窘境,并從觀賞他人的尷尬、吃驚、惶恐等情緒中得到樂趣,可能會造成始料未及的嚴重后果。“淘氣”具有頑皮、愛玩愛鬧、不聽勸導之意,其反義詞是老實、乖巧、聽話等。與一個半世紀前的馬克斯、莫里茨們相比,當代圖畫書中大衛、愛德華們的違規行為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馬克斯和莫里茨的惡作劇都頗具震撼效果:吊死并偷走寡婦的四只雞、鋸開裁縫羊師傅門前的橋讓其落水、往蘭珀老師的煙斗里放火藥引起爆炸、捉瓢蟲放在弗里茨大叔的被褥下面、偷面包師傅的復活節面包、割破農夫的所有糧袋。這些頑皮行為在今天看來都屬“聳人聽聞”,情節嚴重。大衛、愛德華的違規則主要體現在不想吃煎蛋、上課吃口香糖、挖鼻孔、不會把房間整理干凈、忘記刷牙洗臉、看動畫片太晚、不注意聽講、吃飯不排隊、合影時做鬼臉等。兩相對照,大衛們的違規行為絲毫沒有前述惡作劇的震撼性,顯得太過普通平常,同時違規的技法也不如前者更具創造性。當然,這種比較只是更清晰呈現違規的樣態,既非鼓勵兒童的惡作劇,也不是贊賞兒童的小淘氣。
其次,兒童違規的后果或者下場也截然不同。馬克斯、莫里茨的七個惡作劇,以及麗澤砸壞農婦的雞蛋、把農場的蔬菜當雜草拔掉、裝神弄鬼嚇走女仆等,這些行為不但造成他人經濟損失,還導致了身體傷害甚至生命危險,涉及德性問題,確實堪稱“惡”作劇,令人憎惡。然而大衛和愛德華的違規很少是對他人利益的侵害,更達不到此種程度的傷害,很難說是道德善惡層面的問題。同時,這些行為對淘氣者本人也沒造成多大危害,不像彼得們玩火自焚、掉進池塘、被大風刮走等嚴重的自我傷害。但是這些小小的淘氣仍然屢屢被師長們喊“不”進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懲罰。
再者,對待孩子的違規,成人采取的態度也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懲罰的嚴厲程度和懲罰對象兩方面。成人對待彼得、馬克斯、莫里茨們的違規,采取的是毫不客氣近乎嚴酷的修理,對頑皮孩子的遭殃表現出無動于衷的冷漠甚至幸災樂禍。對那個因吮手指而被剪掉拇指的孩子,故事不擔心媽媽會心疼,反而寫“叫他怎把媽媽見”,[1]好像孩子應該為此而羞愧。對待馬克斯、莫里茨的毀滅,村人的反應也看不出多少憐憫:“這真是件悲慘的事兒!但他們完全是自作自受”、“只怪他們太頑皮,還總喜歡捉弄別人”、“感謝上帝,那些亂七八糟的惡作劇終于結束了。”[2]其實這倆孩子的毀滅分明是成人有意為之,故事中文字與圖畫呈現背離關系,互相拆臺,文字講著面包師傅、農夫和磨坊主的“粗心”,可畫面清楚呈現他們就是“存心”要置這倆調皮鬼于死地。譬如農夫用鏟子把一孩子塞進糧食袋,同時雙腿還緊緊夾住另一孩子免得被其逃脫,而文字寫的卻是“兩個孩子也被粗心的默克裝了進去”。文圖之間的張力增加了趣味性和戲劇性,更透露出成人真實強烈的嚴懲態度。而麗澤被撞骨折住院之后,故事也沒有表現同情,反倒慶幸“現在惡作劇終于可以停止!”[3]
但是當今大衛、愛德華們的淘氣下場,幾乎卻是毫發無損。例如同樣的違規行為結局就明顯不同:在捉弄動物這件事上,彼得們踢小狗結果被狗咬傷,臥床養傷還要喝苦藥水;大衛拽小貓的尾巴,僅被喊“NO”。在不好好吃飯這件事上,彼得們瘦得一命嗚呼;大衛不想吃煎蛋,還可皺著眉頭抗議“我必須要吃嗎”,而且也沒導致身體絲毫的“貴恙”。在不講衛生這件事上,彼得們吮手指,被剪掉大拇指;大衛挖鼻孔只是被媽媽喊“不可以”。可見對兒童違規的懲罰越來越有節制,懲罰之后往往還伴隨著愛的擁抱、愛撫與獎賞。
懲罰對象也逐漸從可見的身體轉移到內在的心靈情感。彼得們和馬克斯、莫里茨遭受的懲罰基本都是針對肉體的:被剪掉拇指、被狗咬傷、瘦得一命嗚呼、玩火自焚、掉進池塘、被大風吹走、被汽車撞成骨折、被磨成小碎粒成為家禽的美食等等,而且在這些懲罰過程中基本看不到受罰者與施罰者的感受,大人孩子似乎都是無動于衷。但是到大衛就有了內心情感的觸及,甚至是以情感懲罰為主了,如大衛面壁思過時流下的眼淚,放學被老師留下打掃衛生時的難過與尷尬。[4]雖然在懲罰過程中身體也都參與了,但這些強制性的行為都是對違規者自由的剝奪,身體本身已不再是懲罰的對象,而只是藉以懲罰情感的媒介。讓大衛真正在意與痛苦的是媽媽和老師“愛的撤銷”,而非面壁和勞動自身。因此懲罰變成“能夠使兒童認識到自己的過錯的任何的東西,能夠使他們感到羞辱和窘迫的任何東西:……一種嚴厲態度,一種冷淡,一個質問,一個羞辱,一項罷免”,[5]認識過錯、羞辱和窘迫皆屬于心靈或情感上的痛苦,而成人采取的諸如冷淡、質問、羞辱等方式也迥異于拳腳棍棒式的武力懲罰。
此外,實施懲罰的主體更為隱蔽,受罰變得更像一種“自然后果”。彼得和莫里茨們受到的很多懲罰雖然也具有“自作自受”的性質,但有時懲罰方式和程度明顯跟懲罰主體的“主觀意志”相關,比如拿著大剪刀健步如飛沖進屋里的裁縫,毫不客氣剪掉了康拉德的拇指;身穿紅色長袍的巨人尼古拉先生,眼睜睜把嘲笑黑孩的三個孩子塞進墨水瓶;面包師傅、農夫默克和米勒師傅的懲罰更是“無法無天”,竟然把馬克斯和莫里茨放進火爐、裝進口袋、磨成顆粒喂了家禽!然而,大衛們受到的懲罰主要與其對既有規范和紀律的觸犯直接相關,懲罰主體即使現身,也只不過是一個無辜的“執行者”。譬如《大衛上學去》中,老師之所以讓大衛放學后留下來打掃衛生,是因為他違背了幾乎每個孩子都事先知曉并接受的“規范”和“守則”,換句話說,懲罰大衛的并不是老師本人的主觀意志,而是這些“規范”和“守則”,甚至懲罰方式和程度也是可以預測的。受罰因此變成一種“自然后果”。這樣一來,“由于懲罰在形式上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不會顯得像是某種人世權力的武斷后果。實施懲罰的權力隱蔽起來了。”[6]懲罰主體隱藏到“自然的溫和力量背后”,因而讓受罰看上去更具有必然性和客觀性了。
那么,從“惡作劇”變為“小淘氣”,兒童違規嚴重程度的降低意味著什么?成人通過懲罰想要兒童認識到的是一種什么過錯?懲罰的節制與溫情意味著控制程度的降低,還是一種新的規訓手段的創制?
二、兒童規訓的機制與實質
兒童違規從“惡作劇”到“小淘氣”,嚴重程度的降低不能簡單歸因于今天的孩子更少野性。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這源于一種規訓的機制。
首先是兒童惡作劇所需時空條件的缺失。彼得們玩火柴、吮手指、暴風雨天出門等都是在無成人監管的情況下發生的,馬克斯和莫里茨亦是避開成人來實施一系列的鬧劇,他們有足夠多的自由支配時間,能在生活空間里找到足夠的工具材料,包括鋸子、火藥和瓢蟲,而這一切條件大衛和愛德華們具備嗎?他們主要的生活空間似乎只有家庭、學校和幼兒園,他們的環境是按照現代教育原則精心設計過的,清除了一切無關與危險的元素。他們也總是處在成人的視線之內,隨時被提醒被喊“NO”。大衛們的時間是被細致規劃好的,幾點到學校,幾點睡覺,在什么時間應在什么地點干什么事情都是規定好的。大衛們沒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沒有更多自由活動的空間,當然也就沒有更多自由支配的行動。這意味著,兒童違規的時空條件改變了,從自由時空變為被計劃控管的時空,受到成人更多的規劃,他們不具備彼得、馬克斯和莫里茨所擁有的惡作劇的時空條件。兒童的這種“圈養化”現象,也是現代教育制度確立以來兒童較為普遍的生存狀態:“兒童被越來越多地劃分在通過專門指定地點、單獨設置的環境、專人監督并且按照年齡和能力構建起來的空間中……甚至許多兒童的閑暇時間也常常被框定了。”[7]這一過程也被稱為“童年的制度化”。
其次是成人對違規過程的監控使得兒童違規的“完成度”降低,嚴重后果被避免。彼得、馬克斯們的惡作劇基本都能有始有終地完整實施,并沒有成人在彼得們玩火柴、鞭打大狗、暴風雨天出門時及時制止,因此也沒有給故事中的兒童提供吸取教訓改過自新的機會,彼得們或被燒成灰或被風吹走,麗澤被撞骨折,馬克斯和莫里茨被磨成碎粒。相反,大衛們的父母和老師都會及時看到并干預他們的違規。麗澤爬上蘋果樹摔下來傷己又損人,而大衛踩著椅子去拿高處的餅干桶時還沒摔下來就被媽媽發現并且喊“NO”了。也因此,大衛和愛德華們的頑皮不會導致過于嚴重的后果,因為在導致嚴重后果之前就被成人監控到并制止了。成人從監督兒童活動結果轉變為監督活動過程,這是控制模式的改變,也意味著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可見,從彼得故事到大衛故事,成人是從缺席到始終在場,對違規過程的監控使得兒童違規的“完成度”大大降低,違規過程被中止避免了嚴重后果的出現。
最后是新的規范標準界定的生成。大衛們的違規盡管對人對己造成的傷害都微乎其微,但仍然受到懲罰,細究之,是因為他們偏離了文明社會為“好孩子”制定的規范。盡管規范的內容會隨時代情境而變,但其中很明顯的一個趨向就是,規范的力量越來越貫穿在紀律當中,“其中涉及時間(遲到、缺席、中斷)、活動(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熱情)、行為(失禮、不服從)、言語(聊天、傲慢)、肉體(‘不正確的’姿勢、不規范的體態、不整潔)、性(不道德、不莊重)”。[8]福柯從規訓化社會歸納出的這些失范內容,在大衛和愛德華的淘氣行為中大都可以找到,因此對他們喊出的“NO”主要是一種規范化裁決。這個“不規范”領域的邊界并非如法律般清晰,所以大衛們動輒得咎。然而并不能由此證明今天的孩子更喜歡犯規,因為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正是今天的紀律與規范更為繁瑣和無孔不入,因而才評判出更多的違規。同時,這些違規也可能是對過度規范的抵制,就如福柯所言,“正是由于這些繁瑣的紀律,最終導致整個‘文明’遭到抵制,‘野性’從而產生”。[9]
兒童違規的時空條件越來越有限,違規的過程被隨時監督和干預,對違規標準的界定由損人害己變為對人對己都無多少危害的“偏離規范”,這些都是施行于違規兒童的規訓機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規訓機制的運作,兒童違規的嚴重程度才大為降低。兒童的違規從“惡作劇”變為“小淘氣”,是對兒童實施規訓的結果。
從彼得到大衛,兒童受罰的原因在于違規,而違規的實質在于“不聽話”。要求孩子要“乖”、要“聽話”,這一點在大衛時代和彼得時代幾乎是一致的。很大程度上,現代社會中違規的孩子主要錯在“不聽話”而非“無知”。大衛的媽媽在懲罰因在屋里打棒球而碰碎花瓶的大衛時重申:“我說過,大衛,不可以!”[10]彼得故事的首頁有首說教詩,第一句即為“如果孩子很乖乖,圣誕老人就會來”,書中的十個小故事幾乎都在重復著要孩子聽話的教導以及對不聽話的修理。馬克斯和莫里茨也被指責“不愿意聽智者的教誨”,麗澤得到的教訓同樣是“你總是不聽話”。而要求孩子聽話并給予獎賞,對不聽話予以懲罰改造使之變乖,某種意義上正是兒童規訓的實質。
通過一則童話故事的版本變遷,可以更清晰看出聽話觀念的現代起源。與彼得故事同時代的格林童話《小紅帽》里亦可找到類似的教導:出門之前媽媽就囑咐她不要離開大路,不要停下來跟陌生人說話,但是小紅帽沒有遵從,結果被野狼吞吃了。被獵人營救之后她總結出這樣的教訓:我以后再也不要不聽媽媽的話,一個人離開大路到小路上去了。這與更早的17世紀末夏爾·貝洛的《小紅帽》形成鮮明對比:小紅帽出門前沒有得到媽媽關于危險的任何教導,最后被大野狼吞吃了。所以貝洛版的小紅帽是為她的“無知”付出了代價,而格林版的小紅帽是為她的“不聽話”付出代價。[11]格林童話代表了當時主流的兒童教育觀:孩子是無知的,但無知不要緊,只要聽大人的話。在這里,成人世界與童話故事所建構的兒童世界之間的差異已經概然有別。對成人來說,自柏拉圖以降的理性主義傳統規定了,生活問題完全出于對生活原則的悖逆,即無知,相反,知識即美德;對兒童來說,生活問題則主要出于對成人世界規定的生活原則的悖逆,即不乖,或不聽話。由此,孩子因為天真無知而要乖乖聽話的觀念開啟了近現代兒童教育的規訓之路,西方從彼得一路延續到今天的大衛、愛德華們,我國當代亦有大量“糖衣藥丸”式、旨在培養“聽話”式好孩子的訓誡類作品。從中可以看出,成人對于兒童有意違逆既定規則的態度始終沒有妥協。
需要指出的是,福柯的規訓理論對童年研究確實啟發良多,但這一理論的借鑒也容易忽視兒童規訓的特殊性。監獄、軍隊、工廠、醫院和學校都是現代社會隔離與規訓的場所,然而處在家庭與學校、幼兒園這一場域中的兒童,他所接受的規訓與犯人、病人、士兵、工人等的規訓還有所不同:兒童接受的不僅僅是規訓與懲罰,而是有“愛”交織其間的規訓與懲罰。這種愛主要是母愛或“類母愛”(比如“教育愛”),兒童對其極為渴望與在意。當代對大衛們的懲罰往往伴隨著擁抱、愛撫以及愛的語言,這種溫情脈脈的愛的懲罰,往往更能觸動兒童的心靈與情感,其力道遠勝于簡單的體罰和說教。因為后者只是“動手”、“動口”的教育,前者卻是“動心”的教育。有時這種愛的懲罰甚至會以兒童自我懲罰的方式實現,比如大衛否認蛋糕上的黑手印是他干的,夜里卻從噩夢中驚醒,向媽媽承認“是!是我干的!對……不起。”[12]然后才在媽媽的愛撫中安然睡去。噩夢可視為兒童將成人的既定規則內化認同之后,用以對違規的自我懲罰。近現代以來兒童故事中的成人越來越溫和且具有教育藝術,柔和的敘述就像母親的話語,而這種轉變被認為是從格林童話開始的。詩化的風格,撫慰人心的母性語調,可以建立起“信賴的氛圍”,使讀者的想像經歷一種“似乎非傷害、非教育性、非人為操縱的馴化過程”,[13]從而也更容易掩蓋其馴化的目的。這是否意味著,當愛變成一種教育手段,對兒童的規訓會更為有效?
三、愛的手段化與童年規訓的有效性
大衛聽到的“大衛乖,我愛你”與小紅帽、彼得們得到的“要聽話”的教訓有什么區別嗎?“乖”與“聽話”幾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大衛還得到了媽媽明顯的愛。而在小紅帽和彼得們的故事里,這種愛不太明顯也未發揮多少作用。需要追問的是,當孩子日益變成經濟上無用而情感上無價的存在,當現代教育中融入了對孩子更多的愛之后,成人對兒童的管制是更加寬松了還是更為嚴厲徹底了?
如果說故事里權威專制的男性語調還能激起兒童的抵制與反抗,故事里溫和的母性聲音則輕易就能將孩子融化進無限愛意之中,使其喪失反抗意識與反抗能力。譬如,愛德華在成人的呵斥聲中尚能以變本加厲的違規進行無聲的反抗,他因為踢東西被成人指責是世界上最粗魯的男孩,從那天起他就變得越來越粗魯,在一系列的指責中他成為“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但是當成人對愛德華的同一種行為給予陰差陽錯的賞識,結果就完全不同了:他躲在拐角處伺機把一桶水潑到小狗身上,主人卻說“謝謝你幫我把這條渾身都是泥巴的小狗洗得干干凈凈”,夸他“對動物很有愛心”,從此愛德華就變得越來越有愛心,在一系列的賞識中不知不覺就變成世界上“最可愛的男孩”。[14]再如那個不想去幼兒園的小妖怪比利,他以亂七八糟的畫、可怕的歌聲和嚇人的亂舞來抗拒成人要他去幼兒園的要求,但是高明的老師不但沒有訓斥,反倒找出恰當的理由稱贊并獎賞給比利“三顆星”,[15]于是比利就從死活不肯去幼兒園變為死活不肯離開幼兒園了。可見,小刺頭們最終都被成人溫柔地收服,成為成人期待中的樣子。但同時,變成“可愛男孩”與“好寶寶”的愛德華和比利們,也失去了自身鮮明的個性特色,變得和其他兒童沒有什么區別,或者說像其他孩子一樣普通和標準化了。
孩子的不乖就這樣被成人的寬容和賞識之“愛”悄無聲息地化解了,跟《蓬頭彼得》里剪去孩子拇指的剪刀相比,兩者之間或許只是“無形的剪刀”與“有形的剪刀”之區別,它們都是要修理掉孩子的不乖。而這把“愛”的無形剪刀,對孩子的掌控更加有力。“乖”與“愛”,可謂是近現代以來兒童教育過程中的兩個關鍵詞。成人的一句“大衛乖,我愛你”,也預示著在“乖”與“愛”之間建立了聯結。“愛”是對“乖”的獎賞,也是教化“乖”的手段,愛的給予和撤消其威力遠勝于說教甚至體罰。當“愛”成為教育的一種手段,無論是親子之愛還是教育愛,兒童往往更容易乖乖就范,在故事結尾變成一個“好孩子”,同時讓故事外的小讀者分享和認同這一標準化的童年。現代的兒童故事在教化方法上顯示出無限的創造性,但在規訓童年的觀念上卻一以貫之的保守。
這種有效規訓甚至使得兒童的違規也越來越像成人期待中的樣子。成人在對大衛們的違規行為說“不”的同時,又分明表現出一種審美的趣味。盡管大衛做了那么多違規的事情,但仍讓人感覺他是個可愛的孩子。成人一方面在修正孩子的小麻煩、小問題,一方面似乎又在欣賞兒童的小淘氣。毫不含糊的修理態度表明對違規的反感和零容忍,也隱含著對失控的擔憂和焦慮;審美的態度則暗示了成人勝券在握的自信。大衛的故事里或許有讓孩子安心的東西:即使像大衛一樣做出那些違規的行為,媽媽和老師依然會愛我。但故事也暗示故事外的小讀者:你們在大衛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鏡像”,產生了共鳴,你們就像大衛一樣,都是幼稚的,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無法自己管理自己,需要成人來訂立規則,時刻監督和指導,否則你們就會不斷地闖禍、犯錯誤甚至傷害你們自己。由此觀之,故事也在說服孩子相信自己就是那個樣子,從而明白聽話的重要性,同時也確信即使自己時常犯點小規也仍然可愛,“真正”的孩子都是這樣的,這有點悖論地顯示出成人既要孩子擺脫“不成熟”又想讓孩子維持“孩子氣”的矛盾心態。無論如何,當兒童連違規也越來越像成人想像和期待中的樣子,意味著兒童規訓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因此成人在面對孩子違規時才會有一種從容的心態去審美。
當教育以愛的名義施行,教育的有效性獲得了最大限度的保障。19世紀后半葉隨著想象力的解放與對啟蒙理性的深入反思,文學曾經質疑過以現代文明教化一個男孩的必要性。柯洛迪和馬克·吐溫分別從兩個方向上展開思考并做出選擇:小木偶皮諾喬接受了教化,克服天真與道德的“瑕疵”成為真正的男孩,小哈克則拒絕了文明的教化。[16]其后對教化的質疑卻很快被如何教化的熱情所取代,兒童故事也陷入對教化手段有效性的敘事探究之中。然而,方法與手段遠不是兒童教育的最核心問題。施之于比利和愛德華的那些手段完全可以用來讓孩子成為相反的情況,即用來讓孩子變成“壞”孩子與變成“好”孩子同樣有效。所以手段方法本身無所謂好壞,它所服務的目的才是更根本的,那就是:我們要把孩子引向何方?想讓孩子成為怎樣的孩子?是借助高明的手段讓孩子成為我們所希望的樣子,還是幫助孩子成為他自己?盡管現代圖畫故事中不乏超越規訓的嘗試,顯示出童年想像的更多可能性,但是把從規訓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安置在何處,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還很初步。
野性十足的違規故事長期以來始終流行,既受到孩子的青睞又得到成人的認可,這一事實及其原因也頗值得玩味。對于孩子們而言,或許是故事里的彼得、馬克斯們替他們做了現實中他們想做而不被允許做的事情,釋放了內心撒野的渴望又不會受到實際的懲罰,故而喜歡;如果現實中的兒童都像妖怪國度的比利一樣可以無所顧忌地撒野,這樣的故事就不會有太大吸引力,由此也反證了馴化兒童的現實環境始終存在。但成人也從未一勞永逸地馴服兒童,否則就不會持續需要這類故事提供訓誡。可見,孩子們一直在嘗試挑戰既定的秩序和規范,成人也一直沒有放棄規訓兒童的努力,規訓與對規訓的抵制始終處在一種張力之中。然而,完全出自天然本性的“親親”與“慈幼”對于人類的文明而言似乎也是不夠的,所以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都在探索如何在尊重兒童天性的基礎上施之以理性教育,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主要關注了有效性,而忽視了對教育前提基礎與要義的思考,最終使愛也淪為了教育的手段。
愛的手段化是教育現代性需要深刻反省的重大問題。當兒童被認為是成人加工塑造的對象,成人對兒童的所謂“愛”不過就是一種更為精致的加工方式;當兒童被認為是成為成人的必經之路,成人對兒童的所謂“愛”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更好保障;當兒童被認為是有著柔弱心靈的需要被規訓者,成人對兒童的所謂“愛”不過是顯得更加人性化的控制。兒童世界的“愛”的生產與整個教育現代性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愛是一種關系品質。……有愛的教育事實上都是將教師與學校教育、將教師與學生放置在一種關系之中,放置在彼此最真實的生命存在中。因此當教師去愛學生的時候,他不是把學生當成對象去愛,而是為了愛去愛。愛本身就是愛的理由,此外無它。這不僅決定了教育的本質,也最終決定了人對于人是什么和意味著什么。”[17]愛的這種關系品質亦適用于親子之間。愛應該被視為教育自身的目的和依據,而不僅僅是教育的合理外衣或教育的某種正當名義。
總而言之,考察近現代以來與兒童違規有關的圖畫故事書,會發現其中隱含著成人對于童年野性馴化的歷史,同時也包含著兒童試圖挑戰規范跳脫文明秩序的抗爭。愛的手段化標志著現代教育的有效性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這只是教化方式方法的高明,其中想要規訓兒童的目的并未見根本改變,這正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在任何意義上,愛都不應成為規訓兒童的另一副枷鎖,恰恰相反,愛應該是把兒童從規訓中解放出來的偉大力量,幫助兒童成為他自己,去過一種幸福而有意義的生活。
[1][德]海因里希·霍夫曼.蓬頭彼得[M].衛茂平譯.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14.
[2][德]威廉·布什.馬克斯和莫里茨[M].楊密譯.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20.
[3][德]基利·施米特·泰希曼著、查理·格賴弗納繪.邋遢麗澤[M].楊密譯.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19.
[4][美]大衛·香農.大衛上學去[M].余治瑩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5][6][8][9][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202,118,201-202,330.
[7][英]艾倫·普勞特.童年的未來——對兒童的跨學科研究[M].華樺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33.
[10][美]大衛·香農.大衛,不可以[M].余治瑩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11][加]培利·諾德曼.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M].劉鳳芯譯.臺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3.278-279.
[12][美]大衛·香農.大衛惹麻煩[M].余治瑩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3][16][美]杰克·齊普斯.童話·兒童·文化產業[M].張子樟校譯,陳貞吟等譯.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2006.90-91,135-139.
[14][英]約翰·伯寧罕.愛德華——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M].余治瑩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
[15][英]佩特·哈金森.比利得到三顆星[M].高明美譯.臺北:阿爾發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17]高偉.愛與認識:對教育可靠基礎的追問[J].教育研究,2014,(6).
(責任編輯:劉丙元)
杜傳坤/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