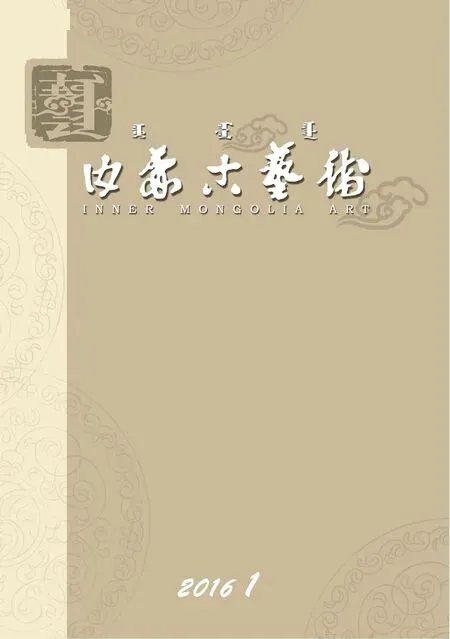從“三圈說”看少數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認同
譚福潔(呼倫貝爾市群眾藝術館呼倫貝爾021000)
從“三圈說”看少數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認同
譚福潔
(呼倫貝爾市群眾藝術館呼倫貝爾021000)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直接使得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宣傳、學習和交流的機會,不但擴大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同時也大大地增強了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這種社會的火熱發展形式的產生主要是由于文化與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體,以科學發展觀來看待“非遺”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培育和形成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要內容的文化產業,緊密拉動內需,進一步推動文化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而對于非遺的保護和繼承來講,政府的主導作用十分明顯,但是群眾的協助作用也十分關鍵,實現社會化參與,形成合理的長遠規劃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前提條件之一。
《中間圈》一書作者為中國著名學者王銘銘。書取名為中間圈,既與“中外”之間的地帶有關,又與費孝通在雞足山上對于自身的“英美式”社會科學生涯流露出的反思有關。作者借中間圈,將思考社會科學中諸如“社區”“社會”“文化”“民族”“國家”“族群”等諸多“單位”的局限性,對社會科學加以反思。本文通過“三圈說”的理論來淺說它與“非遺”中的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
《中間圈》中有關于“藏彝走廊”的提出,背景如下:1978年,費孝通在全國政協關系民族識別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在給“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研討會”的信函中費老提出“藏彝走廊”這個學說的最后闡述。他提出,之前對民族的研究只以獨立的某個民族為單一的研究對象,而不去研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主張應該按照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來進行綜合研究。在2003年,費老將這一學說最后總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問題。
費孝通先生提出,根據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可以將中國劃分成6個板塊,三條走廊。這6個板塊分別是:北部草原地區,東北高山森林地區,青藏高原地區,云貴高原地區,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三條走廊是:藏彝走廊,南嶺走廊以及西北河西走廊。這樣劃分,就打破了歷史上按照行政區域劃分的規則。而呼倫貝爾正屬于北部草原地區。
借用費孝通先生的一段表述:“這個走廊是漢藏,彝藏接觸的邊界,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過政治上拉鋸的局面。這個走廊在歷史上是被稱為羌、氐、戎等名稱的民族活動的地區,并且出現過大小不等、久暫不同的地方政權。現在這個走廊東部已是漢族的聚居區,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區。”藏彝走廊地處青藏高原的東南部,是橫斷山區、怒江、金沙江瀾滄江三江并流處。它是以康定為中心,向東和向南延伸的這一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眾多,文化多樣性大,是多元文化區。
這一個區域內,歷史上民族遷徙頻繁,有很多民族和支系在這里繁衍生息。由于處于山區地帶,地理狀況的特殊性,很多古老的民俗被保留下來。歷史上,有很多民族是從北方遷徙過來的,例如彝族,納西族,羌族,這些民族在他們口頭的史詩或者傳說、習俗中都被記錄下來。在彝族語支的傳說中就有“送魂”的傳說:在送魂的儀式中,送魂的路線會選擇沿著河流往北走,回到祖先來之前的地方。
在今天西南各民族的史詩傳說中,尤其是一些民族的“送魂”傳說,可以認為兩大流域間一些古代通道的變化與這種同一古代民族內的不同支系部落間的沖突也有關系。由于強敵擋道,有的部落只得跨流域遷徙,到另外一個地區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費先生指出的“政治上拉鋸的局面”,也就說明是漢、藏、彝族之間長期存在的“禮”與“戎”的關系。這類關系有著自身的內在涵義,而民族間的關系造就了所謂的“局面”,則可能將除卻這三個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比如:氐族、羌族)當作各自的“邊緣”席卷到“局面”之內。通過禮尚往來及市場交換意義上的物品交換與政治意義上的征戰——抵抗來實現。在藏彝走廊上,不同宗教、不同物品、不同勢力的分離與交織,為我們研究文化接觸、沖突與并存造就了一個內容豐富的“文化區”。
從非遺的角度看,核心圈就是我們研究的漢族農村和民間文化。而核心圈之外就是屬于少數民族地區,其中也包括內蒙古自治區。
中間圈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地帶中,居住方式錯綜復雜,不是單一民族的,是因人口流動,自古也有與核心圈的東部漢人的雜居與交融。這個圈子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西部”基本一致,但也可以說是環繞著核心圈呈現出來的格局,在東部,一樣有自己的地位。
從歷史時間看,中間圈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至近代國家疆界確定之后,居住在這圈里的主要人群便被稱為“少數民族”了。少數民族這個稱呼是50年前才有的,是晚近的發明。古代則不一定得到“中間圈”這個稱呼,這個圈子與外圈結合著,有時是內外的界限,有時屬于外,有時是內外的過渡。至于這個圈子與核心圈的交往,自古也十分頻繁。中國有幾個重要的朝代,也是所謂中間圈的部落勢力創建的。可以認為,核心圈與中間圈之間的差異,恰在于地方行政是否實現了其對地方的直接控制,而這個標準,又與兩圈“教化”程度的差異有關系。
通過這本書,對我啟發如下:
“藏彝走廊”以及“三圈說”的提出,不僅對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遺產學等學科有指導意義,對內蒙古呼倫貝爾的俄羅斯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俄羅斯族是俄羅斯移民的后裔,屬東斯拉夫人的一個族群。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在中國俄羅斯族的總人口為15609人。總體上看,生活在中國的俄羅斯族人數較少,多散居于西北和東北的沿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的邊境地區,只有在內蒙古的額爾古納市,俄羅斯族的居住才相對較為集中,設有全國唯一的俄羅斯族民族鄉。在民族鄉以外的其他地區,也居住著人數和比例都很大的俄羅斯族居民,一般都可以形成民族圈或民族社區。由于相對集中居住、交往交流和本民族內方便通婚等原因,使許多俄羅斯族的風俗習慣得以保留下來,在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性情性格等方面,基本上延續了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和特點。所以說,額爾古納市,是我國俄羅斯族居民重要的聚居區,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俄羅斯居民的代表性居住地區。
生長在邊境地區的俄羅斯族,生活在俄羅斯文化與漢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間,導致今天的俄羅斯族文化中,不但有本民族的文化歷史,也有漢族、甚至是蒙古族、達斡爾族(通婚的結果)等等的文化摻雜其中。
有人說:移民永遠是文化上的失落者,而第一代移民尤其如此,第二代略好,直到第三代才真正開始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第一代的移民只好在兩種不同文化的邊緣游離,文化認同就變成了一個國際問題。今天國際關系的熱門話題既不是意識形態的沖突,也不是領土爭端,而是民族、宗教等因素所產生的沖突,而在這些因素后面的核心概念就是文化認同。可以預料,文化認同將使得這個世界的秩序發生深刻演變。
通過看這本書,我覺得文化認同,對我們自身也是有分層的。在每一個地方,我們每個人的位置都不一樣。我們的參照物不同的時候,層次也會隨之改變。比如,某人可以說他是漢族,他是浙江人,他是南方人,但是不論最后怎么變化,最后都會歸為他是一個中國人。而移民原因造成的民族,對自我的認定就常常會在大環境中有疑問。外界的不認可和自我認可之間的矛盾也常常存在于每一個跨界民族的內心并產生疑慮。
中俄邊境處于邊緣地帶,邊緣地緣往往保留和延續的是最古老的原生態文化。同時邊緣地緣也往往是文化與歷史的沉淀帶,邊緣也多文化交匯,文化也較寬容與開放,這與“三圈說”理論正好是吻合的。那里有草原,原始森林,河流眾多,地形較之平原地帶要復雜得多,以農牧業為主。一些原始的民俗猶在,節日儀式、婚喪嫁娶的儀式、宗教信仰等等都沒有過多的改變。在這些留存的儀式中,蘊含著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如何讓這些民族的文化保存下去,如何為俄羅斯族的定位做出一點貢獻,我認為中間圈的理論框架是最好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