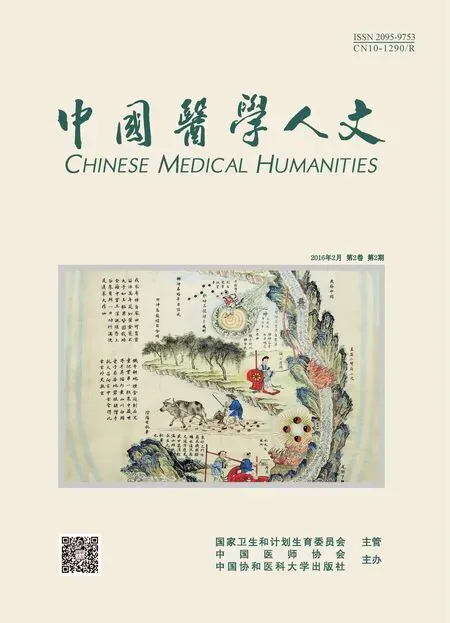本能的生 快樂的活——我的抑郁筆記
文/堯 戈
?
本能的生 快樂的活——我的抑郁筆記
文/堯 戈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醫學部
出院不久,我就在微信上看到了一條令人痛心的消息。“距簽約工作11小時前,24歲北郵研究生孫某在宿舍樓上縱身一躍……”相同的年紀、同樣的學歷、相似的經歷,讀完文章不由地驚出一身冷汗。“你出了一個我永遠無法破解的謎題,我日夜后悔遺憾自責思考探求,但你不留痕跡不愿透露”——死者女友。是的,我想這是很多人的疑問,平日里表現那么優秀的小伙子怎么就選擇了這樣一種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答案是抑郁癥!
一方面,我能一定程度地理解孫某為何會做出這種選擇。因為前不久我也患上了抑郁癥,抑郁的時候常有生不如死的念想;另一方面,我也在內心里不斷暗示自己:這是一種懦弱的選擇。雖然現在寫出了這篇文章,我仍不敢說自己戰勝了抑郁,因為一直還在服用一些抗抑郁藥物。但是,我想說的是:抑郁并非是不可戰勝的,勇敢地活下去并努力與之對抗才是人生路上真正的勇士。孫某的事讓我想到了自己在抑郁住院期間認識的一位病友博易(化名)。
博易是一位長期重度抑郁癥患者,像我這種體會過中度抑郁的人已經覺得是病痛難忍,他的痛苦可想而知。博易是云南宣威人,從高中時就患上了慢性抑郁癥。經過自己驚人的毅力和堅持,考取了西南財經大學,不幸的是,大學期間抑郁再次發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辦理休學艱難地熬過了一段時間,最后不得不選擇退學接受全面的治療。他給我講起自己的病情是這樣說的:“每次抑郁來襲,感覺好像生命的氧氣被斷掉了,一種強烈的窒息感讓人生不如死。”為了對抗抑郁帶來的強烈的自殺念頭,博易選擇了一種外人看來相當極端的方式——自殘。他的兩臂、大腿、背部、腹部有大大小小八九個米字型劃痕,加上他的疤痕體質,使得他在自己身體劃過的疤痕顯得格外的刺眼;手腕上的劃痕已經成了一種網狀結構;左手食指被自己切斷了一截。最開始接觸的時候,我不解地問:“你是有多么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答案讓我愕然:“這么多疤痕并不意味著我要選擇死亡,而是因為我想活下去,在強烈的輕生念頭時只有這樣做才能緩解這種不好的念想。”博易對抗抑郁的方式并非簡單的自殘而已,在他的空間里有一篇五萬字的日志《平淡平凡平常》,開頭這樣寫道:“一個人,九十九天,我從宣威市龍潭鎮第二中學的家里走到了拉薩。曾經三次自殺未遂的年輕人想要去尋找新的人生,于是便往那更藍的天空走去。我出發了,然后,我到達了。”這篇日志目前為止已經被贊了近七千次。這是博易對抑郁的挑戰!在他將要出院和我告別時跟我說,“我打算去支教,要有意義地活著”。我說,“還要嘗試去快樂地活著,祝你出院后一切都好!”
我在不久之前也患上了抑郁癥,所以對于孫某輕生的念頭并無太大的詫異。理解歸理解,但是我還是想說:“生是一種本能,更是一種尊嚴!”面對抑郁,我的選擇大概比較有代表性:求助!求助于師友,求助于父母,求助于醫生。現在的我雖然并沒有完全將抑郁驅逐,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緒在一天天好轉。有時想想之前輕生的念頭會淡然一笑,有一種滑稽的喜感。人生真是奇妙!生命仍然美好!
談起住院感想,首先要從如何生病說起。“我有抑郁癥!我怎么可能有抑郁癥!我沒什么可抑郁的。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說我非常樂觀。我這種人要是有抑郁癥,那——全省人民大概都有這個病。”李蘭妮在自己的《曠野無人》書中有這樣有一段自白。是的,我也有著同樣的疑問。我得病了嗎?得的什么病?抑郁癥!嗯?怎么可能?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有著近乎理想的幸福生活:愛我的爸爸媽媽,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算不上大富大貴,家庭的收入也足以滿足我大部分生活需求;我有很多的朋友,發小、從小學到研究生積累的各種同學朋友,列個好朋友的名單可能數量上還要超出同齡人平均水平;我有著很多人羨慕的生活——北大,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學校!而我,課余時間,熱愛運動,籃球、乒乓球等球類運動玩得都可以,平時熱愛踢足球,甚至還代表學校參加了全國大學生足球聯賽;除此之外還積極地投身各種學生活動和組織……看起來我應該是一個生活充實、積極進取的有志青年。忽然,醫生給我下了診斷——中度到重度抑郁。
是的,我得了抑郁癥。我有著和其他抑郁癥患者相似的癥狀。早上不想起床,早醒后非常希望起床時間能慢些到來;不愿見人,不愿看微信、郵箱等信息,老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一個人在房間對聲音很敏感,不希望有人接近房間、時常會胡思亂想(學業、謀生、婚姻、贍養父母、自己的健康狀況、不斷反省質疑自己的性格——缺乏耐性、自控、好的意志力、為過去的所作所為后悔)而焦慮、發急、心慌、驚慌,老想躺進被窩,而且一個人時焦慮起來會逐漸變重,以致產生輕生的念頭,做什么事都覺得麻煩、嚴重的拖延癥,食欲下降,重復某些單一動作,幻想著時間停止、徹底換個人。睡覺早醒后我看到頭在一旁漂浮,四肢像被斬斷的青蛙發蔫,身子是空的,腦漿、鮮血、額頭那一塊皮、兩個眼珠子……浮在空中飄,各飄各的。過去我看不懂畢加索的畫,現在我就是畢加索的一幅畫。
具體來說得病的過程,要從去年三月份談起。由于意識到自己并非醫學生出身,專業基礎薄弱,研二的寒假我就啟動了自己的論文計劃,不巧的是得了肛瘺,做了個小手術,于是及早開始論文的計劃便被擱置了。三月份開學做出了兩篇小論文,交給導師審閱,都未能達到要求。然后四月份開始,跟著北大校學生足球隊接連征戰北京市大學生足球乙級聯賽和特步全國大學生足球聯賽(哈爾濱),在比賽期間,腹股溝拉傷,無法再繼續運動。四五月份期間還要準備大學研究生會的競選,其實當時出于對學業和將來就業的考慮,已經開始有些排斥這次競選。但是在好朋友的拉攏和扶植下,還是參與進來了。五月初,我的心里好像出現了一道裂縫:一邊是足球比賽和研究生會的競選工作,另一邊是學業論文和對將來就業方向的考量。于是,出現了焦慮的癥狀。焦慮發展到后期非常難受,坐立不安,抽煙抽得越來越兇,便自行到校醫院開了抗焦慮藥物。吃了半個月似乎有很大的緩解,同時伴隨比賽結束和競選成功,情緒表面上有了一些好轉。
轉眼到了暑假,按照之前請教導師的情況,暑期一個人留在了學校做畢業論文設計。但是進展得很不順利,晚上難以入睡,睡眠很淺,早上起不來,即使強撐著早起也是無精打采的。看論文很難集中注意力。加上論文中確實有一部分是需要技術指導的,當時便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焦慮再次來襲!離開學的日子越來越近,焦慮也越發的厲害,神經衰弱的癥狀似乎也有所增加,有種拖著僵硬的身體行尸走肉的感覺。慢慢地,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后來泛化到懷疑自己的性格、成長經歷等等,愈發的不自信。八月底離開學只有幾天的日子,精神上已經煎熬得不行,開始出現了輕生的念頭。輕生念頭嚴重的時候甚至有一些滑稽的舉動:晚上一個人躺在北醫花園的座椅上想凍死自己;在宿舍樓頂弄好了繩子勒自己的脖子;用晾衣架制作成夾子夾住自己的脖子;總想找沒人的地方自己獨處。
就這樣熬到了開學,隨著同門師兄姐弟順利地開題、寫論文。巨大的壓力感再次來襲,十一假期前一天倉皇逃回了家里。在家里待了一周,10月7號到我們市的心理專科醫院看病,被診斷為廣泛性焦慮障礙。10月8號住進醫院,住了十天左右,癥狀得到了很大的緩解,后來想想緩解是一種假象,只不過是逃離到了另一個無需面對現實的環境。出院后在家待到了11月15號,期間各種癥狀逐漸來襲。于是出于各種綜合考慮,和爸爸一起回到了北京就診。
醫生給我診斷是中度抑郁,建議住院治療。11月17號住進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在這里與世隔絕的40天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趣的,也是我病情得以好轉的關鍵時期。

挑戰死神 攝影/李 穎
早上六點,伴隨著王力宏歌聲的巨響,病友們紛紛爬起來洗漱、疊自己的被子,如果有病友疊被子不自覺會由護工謝師傅代理。謝師傅是蒙古人,偶爾在晚上值班的時候給家里通電話,沙啞的蒙語別有一番風味。每天早上六點半,病房中的病人基本洗漱完畢,大家聚集在大廳聊天,不愿意聊天的病友則在樓層的走廊里踱步;六點五十,護士給病友們發早上的藥,七點排隊打早飯;吃完飯又是短暫的自由活動;八點整,二樓和一樓的工娛室開放,二樓提供:KTV、報刊雜志、專門練書法的一個小房間,還有很多可以借閱的書籍。各種各樣的書琳瑯滿目,大部分是小說和暢銷書,少部分是心理專業類書籍。相比二樓的工娛室,一樓的工娛室面積上大了很多,提供的娛樂項目就更多了:乒乓球、鋼琴、象棋、五子棋、跳棋,當然還可以看電視。我在一樓工娛室學到了一個新技能就是打麻將,頭幾次打就連胡了七把,驚得大媽下巴都快掉下來了,相對優雅的項目就屬彈鋼琴了,女病友里不乏彈鋼琴的好手,《夢中的婚禮》時常回旋在麻將牌的碰撞聲中。
從早八點到十點,除了一樓和二樓的工娛室,病友們還可以到外面的小花園進行戶外活動,籃球、羽毛球、散步都是不錯的選擇。十點一到,各自回到病房,歇一歇、聊聊天、看看電視,不知不覺就到了中午吃藥的時間。吃過午飯就是午休,下午兩點到四點,大家又跑到一樓和二樓的工娛室各玩各自感興趣的項目。四點回到二樓玩會撲克。晚上六點到九點半,只有一樓的工娛室開門,不允許戶外活動了,所以這也是一樓工娛室最熱鬧的時候:老年人、青年人,還有兒童、陪護都混在一塊兒,各自找自己的好伙伴撒歡地玩。即使是聊天也是聊得不亦樂乎,甚至有互有好感的年輕男女會在這個時候悄悄聚在角落擦耳私語,在我住院期間就見證了幾對情侶的誕生。病人面對病人,隔絕了外在的世界,是極容易催生出某種情感的。當然,也有不少悶聲不語的特例,因為病情不同、程度不同,不同的病人便構成了錯綜復雜的小世界。八點半吃晚上的藥,然后在樓層和大廳自由活動,晚上九點半睡覺。
常見病的種類有以下幾種:抑郁癥、躁狂癥、雙向情感障礙(躁狂和抑郁交替發作)、精神分裂癥、強迫癥、潔癖等。因為不同的病種混在一起鬧出了很多笑話。病房中的一個大哥,早上住進醫院號召大家造飛機,口出狂言,要建造自己的飛機制造廠、醫藥博物館,信誓旦旦地招攬人才,結果午睡打了兩針之后,下午就蔫了,別人找他聊天他也不說話。很明顯,這是一位雙向情感障礙的病友。還有,我的一個好伙伴——巷子經(化名),六歲得了抽動癥,十歲患有精神分裂。他的典型癥狀就是經常穿著拖鞋來回跳動,有一次大家正在排隊打飯,只見他高高跳起,不巧的是,他飛起的拖鞋不偏不斜地落在了后面大哥的頭上;還有一位潔癖大哥,30歲左右,唐山人,已婚并且有一個5歲的兒子,他的強迫癥狀就是反復要求別人用他的香皂洗腕帶;類似的笑話著實不少……現在想起來,都忍不住暗自發笑。
笑話背后,我感受更多的是凄涼。很多病友在住院之前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磨難。
由于我在醫學院也度過了兩年多時間,也算半個醫學生吧,有幾個病友對我很信任,有時間促膝長談,他們會給我講屬于他們的故事。雖然我不是專業的臨床醫生,但是我時常想起著名醫生特魯多的一句話——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在醫院里,我將這句話融入了我的行動。當發現有人孤獨時,我會跑去陪他聊天;當發現有人心思很重,不愿和醫生交流時,我會借助自己的獨特身份嘗試去了解,幫助其傾訴出內心的擔憂和苦惱;有的人整日躺在病床,我便嘗試著拉他下床一起活動;這些時候,我完全忘記自己也是個需要別人幫助的病人,我只覺得醫學真神圣,醫生真偉大……
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其目的是為了呵護人的生命與健康。既然我們解決的是人的問題,我們就必須關注人的需求。任何一個人,既是生物的,也是社會的,因此病人不是器官與系統的簡單相加。他們到醫院就醫,不僅僅希望通過醫生的治療解除癥狀,同時也非常希望在醫務人員的理解與幫助下緩解與釋放心中的不安與焦慮等心理問題。因此,一名優秀的醫生必須在治療疾病的同時,更多地去安撫病人的情感,表現出設身處地的同理心,使病人足以抒發焦慮,并給予開導,解釋與再保證等等。
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是一種人性的傳遞,也說明了體貼的安慰、鼓勵的語言在醫學實踐中的重要性。這些積極的語言不僅使患者感到溫暖和安全,同時也能調動患者的積極因素,及時解除患者的心理隱患,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說:“醫生有三件法寶,第一是語言,第二是藥物,第三是手術刀。”在醫療服務中重視語言的作用,也正說明了醫學是一門人學。抽去醫學的人文性,就拋棄了醫學的本質屬性。
活著,然后嘗試快樂地活著。一起加油吧,病友們,活出屬于自己的獨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