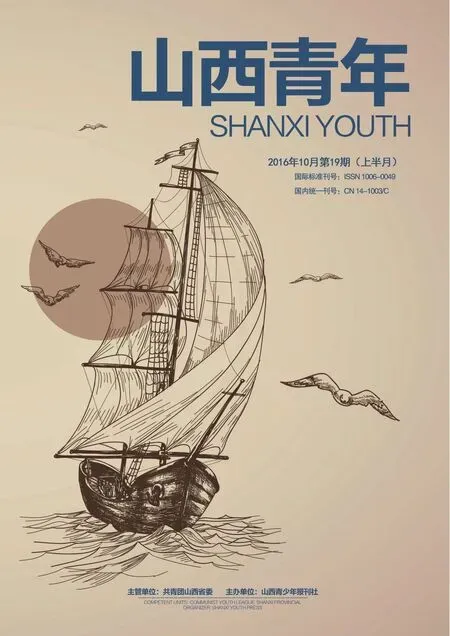抗日戰爭之前黨的“階級關系”理論演變規律
王 蕾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北京 100089
?
抗日戰爭之前黨的“階級關系”理論演變規律
王蕾*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北京100089
抗日戰爭前夕伴隨“瓦窯堡會議”的召開,黨有關的“階級關系”理論已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中國階級關系的成熟分析與判斷,是將其幻化為“人民戰爭”的戰略形式與各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與政策的關鍵。黨從“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走向“全民族的先鋒隊”經由了一個曲折的“統一戰線”過程,這一過程即有關“黨群關系”的歷史問題也有關黨自身的建設問題。
黨的階級基礎;“統一戰線”理論;“瓦窯堡會議”
一、黨的“階級關系”理論的基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辛亥革命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實質依舊。但隨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利用一戰的機遇實現的重大發展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中國社會產生變革的關鍵,它著重體現在工人階級的發展上。“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二百多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會力量”。①
工人階級初期的壯大與所表現出的斗爭精神是逐步與黨的建立結合共生的。“五四運動”是工人階級彰顯能力的第一個舞臺,自6月起,以在滬的六七萬罷工工人為代表,工人階級走到了運動的前沿。在斗爭中他們還逐步認識到了運動所應具備的政治意義,并在罷工的實踐中意識到了組織與領導的重要性,這不僅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階級基礎與人才儲備還提供了初步的斗爭與領導經驗。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并拒絕在巴黎合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勝。
“十月革命”的炮聲打響了!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說,辯證唯物主義起源于中國,由馬克思進行一番科學化后又回歸到了中國。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頌揚“十月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影響與宣傳下,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改變國家命運。五四運動中,部分青年學生見證了工人階級的魄力與勇氣,因此那些具備初步共產主義理想的先進分子開始到他們中間去,建立學校、成立工會、發動工人運動,這些實踐也為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骨干。
現實的實踐與理論都決定著使工人階級成為自己的階級基礎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選擇。黨的一大更是將組織工會與領導工人運動作為了實際工作目標,從成立之初就注重與本階級的親密聯系,這是黨的重大優點。黨成立一個月后,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首個非隱蔽工會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很快建立起來了。
二、“大革命”時期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的初步實踐
在內外交困狀況下的中國,要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僅僅依靠年幼的黨和局部的工人力量是艱難的。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慘敗致使黨領導的第一個工人運動高潮偃旗息鼓。對失敗的感悟表明黨對中國“階級關系”的認識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年幼的黨是帶著“所可恃者以救中國的只有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聯合起來,實行國民革命”②的覺悟走入以國共合作為標志的大革命時期。實際上1922年7月黨的二大就參照了之前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議案》與“統一戰線”的精神,因此黨的二大在明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的同時也制訂了“聯合全國一切革命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聯合戰線。”③等一系列政策。正確的民主革命綱領指導了正確的階級路線。同年8月,“西湖會議”正式明確“黨內合作”的方針,拉開了國共合作形成統一戰線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從一大主張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相互關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是一個很大的進步。”④這是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的第一次重大實踐。
(一)“統一戰線”理論在各階層的初步運用
國共合作使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各方面運動有了新的發展。以工人運動為例,1924年7月,廣州沙面興起的反對英法“新警律”的政治大罷工,成為工人運動從低谷邁向新高峰的起點。鄧中夏對這次罷工有很高的評價,他說:“自‘二七’失敗后,消沉狀態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還未改變,七月廣州沙面發生大罷工,才表現著這種消沉狀態應該中止了。”“此次罷工確哄動了廣州與香港,并且影響還及于中部與北方。”⑤工人運動取得復蘇與進步的同時,農民運動也有了起色,在澎湃的舉薦下,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下在廣州成立了,此后講習所共舉辦過六屆,并給20多個省份培養了“初步武裝”——農民自衛軍。“中國的農民原來素稱馴良,近來因為迫于軍閥的禍害,也漸漸知道團結反抗了”。⑥中國的農民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武裝。在國共合作的推動下青年學生和婦女運動也呈現出了活躍的狀態,這更進一步帶動了社會精神面貌的變化。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的這種新形勢下獲得了成長的契機。1925年在領導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的過程中,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黨組織也普遍發展起來。
但伴隨國共力量對比的變化與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左”、“右”兩條線路的差異不可避免地反應和影響到黨的階級關系發展上來。
(二)黨有關處理“階級關系”問題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初步積累
伴隨革命的深入,如何處理國共合作之間的矛盾?如何掌控民眾運動的程度?成為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的癥結所在。自1925年底國民黨中的新、老右派便不斷制造反對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的活動,“《整理黨務案》事件”之后國民黨中的政治、軍事大權一步步落入蔣介石的手中,這意味著革命雖然在發展,但已危機四伏。
首先要看到黨對農民、農村以及群眾性革命運動的重要性的認識是繼續發展的。1926年11月,中央農委以湘、鄂、贛、豫為重點發動的農民運動嚴厲打擊了不法地主劣紳,沖擊了腐朽宗法制度與思想并使權利歸于農會,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農村大革命,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⑦伴隨農村大革命形勢的是城市工人運動的進一步興起,同時在工農運動的推動與支持下,群眾性的反帝斗爭更是碩果累累。1927年初,在中共組織以及武漢工人、市民的努力與影響下,國民政府與英國達成協議,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中國人民取得了百年來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首次勝利。
但革命的形勢已不再滿足于黨一味的著力于民眾運動,許多地區還出現了民眾運動與國民黨階層的矛盾沖突,在湘、鄂、贛等省的工農運動高漲之時,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卻極大落后于形勢:它所犯的重大錯誤,就是“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⑧而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與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對國民黨右派又一味妥協,使黨的處境更加如履薄冰。1926年12月的漢口特別會議,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已展露無遺,盡管這次會議的決議遭到了毛澤東、瞿秋白等同志的反對但實際上還是確立了陳獨秀的有關壓制工農運動謀求同右派妥協的投降主義方針,這便導致了嚴重的后果: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獨立的軍隊,現在連工農力量都削弱了,失敗的陰影更加步步緊逼。很快“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重勢來襲給黨組織帶來了幾近“滅頂”之災,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慘敗收場。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不能抹煞它在黨的歷史上的非凡意義:黨組織不斷壯大的經驗與基礎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積累的;黨有關的“統一戰線”理論更是在這一過程中通過組織各種工農群眾運動的實踐開展的;黨與工農群眾的關系,黨對于如何發動、組織、甚至武裝群眾的思想理論是在這一時期中逐漸萌芽的;通過革命勝利與失敗的反復,更使黨與黨員同志掌握了正反兩部分的經驗教訓,即使黨經歷了慘重的打擊,但這一切的經歷,為黨把斗爭推向新的階段埋下了伏筆。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展現了其在組織工農群眾方面的卓越的領導才能,即使后來大革命失敗了,但堅持與工農群眾為伍的革命品質卻深深烙在了黨的成長過程中,這正是大革命留給黨最寶貴的財富。
三、土地革命時期“階級關系”問題在理論與組織上的發展
(一)黨自身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時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
在階級狀況復雜的中國,階級形勢可分為3個營壘,即在對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營壘外,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間營壘或稱中間勢力。它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村中的中農、富農和小地主。處理與中間階級的關系并使大量的工農武裝與軍隊一起參與斗爭成為土地革命時期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的主要特征。
1.整肅精神面貌——革命的恢復與“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大革命失敗后黨開始在“反思”中覺醒,“八七會議”便是黨由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會議在清查“右”傾錯誤后制定了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土地革命與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自1927年中國共兩黨分裂后,毛澤東拿起了槍,他所有的共產黨同事也都握槍在手”。⑨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有關“槍桿子”的講話與他會后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是這一時期黨群關系特征的縮影。湘贛邊“秋收起義”使軍事問題與土地問題得到了結合,斗爭的主體不再僅限于軍隊并首次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號,農民開始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起義在攻占大城市失敗后創造性地創立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山初期,毛澤東為部隊制定了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后來又提出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⑩這些都是他從日常軍民關系的實踐中總結出的,看似細枝末節,但使整個軍隊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并對處理軍民關系,爭取群眾壯大力量,體現人民軍隊實質起著決定性作用。
2.黨的“階級關系”理論在抵制“三次‘左’傾錯誤”中的發展
1927年11月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1930年6月開始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1931年1月由六屆四中全會開始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可以說是貫穿整個土地革命階段的三次嚴重“左”傾危機。其實早在“八七會議”時,受斯大林的影響就出現了將蔣介石與汪精衛的背叛與整個民族資產階級與上層小資產階級劃等號的現象,這是黨階級路線的嚴重倒退。“左”傾錯誤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形勢、工作重心以及革命方式有著嚴重的誤解,這是黨一次次在鼓吹革命高潮的情勢下失敗的根源,井岡山的“星星之火”與“割據思想”未能得到黨的重視,黨的工作中心始終遠離具有決定意義的農村。

錯誤的教訓是痛苦的,但對痛苦的反思和對錯誤的糾正就會是前進的,伴隨革命的深入發展,對錯誤的抵制逐漸開始反映到黨的理論與組織建設上來。

在農民與土地問題發展的同時,處理與黨有關的“階級關系”問題在根據地黨和軍隊建設上也有了進步。實際上井岡山時期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已經可以看作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的一個初期理論成果。而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作為建黨建軍的偉大綱領的同時更進一步從組織與紀律制度上對處理階級關系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它使黨在無產階級革命性質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吸收了更多的農民黨員因而適應了長期處于農村的工作形勢;此外還解決了在軍隊主要構成成分混雜的形式下,如何將其打造為聽黨指揮,服務政治斗爭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難題。這意味著,革命的工農軍隊已逐步走向有組織有紀律的“人民的軍隊”。
黨有關“階級關系”問題的經驗與理論已然在抵制“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在個個方面發展起來了,但正確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還在于人,在于一個強大而正確的中央領導組織。黨在經歷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后已迫切需要建立這樣的中央組織。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后一切似乎都不成問題了。會議解決了起決定作用的軍事與組織問題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組織,歷經漫長的坎坷之路,黨終于迎來了在組織上的堅強保障。
(二)抗戰前夕“瓦窯堡會議”的貢獻——“全民族的先鋒隊”

四、結語
從成立初期黨逐步奠定自己的階級基礎,到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處理復雜階級關系問題的歷練,黨的“階級關系”理論有一個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尤其是經由“統一戰線”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為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埋下了伏筆。更具體地說,之后黨的歷史中延安時期對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從“嚴苛”轉向“減租減息”,迅速爭取到更多開明士紳對黨的擁戴以及文革與改革的正反兩種效果,都能從“瓦窯堡會議”中找到注腳。黨在新的“階級關系”理論的指導下成熟的應對了之后的“西安事變”,使黨在即將到來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中贏得了主動權。中日民族矛盾的火藥桶即將點燃,但中華民族全員振奮,黨已經做好了抗戰的準備。
[注釋]
①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12.
②周恩來.《軍閥統治下的中國》.《赤光》第1期.
③蓋軍,劉建輝主編.《新編中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2011:014.
④《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81.
⑤鄧中夏.《鄧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526.
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94.
⑦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16.
⑧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544.
⑨[美]羅斯·特里爾著.胡為雄,鄭玉臣譯.《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09.
⑩李踐為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287.




[1]蓋軍,劉建輝主編.《新編中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版)[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004-058.
[2]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12-88.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美]羅斯·特里爾著.胡為雄,鄭玉臣譯.《毛澤東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09-110.
[5]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123-398.
王蕾(1992-),女,河南洛陽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中共黨史專業研究生。
D231
A
1006-0049-(2016)19-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