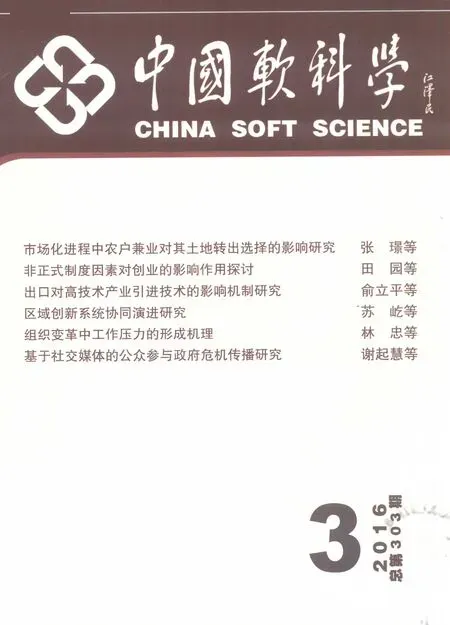寓利于義?企業慈善捐贈工具性的實證解析
眭文娟,張慧玉,車 璐
(1.電子科技大學成都研究院,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1731;2.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
北京 100048;3.浙江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
寓利于義?企業慈善捐贈工具性的實證解析
眭文娟1,2,張慧玉3,車璐2
(1.電子科技大學成都研究院,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成都611731;2.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
北京100048;3.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圍繞“為什么理性、逐利的私營企業樂于慷慨捐贈”這一問題,本文采用全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實證揭示隱藏在企業“義舉”背后的經濟“訴求”,并結合內外部因素探討影響慈善捐贈工具性作用發揮的邊界條件。研究表明,在轉型經濟情境下,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工具性的“寓利于義”,本研究對深入理解企業慈善捐贈戰略、引導企業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慈善捐贈;工具性;組織績效;私營企業;成長階段
一、引言
慈善捐贈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表現形式和企業公民理念的核心內容之一[1],不僅是企業貢獻于社會的關鍵手段,也是滿足社會事業需求的重要方式。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企業的公益參與及捐贈行為一直是衡量企業社會責任投入與社會績效的重要指標[2,3]。作為發展中國家典型代表的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企業慈善捐贈在調節社會資源再分配、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和發展以及改善企業公共關系等方面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民政部發布的《2012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企業群體是國內捐助的主要力量,2012年共捐贈474.38億元,占全國捐贈總額的58%,其中私營企業捐贈275.06億元,占企業捐贈的57.98%。自2007年有全國性的捐贈統計以來,私營企業的捐贈數額一直占企業捐贈總額的一半以上,是中國社會慈善捐贈和公益活動的中堅力量*人民網.民政部發布《2012中國慈善捐助報告》 紅會受捐同比降23.6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21/c1001-22983653.html.。
然而,對于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經濟組織而言,慈善捐贈是一種“奢侈的行為”,意味著企業要犧牲商業利益,將部分資金或實物資源用于非盈利的慈善公益事業,構成企業運營的額外成本。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企業的本質屬性是逐利,即追求股東利潤的最大化[4],而利他性的慈善捐贈會侵蝕企業相對稀缺的資源,損害股東利益,進而有悖于企業最基本的經濟責任。作為改革的特殊產物,私營企業在中國只有30多年的發展歷史,大部分企業正處于生存、發展的原始積累階段,盈利及成長是其首要目標。而從社會賦予的角色來看,中國私營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活躍市場,擴大就業,促進社會主義的經濟繁榮*1983年,中共十三大的報告就已經指出“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2003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再次提出“要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對于處于這樣特殊社會經濟地位的私營企業而言,利他性不能充分闡釋其慈善捐贈行為的動機及目的。
那么,理性的、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企業為什么會慷慨解囊?已有研究從戰略慈善、制度回應、政治訴求、道德資本等角度對慈善捐贈的作用進行了詮釋,并嘗試以此證明企業可以通過“行善而獲利”[5,6,7]。這些針對前置因素的研究豐富了學術界對企業慈善捐助的認識。盡管慈善捐贈受到外部環境和企業家個人特質的影響[8,9],但企業的捐贈決策最終取決于企業本身的特點及所依賴的情境特征[10]。不少研究實證檢驗了慈善捐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11,12],但大部分探討是基于特殊的災難背景[3],難以充分闡釋常態下的企業慈善行為。此外,很少有學者以企業自身的需求為基礎來分析慈善捐贈的直接作用,而外部環境對其作用產生過程的影響也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國特殊的轉型經濟為情境,充分考慮私營企業自身的特點和需求,嘗試深入挖掘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作用及其內在機理。具體來說,本文分別探討慈善捐贈對企業財務績效與成長水平的效應機制,并通過剖析組織可見性、政治關聯、成長階段、市場環境等內外部因素對主效應機制的影響進一步明晰其邊界條件。實證分析表明,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寓利于義”的工具性行為,實現企業的經濟利益依然是其關鍵目標。基于此,本文指出可以根據私營企業的捐贈目的正確引導其行為,從而有效促進資源的“第三次分配”與社會和諧發展。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一)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
慈善捐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是企業慈善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已有研究就此展開了大量的探討[6,11-13]。由于慈善捐贈被普遍視為是一種企業可“自由量裁”(discretion)的社會責任[14,15],利己主義認為,企業之所以采取慈善行為,是因為確信這一行為可以保障企業的最佳利益[16]。以西方發達國家為背景的諸多研究指出,慈善捐贈可以促進企業盈利[13]。但中國現階段的國情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慈善捐贈可以作為規避稅收的合法手段;但在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市場和制度體系尚不完善,稅收政策差異顯著,類似的優惠政策并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執行,企業免稅資格在異地無法認可的爭議更是暴露了稅收政策的“灰色地帶”*公益捐贈稅收優惠“灰色地帶”[N/OL],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5/20/content_1990544.htm。因此,西方情境下稅費減免[17]、政治游說[18]等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私營企業慈善行為的動機。
新制度理論為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提供了新的闡釋視角。從合法性角度來看,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所有社會機構的生存權和其他權利都源自社會的賦予[19]。企業開展各項活動的目的、運營方式以及最終的結果必須與社會體制的“游戲規則”保持基本一致[20]。企業的經濟業績并不是保障其生存與發展的充要條件,企業必須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獲取、提高并維持自身的合法地位,減少相對弱勢,進而尋求并把握成長機會[17,21]。在中國,私營企業長期受到意識形態和政策上的雙重歧視,在市場競爭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受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導政策的制約,私營企業始終面臨“老三樣”問題,即融資難度大、市場準入壁壘高、稅收費用負擔重*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融資困難和宏觀環境不佳是民營企業的兩大魔咒[N/OL],http://mea.pku.edu.cn/7/3/2012-07-01/4206.html。由于資源掌控者更愿意將資源提供給符合社會期望的組織[20],中國情境下開展的慈善捐贈能為企業績效帶來間接、迂回的利益[22],具體體現在企業利用慈善捐贈向社會或者政府進行尋租,通過構建社會合法性來提高組織吸引和獲取資源的能力。現行企業廣泛采用的做法是利用慈善捐贈將自身包裝為公知企業,積極參與修路建橋、辦學助教、扶貧濟困等公共事業。此類策略將慈善作為重要公關手段,以此來影響主管部門的政策決策,從而交換所需的市場資源和成長機會,如減少資源約束、增大市場準入、獲得信貸支持、謀取財政補貼等,進而提高組織績效。
從戰略視角來看,諸多研究認為慈善捐贈的效應具有即時性,即體現于對企業的短期財務績效的影響。將慈善與營銷有機結合的“善因營銷”即為一個突出的例子[23,24]。這種特殊的行銷方式將公益事業冠以企業或產品的名稱,因勢利導地借助新聞輿論和公眾關注達到廣告宣傳的目的,從而在短期內實現銷售額與企業利潤的顯著增加[25]。這種即時廣告效應在中國情境下更為突出。中國大多數私營企業正處于早期發展階段,本身缺乏資源的積累,更注重短期盈利。尤其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中,良好的聲譽能夠有效地促進產品推廣等關鍵商業活動的開展,成為企業改善績效與盈利的重要工具[26,27]。慈善捐贈與企業的市場目標相互兼容,企業慈善捐贈實際上是企業在環境和戰略互動作用下的一種戰略行為,目的在于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建立聯系,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促進產品銷售的同時創造出多種無形資產,如聲譽資本、員工信任、消費者忠誠等。以此,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可以看成是一種受到利己主義驅使的戰略性慈善活動,用來建立穩定的外部聯系,可以為關系型資產提供保護,有利于企業從中獲得資源和成長機會,改善組織績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慈善捐贈正向影響私營企業的績效。
(二) 組織可見性的調節影響
組織可見性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行為進行判斷的先決條件,反映了市場和制度環境下企業的地位及企業行為被關注的程度[28]。一家企業的可見性越高,其行為在公眾中的關注和識別度越高,利益相關者對其行為的期望越大,相應反應越顯著。可以預見,組織可見性會對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的效用產生影響。
一方面,組織可見性可以通過推動合法性與資源獲取正向影響慈善捐贈對績效的效應機制。Wang 和Qian[12]的研究指出,可見性正向影響捐贈行為帶來的盈利水平。組織可見性有利于增加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互動關系,推動社會合法性的獲取,從而有助于企業的資源整合與績效改善。可見性能夠促進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關注與認識,并通過對企業相關活動的了解來做出有意義的反饋,其中包括:來自投資者和第三方組織的有利評價[29,30]、消費者愿意支付高額的產品價格、對潛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等。這些因素實際上是企業逐步獲取社會認可與合法性的過程,能夠促使慈善捐贈行為更好地推動私營企業獲取資源、提高績效。組織可見性越高,企業的捐贈行為就越能獲得利益相關者的關注與認可,得到相應反饋;而對于可見性低的企業而言,利益相關者可能難以注意到其捐贈行為,因而慈善投入并不會給企業帶來顯著的收益。
但另一方面,組織可見性可以通過增加社會期望與審查負向影響慈善捐贈對績效的效應機制。組織可見性越高,企業的經營活動越容易吸引社會和公眾的關注及監督。利益相關者對高可見性企業的社會責任賦予較高的期望,并傾向給予這些企業更多的監督和審查。規模大的企業擁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但同時也要承受更多的社會壓力。在這種高標準和嚴要求下,高可見性企業的慈善活動更多地被潛在定義為社會義務,通過此途徑獲取合法性、整合所需資源的效用將減弱;更重要的是,高可見性企業的“不作為”或“不當行為”會使得企業遭受嚴重的公眾輿論壓力,甚至引發公關危機。現實中不乏此類案例,最突出的是2008年地震后公眾、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反應。相關組織通過網絡公布了慈善參與企業的捐贈額度,基于此產生了明顯的對比效應:一方面網友對盛名在外的大型企業設立了“鐵公雞排行榜”,并引發社會公眾的強烈反響和對這些“吝嗇”企業的產品發起抵制行為,造成其當年業績的直線下跌;另一方面,一些先前知名度較低的中小型企業通過數次“豪捐”迅速獲得輿論支持與消費者親睞,為產品銷售和市場地位打下了牢靠基礎。從這一角度而言,組織可見性對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有著負向的調節作用。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下述競爭性研究假設:
假設2a:組織可見性正向調節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假設2b:組織可見性負向調節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三)市場發展程度的調節影響
企業總是處于特定的市場和制度環境中,其組織決策、行為因此而受到相應的制約,而環境的這種影響力不僅作用于行為結果,也作用于背后的因果機理。由此可以基本判斷,無論是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本身,還是盈利水平的提升、聲譽資本的積累或市場機會的獲取均要受到企業所“嵌入”環境變動的影響[31,32],這是研究私營企業慈善捐贈問題不可避開的重要方面。中國處在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經濟體制結構呈現出計劃與市場共生并相互影響的狀態[33]。這種特殊的二元結構在不同層次形成特征各異的組合,加深了區域間的制度環境差異,如何應對現有市場環境、處理與制度的關系是私營企業戰略決策的重要考慮,對企業行為的最終結果造成相應影響[34]。因此,市場發展程度將對中國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產生重要的調節作用。
一方面,在發展較為充分、成熟的市場環境中,市場機制對宏微觀經濟活動的主導作用顯著[35],慈善捐贈幫助私營企業獲取公眾認可與支持、提高合法性的作用受到限制。在相對成熟的市場環境中,企業的經濟活動更加透明,與投資者、消費者、供應商、公眾等關鍵利益相關者的信息和溝通也更加暢通,利益相關者很容易通過企業本身或者其他公開渠道較多地了解到有關企業創新、市場戰略等方面的真實信息,因而可以更清楚、準確地了解并評判企業在創新、產品、市場等方面的潛在優勢,以此作為輿論判斷與購買行為的基礎。例如,消費者可以通過股票交易市場、大眾媒體報道等公開信息源中獲得有關企業及其產品的詳細信息,慈善捐贈對其認知判斷產生的影響作用減弱。因此,在相對自由、透明的市場環境下,利益相關者能夠根據充裕的信息更理性地對待企業的公益慈善行為,而慈善捐贈等方式吸引利益相關者的關注、認可及支持的工具性意義降低。
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與市場運營、資源分配等相關的正式制度將得到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產權保護舉措更為健全,私營企業通過慈善捐贈行為獲取利益相關者關注、認可、支持的動機降低。所在地區的市場發育程度越高,產品、要素以及中介市場發展也越完備,非市場化因素的影響作用減少,交易成本相對較低,而企業通過慈善捐贈進行尋租的潛在收益也隨之減少。即便是處于相對弱勢的私營企業,也可以通過相對公平的市場運行機制獲得所需資源和信息,提高自身競爭優勢。換言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環境中,不僅私營企業通過慈善捐贈獲得合法性及尋租利益的動機減弱,借此獲得的尋租利益及其他資源也將受到顯著約束。因此,企業的合法性要求及尋租動機降低,其行為將更加規范,決策將更加程序化,市場導向的戰略選擇越來越重要,并開始在企業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慈善捐贈對企業績效及發展的影響將減弱。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3:市場發展程度負向調節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四) 政治關聯對慈善捐贈與績效關系的調節影響
作為中國現階段最顯著的制度特征之一,政治關聯可視為企業獲得合法性的關鍵表征,是其迅速得到正式制度認可的有效方式,這在政府干預突出、市場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的轉型經濟中尤為重要。盡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強化市場作用、弱化政府干預的過程,但政府依舊是資源和合法性的關鍵來源[36,37],因此,政治關聯將對私營企業成長戰略及其作用機制產生重要影響[38]。就慈善捐贈這一特殊的戰略方式而言,政治關聯能夠從不同的方面強化其工具性作用。
首先,政治關聯是政府對企業的一種政治承認,建立和維護與政府的良好關系不但可以降低“尋租”風險,還能提升企業的社會地位和相應的政治權利[12,38],從而能直接提升慈善捐贈的工具性意義。很顯然,對私營企業而言,獲得政治關聯或者政治身份無疑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資源[34,39],在中國情境下尤為如此。以政府支持為隱性背景,政治關聯可以從根本上提升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互動中的信任基礎,為企業相對容易地贏取社會認可與支持。而在政府干預強、政治力量作用顯著的制度環境中,政治關聯本身就是一種無法替代的廣告效應[40]與資源及能力的象征,能夠直接、有效地促進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績效機制的實現與提升。
其次,政治關聯能夠有效提升私營企業在產權上的安全感,是私營企業合法性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因而能夠促進慈善捐贈工具性作用的發揮。在政府力量顯著的制度環境中,政治關聯不僅直接賦予企業政治合法性,而且能夠助其間接獲得公眾認可與社會合法性。對私營企業而言,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關系意味著有形或無形的政策保護,有機會獲得直接支持或間接回報,對其生存和發展存在顯著影響。由于政府擁有較高的資源支配權,企業與政府關系越密切,其尋租空間和尋租收益便越大[42]。地方公益為主導的慈善捐贈便是企業通過協助地方政府減輕公共服務負擔的常用尋租手段。因此,在以“關系”為紐帶、政府干預角色依然舉足輕重的中國制度環境中,處于相對資源弱勢的私營企業將充分利用政治資源在市場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政治關聯能夠幫助私營企業實現慈善捐贈的潛在收益。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4:政治關聯正向調節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五)慈善捐贈的績效機理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
企業發展是一個與眾多利益相關者相互作用、協同共進的動態過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企業戰略目標、內部資源、管理能力以及面臨的外部期望和需求都存在顯著差異[43],這些差異化因素必然對企業行為及其效應機制產生顯著的影響,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同樣如此[44]。有關中國情境下成長階段對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績效機理的影響在近年來也引發了國內學者的關注。陳宏輝和王鵬飛[45]以廣東省私營企業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私營企業的成長周期會對私營企業是否參與慈善捐贈產生顯著影響。易冰娜[46]利用私營企業上司公司數據驗證了慈善捐贈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對企業價值機理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本文將延續前期發現,探討成長階段對私營企業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作用機理的不同影響。
處于初創期的私營企業成立時間短,組織規模小,結構簡單,經營業績不穩定,可用于營業外支出的冗余相對較少。在此階段,企業戰略都將聚焦在可以保障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活動上,對于慈善捐贈這一奢侈行為的投入決策相對謹慎,自愿性相對較低;但是迫于對合法性與其他稀缺資源的需求,初創期的私營企業更容易受到慈善捐贈工具性行為的驅使,更加關注、重視慈善參與帶來的經濟回報。此外,社會公眾對初創期企業的社會參與期待相對較低,這些相對“弱勢”企業的慷慨解囊也因而更容易得到認可與贊譽,轉化為社會資本、道德資本與合法性。因此,盡管初創期的私營企業可用于慈善捐贈的冗余資源有限,但在工具性利益的驅使下,他們若能戰略地滿足或超越較低的社會期待,便能給績效與成長帶來更顯著的推動作用。
處于成長期的私營企業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產品和服務結構基本完善,市場份額較為穩定,經過前期的試探和妥協與利益相關者建立了信任基礎,并獲取了一定的社會資源,但由于處在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對合法性、聲譽及資源性支持的需求依然很強,慈善捐贈背后的工具性利益依然對其充滿誘惑力。隨著在發展過程中更多地融入到當地社會環境后,企業更能清晰地認識到自身與社區及公眾的密切聯系,更愿意參與到社會性慈善活動中,以此構建良好的公民形象,獲得輿論支持,從而間接促進組織績效的提升。與此同時,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與社會期待的增加,可用于慈善捐贈的冗余資源增加,對慈善事業的管理能力更強,因而可以更好地挖掘、利用善舉中的工具性效應。因此,處于成長期的企業在慈善捐贈行為及過程等方面可能與創業期企業存在顯著差異,其績效作用機理也可能產生相應的變化,但其慈善行為對組織績效的推動作用同樣強勁。
然而,對處于成熟期的私營企業而言,經營活動比較穩定,產品和服務市場相對集中,已經與利益相關者建立了長期穩定的關系,組織與環境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合法性、社會資本、聲譽資本等方面的積累同樣趨于穩定,對慈善捐贈的工具性利益依賴顯著降低。同時,處于成熟期的組織都經過了反復的“試錯”過程和經驗積累,對制度環境與社會期望均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自有認知和應對機制,慈善行為的工具性作用隨之減少。此外,社會公眾往往對成熟企業的社會參與持有較高的期待,這將負面影響這類行為的工具性及戰略性效應。因此,盡管成熟期企業有較為充裕的冗余資源參與慈善捐贈,但其參與動機及驅動力均相對較低,更趨向于有選擇性地參與到有限的慈善活動中,且工具性目的相對較弱。
鑒于成長階段對企業行為及其效應可能存在全方位的滲透性影響,成長階段對私營企業慈善捐贈效應機制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效應結果本身,而且嵌入在其作用機理中,影響邊界條件作用的發揮。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系統性假設作為后續實證檢驗的基礎:
假設5:在企業不同成長階段,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推動作用及其機理存在顯著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基本情況
本文數據源自2012年第十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樣本,剔除了數據缺失和數據異常的樣本。經過篩選后,獲得來自19個主要行業共2143家企業構成本文的分析樣本。有關地區層面市場環境的測度,本文采用市場化程度的指標進行衡量。由于截止本文日期,2011年市場指數還未報告,本文實際使用的是2009年的數據。
表1列示了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從企業主年齡分布來看,接近一半的私營企業主處于41-50歲年齡階段,而30歲以下的樣本相對較少;從學歷分布來看,絕大部分私營企業主的受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下,大部分為高中和大專學歷,基本符合我國私營企業的發展現實。從企業行業分布來看,有超過四成的樣本來自制造業,符合我國私營企業的行業現實。

表1 所選樣本企業部分特征統計(N=2143)
對于企業成長階段的劃分,已有研究的觀點存在差異,其中Biggadike[47]的劃分方式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可和引用。本文根據其建議,將成立小于或等于8年的企業劃入創業期,創建8-15年的劃入成長期,而創建大于15年的,則歸入成熟期。以此為標準,本樣本中一半以上的企業(1143家)處于創業期,約11%的企業(231家)處于成熟期,這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過程及私營企業分布情況基本一致。
(二)變量測量
本文使用到的各主要變量如表2所示。
1.因變量
對于因變量組織績效,鑒于大多數私營企業依舊是處于發展中的中小型企業,本文主要從盈利水平以及企業成長兩個角度來進行衡量。
盈利水平。現有研究研究通常利用會計指標如總資產回報率ROA、權益回報率ROE、或者銷售利潤率ROS等衡量企業的短期財務績效。本文根據以往研究的做法結合所使用數據的特征,用ROA來衡量私營企業的盈利水平,計算方式為:ROA=凈利潤/總資產;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ROE來替代ROA對財務績效進行衡量,計算方式為:ROE=凈利潤/權益總額。
企業成長。由于企業的銷售收入反映了組織把握競爭時機或者拓展潛在市場的顯著成效,本文利用2011年的營業收入來衡量私營企業的成長能力。同時,為了減少特異質對回歸系數估計的影響,本研究對營業收入均取自然對數。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使用信貸資源代替銷售收入來衡量企業成長,計算方式為對商業銀行貸款取自然對數。
2.自變量
慈善捐贈。本文指對在扶貧、救災、環保等公益慈善活動中現金捐贈或者實物、工程勞務折合現金的總和。參照張建君[48]在研究中有關私營企業的捐贈可能性的測量,本文前置一年,對2010年度有捐贈的企業編碼為1,沒有的企業編碼為0,從而建立是否捐贈的二元啞變量。在后續的穩健性檢驗中,本文采用實際捐贈金額衡量慈善參與程度,并考慮特異值對回歸系數的影響,遵循之前研究的處理辦法,對捐贈金額取自然對數。
3.調節變量
組織可見性。Luo等[49]指出大型企業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可以作為組織可見性的衡量標準。本文借鑒Su 和 He[50]的研究,采用企業規模,即企業的總資產來衡量組織可見性,考慮特異值對回歸系數的影響,對2011年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市場發展程度。本文對此指標的測量源自樊綱等[35]編撰的中國市場指數,這一指數反映了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市場化的相對進程。本文選取市場化程度的總指標從整體上衡量不同地區市場的發展和制度環境的完善程度。
政治關聯。本文使用啞變量,即企業主是否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來衡量私營企業的政治關聯。對擁有上述兩種身份中任何一種的企業編碼為1,否則編碼為0。
企業成長階段。本文參照Biggadike[47]的建議,根據成立年限來劃分私營企業的成長階段。若企業創建小于或等于8年(即2003年以后創建),則處于創業期,取值為1;若該企業創建8年至15年,則處于成長期,取值為2;若該企業創建大于15年,則處于成熟期,取值為3。
4.控制變量
為了更好地檢驗私營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本文參照已有研究發現控制了部分可能影響企業績效的變量。在歸納和分析相關文獻后,主要控制了相關的企業主特征和企業特征。企業家能動論認為管理者的能動性對企業的決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51]。本文用私營企業主個人經歷、受教育程度和政府背景來刻畫企業家的認知和才能,這三個變量都可能會影響企業的生產和發展前景。同時,本文還控制了對組織績效可能產生影響的部分企業特征,包括所有權集中度、資產負債率、行業、所在地等。
四、研究結果
(一)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3報告了本文研究樣本中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和最大值等描述性統計結果。
在所有的2143個樣本中,就因變量而言,營業收入存在著個體差異。65.4%的私營企業參與了各類公益捐贈,在參與程度上存在著個體差異。從企業特征來看,企業資產有著較大的個體差異。四成以上樣本來自制造行業,一半以上的私營企業注冊地在沿海發達地區。

表2 本文使用的主要變量定義及測量方法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企業主個體特征來看,企業主的平均年齡約為45歲,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大專,相對以前調查結果有提高,13%的企業主有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工作經歷。接近一半的企業主擁有各級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身份。
為了考察本研究所涉及的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是否有較高的內在聯系,以及考察自變量、調節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關性檢驗,表4報告了各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與預期一致,私營企業是否捐贈和捐贈額度與短期財務績效ROA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6(p<0.01)和0.07(p<0.01),與ROE之間也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8(p<0.01)和0.10(p<0.01)。
與預期一致,是否捐贈、捐贈額度均與企業成長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47(p<0.01)和0.57(p<0.01)。
從自變量與控制變量、控制變量和調節變量之間的關系來看,相關系數大多低于經驗文獻中多重共線性閥值0.5,最大三個分別為0.75,0.51和0.50,這說明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所有解釋變量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分析,結果表明只有市場程度、沿海地區的VIF值超過了2,分別為2.53和2.39,其變量包括自變量和調節變量的VIF值均在2以下,都低于經驗分析定義的閥值10,并且平均VIF為1.49。可以判斷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并且這一結論在后面的回歸分析中也得到了佐證。
為了進一步判斷捐贈有無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對慈善捐贈與否與短期財務績效變量ROA、ROE、ROS以及企業成長變量包括營業收入、商業銀行貸款、公共和攤派支出在樣本均值之間的差異顯著性進行了T檢驗。其中,ROS,商業銀行貸款,以及公共和攤派支出作為相應的驗證變量。銷售利潤率ROS的測量方式為凈利潤/營業收入,用于衡量企業的盈利水平,反映企業對總體資源專業化運營的能力。之所以選擇商業銀行貸款這一變量,是因為2004年國有銀行改革后,私營企業發展需要的資金借貸主要來源于各大商業銀行,企業獲取金融資源的能力也是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指標。
表5顯示,參與慈善捐贈的私營企業(n=1402)與未參與慈善捐贈的私營企業(n=741)的短期財務績效和組織發展上存在著顯著差異(p<0.01)。這說明,參與捐贈的私營企業有更好的財務業績表現、更高的營業收入水平,以及獲得更多的商業銀行貸款,初步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及其下屬假設。另外,是否參與慈善捐贈的企業之間銷售利潤率的差別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ROS代表著企業對自身資源的運營能力,而慈善捐贈對這一能力的工具性影響并不明顯。

表4 各變量相關系數分析

表5 是否捐贈與組織績效的T檢驗
注:?p<0.1,*p<0.05,**p<0.01,括弧內為標準差
(二) 回歸分析與假設檢驗
本文對私營企業組織績效的影響分別從短期財務績效和組織成長兩個方面進行刻畫。考慮到二者都是連續變量,對于研究假設的驗證將采用OLS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此外,為了體現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調節變量的獨立影響作用,本文通過逐層放入的方法,從而比較不同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作用。
異方差檢驗。考慮到利用橫截面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的時候容易產生異方差現象,因此在執行回歸命令后,用estat imtest,white 和 estat hettest命令檢查異方差情況,發現P值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存在一定的異方差問題。為了防止對異方差的過度反應,本文遵循陳強等[52]的建議,利用OLS和OLS Robust穩健性回歸兩種結果進行對比。
內生性檢驗。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之間可能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本文結合了兩種方式進行處理,首先將自變量前置一年,其次,采用了工具變量法,使用兩階段估計進行檢驗。借鑒Su和He[49]的研究,慈善捐贈的工具變量選取了企業主對其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三方面自我評價的均值。從理論上看,自我評價越高,越容易參與到社會公益慈善活動中,事先的檢驗也顯示,與組織績效變量也沒有存在顯著的直接關系(β=0.004,p>0.1)。當使用自我評價作為慈善捐贈的工具變量時,Hausman估計量=17.68,P=0.1257,不能拒絕原假設。因此可以判定,內生性問題在本研究中不顯著。
1.慈善捐贈對企業盈利水平、成長水平的直接作用
表6報告了是否捐贈對企業盈利水平、成長水平兩類績效指標的OLS回歸與穩健性回歸的結果。可以判斷,異方差問題在本文研究中不顯著,并且大部分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在模型中保持穩定。與預期一致,模型1-2和模型3-2的回歸結果均表明,慈善捐贈能夠顯著地促進私營企業的盈利水平(β=0.232,p<0.01),模型2-2和模型4-2的回歸結果表明,慈善捐贈對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733,p<0.01),由此,OLS回歸和穩健性回歸的結果都支持了假設1,即慈善捐贈對私營企業的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6 是否捐贈對組織績效影響作用的OLS回歸和OLS Robust回歸結果
注:括弧內為t值,?p<0.1,*p<0.05,**p<0.01
2.調節變量的影響作用分析
為了檢驗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機理,本文進一步考慮了組織可見性、市場發展程度和政治關聯這三種情境因素對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績效的調節作用。本文首先將這三種變量與慈善捐贈變量做中心化處理,然后將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乘積項一起放入回歸方程,用以檢驗在不同條件下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機理。同樣的,本文考慮了異方差問題,并在表7和表8均報告了OLS回歸和穩健性回歸的結果。

表7 不同調節變量影響下捐贈與否對ROA的OLS回歸和OLS Robust回歸結果
注:基準模型為模型1-2,括弧內為t值,?p<0.1,*p<0.05,**p<0.01
表7報告了不同調節變量影響下是否捐贈對盈利水平ROA的回歸結果。從整體上來看,表中所有模型都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大部分變量的方向與顯著性保持穩定,比較OLS回歸和穩健性回歸的結果后,同樣可以判斷異方差問題也并不顯著。
從回歸系數來看,與基準模型1-2中的結果一致,私營企業參與慈善捐贈對企業盈利水平有顯著的促進作用(β=1.468,p<0.01),組織可見性(規模)對ROA有負向顯著的直接作用(β=-0.067,p<0.01),市場化程度和政治關聯對盈利水平的正向直接作用不顯著。
從交互項系數來看,組織可見性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ROA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078,p<0.01),政治關聯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ROA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02,p<0.1),但是,市場化程度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ROA的影響不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假設2和假設4得到支持,假設3未得到支持。
為了更直觀地展現組織可見性和政治關聯交互項對盈利水平的調節作用模式,本文基于模型5-3使用STATA13.0繪制了圖1和圖2。圖1顯示隨著企業在市場上的可見性的增加,慈善捐贈對盈利水平的正向促進作用將顯著減弱。相反,圖2顯示當私營企業擁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資源后,慈善捐贈對盈利水平的工具性促進作用將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表8報告了不同調節變量影響下是否捐贈對組織成長的回歸結果。從整體來看,表中所有模型都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大部分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保持穩定,比較OLS回歸和穩健性回歸的結果后,同樣可以判斷異方差問題也并不顯著。
從回歸系數來看,與基準模型2-2中的結果一致,私營企業參與慈善捐贈對企業成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β=1.471,p<0.01),組織可見性(β=0.585,p<0.01)、市場化程度(β=0.247,p<0.01)和政治關聯(β=0.465,p<0.01)對企業成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從交互項系數來看,市場化程度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企業成長有負向影響,并在統計上顯著(β=-0.158,p<0.01),假設3得到驗證,而企業可見性、政治關聯對捐贈與否與組織成長之間的正向關系沒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假設2和假設4未能得到驗證。

圖1 組織可見性對是否捐贈與盈利水平ROA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變量因變量:企業成長模型7-1模型7-2模型7-3模型8-1模型8-2模型8-3企業主教育0.159**0.161**0.148**0.159**0.161**0.148***(4.97)(5.09)(4.71)(4.82)(4.92)(4.58)企業主年齡0.014**0.012**0.011**0.014**0.012**0.0111**(3.41)(3.08)(2.83)(3.16)(2.88)(2.65)前政府官員-0.086-0.063-0.082-0.086-0.063-0.0809(-0.87)(-0.64)(-0.83)(-0.93)(-0.70)(-0.90)所有權集中度-0.277*-0.352**-0.381**-0.277*-0.352**-0.381**(-2.46)(-3.15)(-3.43)(-2.24)(-2.88)(-3.14)資產負債率0.323*0.276*0.292*0.323*0.276?0.292*(2.28)(1.97)(2.10)(2.18)(1.87)(2.01)行業類型0.323**0.271**0.280**0.323**0.271**0.280***(4.57)(3.81)(3.96)(4.64)(3.82)(3.98)沿海0.347**-0.064-0.0520.347**-0.064-0.0516(5.09)(-0.63)(-0.52)(4.87)(-0.59)(-0.48)是否捐贈0.467?1.579**1.471**0.467?1.579?1.471?(1.83)(2.87)(2.66)(1.68)(1.80)(1.69)組織可見性0.619**0.605**0.585**0.619**0.605**0.585***(22.63)(22.26)(20.98)(10.18)(9.85)(9.26)組織可見性×是否捐贈0.0320.0530.0410.0320.0530.0414(0.97)(1.65)(1.24)(0.55)(0.92)(0.69)市場化程度0.251**0.247**0.251**0.247***(7.35)(7.27)(6.91)(6.80)市場化程度×是否捐贈-0.170**-0.158**-0.170**-0.158***(-4.95)(-4.62)(-4.68)(-4.35)政治關聯0.465**0.465*(2.81)(2.56)政治關聯×是否捐贈0.0240.024(0.13)(0.12)截距4.416**2.835**3.214**4.416***2.835**3.214***(9.98)(5.82)(6.49)(5.06)(3.13)(3.45)N214321432143214321432143F值338.16**293.19**258.77**307.80**261.96**228.86**R20.61330.62290.63000.61330.62290.6300Adj-R20.61150.62080.6275
注:括弧內為t值,?p< 0.1,*p<0.05,**p<0.01
同樣,為了直觀地展現市場化程度對慈善捐贈與企業成長關系的調節作用,本文基于模型7-3使用STATA13.0繪制了圖3。圖3 顯示,隨著市場的發展和制度的完善,慈善捐贈對企業成長的正向影響作用將顯著降低,與預期的一致,有效的市場機制將弱化慈善捐贈的工具性作用。
3.成長階段差異的影響作用

圖2 政治關聯對是否捐贈與盈利水平ROA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圖3 市場化程度對是否捐贈與企業成長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從理論上而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私營企業,其參與慈善捐贈的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作用存在著差異。在上述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檢驗了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作用在創業期、成長期和成熟期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在具體假設檢驗時,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分別檢驗了調節變量與是否捐贈構成的交叉乘積項分別與組織盈利水平、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的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考慮到異方差問題在本研究中并不顯著以及論文的篇幅,本文在下述分析中只提供OLS回歸的結果。
表9的回歸結果顯示了很有意思的結論,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各變量對組織績效尤其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假設5,具體而言:
模型9-1至模型9-3顯示,在創業期和成長期,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對ROA的影響都是顯著為正的(β=1.474,p<0.01;β=1.761,p<0.01),而成熟期企業的慈善捐贈對ROA產生負向影響(β=-3.063,p<0.1),這一結果論證了本文的假設,說明慈善捐贈對成熟期企業的工具性作用明顯降低,這基本符合企業的運營戰略的邏輯。在不同發展階段,組織可見性和慈善捐贈的交叉項對盈利水平的影響作用也存在差異。其中,在創業期和成長期,這種影響顯著為負(β=-0.082,p<0.01;β=-0.093,p<0.01),而在成熟期這種影響變得顯著為正(β=0.299,p<0.01)。這表明,當利益相關者可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和評價企業時,慈善捐贈的工具性可能會被其他機制替代;由于成熟企業對慈善捐贈工具性的依賴性不高,反而可能因長期持續性的“善施”行為被大眾所關注,進而獲利。

表9 發展階段差異對捐贈與否與組織績效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
注:括弧內為t值,?p<0.1,*p<0.05,**p<0.01
同樣,政治關聯與慈善捐贈的交叉項對盈利水平的影響作用在新創期顯著為正(β=0.262,p<0.1),但在成長期、成熟期這種正相關并不顯著,這說明對缺乏信任歷史的新創企業來說,政治關聯可用來從根本上提升企業在與利益相關者互動中的信任和好感,由此來更好地實現慈善捐贈的工具性。當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和公眾認知,依靠參與慈善捐贈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并不會隨可見性的變化、或獲得政治資源而發生顯著變化。
此外,模型10-1至模型10-3的結果顯示,成長期私營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行為對其成長的影響作用顯著為負(β=-2.494,p<0.5)。這說明當私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已經建立起較為成熟的客戶資源和市場經驗,同時也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備的管理流程和成長方式,盲目跟風的慈善捐贈反而成為企業的負擔。相反,處于創業期的私營企業,慈善捐贈與組織成長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2.114,p<0.01)。另外,在不同階段,組織可見性和慈善捐贈的交叉項對企業成長的影響作用也存在明顯差異。模型10-1顯示,在成長期,公眾關注越大的企業投入到慈善捐贈越有利于其發展壯大(β=0.235,p<0.01),這是因為慈善捐贈對成長企業而言,猶如其他戰略,適當的慈善投入能夠帶來顯著的市場或社會回報。但對于創立企業而言,由于缺乏良好的前期信任基礎,企業可見性越高,慈善捐贈的工具性可能被其他機制所弱化(β=-0.002,p>0.1);而對成熟企業而言,慈善捐贈對市場的促進作用也不再明顯(β=0.073,p>0.1)。此外,市場化程度與是否捐贈的交互項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在創業、成長、成熟兩個階段都非常顯著,說明市場總體環境的完善可以從根本上減少企業將捐贈作為獲利工具的市場動機和結果。
綜上所述,假設1及其下屬假設1a和假設1b都得到了強烈的支持;假設2、假設3和假設4得到了部分支持;假設5得到了強烈支持。
4.穩健性檢驗
為了使得上文分析中私營企業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得到更為可靠的研究結論,本文借鑒已有文獻研究和上述研究思路進行了兩種穩健性檢驗。
首先,為了更全面地反映組織績效,本文將ROE作為因變量盈利水平的代理變量,將信貸資源(商業銀行貸款取自然對數)作為企業成長的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10所示,檢驗結果與預期相一致,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顯著正向關系不受到衡量指標變更的影響。
模型11-3顯示,組織可見性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政治關聯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兩者對盈利能力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均未受到衡量指標調整的影響。但是,模型12-3顯示出少量差異,將因變量替換成信貸資源后,雖然市場化程度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企業成長的為負向顯著(β=-0.200,p<0.1),但是組織可見性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企業成長的正向影響變得顯著(β=0.709,p<0.01),政治關聯與捐贈與否的交互項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方向改變,但依然不顯著(β=-0.284,p>0.1)。
考慮到企業成長對信貸資源的依賴,產生這種結果可能是信貸資源本身也受到環境的影響。即便我國信貸政策市場化改革日見成效,但獲得良好口碑的大型私營企業更容易受到銀行的關注。總體看來,本文的假設檢驗結果較為穩定。其次,考慮到利用啞變量可能會放大慈善捐贈的效果。本文還更換了自變量衡量方法,利用捐贈額度來刻畫私營企業慈善參與程度,重新運行上述分析,實證結果見表11所示。結果表明,本文重點驗證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與之前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具有穩定性。

表10 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影響關系的穩健檢驗結果(替換因變量)
注:括弧內為t值,?< 0.1,*p<0.05,**p<0.01;為了減少文章篇幅,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在表中省略,如有需要,可提供。
進一步,模型13-2顯示,組織可見性與參與程度的交互項對企業盈利水平ROA的負向作用依舊顯著(β=-0.009,p<0.01);而政治關聯與參與程度的交互項對企業盈利水平ROA的正向作用也依舊顯著(β=0.028,p<0.01);政治關聯對ROA的直接影響在方向上發生了改變,但依舊不顯著,其他變量與上述結論基本一致。模型14-2的結果與表8保持一致,市場發展程度與參與程度交互項對組織成長依舊存在顯著的負向作用(β=-0.016,p<0.01),其他變量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性均未有改變。由此可以判斷,本文之前的假設檢驗結果較為穩定。
同樣,本文利用捐贈額度做自變量,考慮不同成長階段私營企業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影響的差異,進一步保障結論的穩健性。如表12所示,只有捐贈額度對ROA、企業成長的直接影響發生了較顯著的改變,但影響方向保持不變。其他主要解釋變量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性均未有改變。由此可以判斷,本文之前的假設檢驗結果較為穩定,與前文中表9的結果較為吻合,即企業發展階段是影響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組織績效作用機理的重要因素,也進一步證實了前文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五、討論與結論
(一)結果與發現
圍繞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效應機制及其邊界條件,本文基于2012年全國范圍內2143家私營企業的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大部分假設得到了實證支持,由此得出一系列頗具意義的發現與結論。
第一,慈善捐贈對私營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組織成長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經濟轉型情境下,對理性、逐利的私營企業而言,“善施”并非純粹的利他行為,而是用來提升經濟績效、改善市場地位的重要工具,也是實現發展目標的有效手段。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具有工具性,通過社會參與用以實現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的平衡,是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寓利于義”。
從短期看來,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的工具性體現在并未對股東利益造成損害;相反,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從資產利用水平(ROA)還是股東回報率(ROE)來看,私營企業始終把謀取經濟利益看作企業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當看似“奢侈”的捐贈投入通過理性的戰略決策與市場策略、商業利益結合起來時,其所帶來的短期收益大于參與慈善活動所付出的成本。從長期看來,慈善行為的工具性作用主要體現于對企業外部環境的改善,企業自身通常容易獲得擴大再生產和拓寬市場的機會,而與政府政策密切相關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更樂意貸款給有慈善捐贈行為的企業。從這一角度看,捐贈行為是企業戰略性的公關投資,對缺乏關系資源的私營企業來說,更具有戰略上的間接性和迂回性。
第二,慈善捐贈對短期績效的正向影響會因組織可見性的提升而降低,但會隨著政治資源的獲取而增加。這一結果表明,雖然私營企業可以利用“善施”在較短時間內賺取輿論支持,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升企業的合法性與聲譽,以達到增加產品銷售、快速有效地改善財務績效的目的。但隨著組織可見性的提高,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的各類行為越容易被利益相關者識別和監督,他們進而對高可見性的企業賦予更高的期望設定。而很可能正是這些潛在的高期望和嚴要求,制約了慈善捐贈提升私營企業盈利水平的工具性作用。

表11 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影響關系的穩健檢驗結果(替換自變量為捐贈額度)
注:括弧內為t值,?p<0.1,*p<0.05,**p<0.01;為了減少文章篇幅,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在表中省略,如有需要,可提供。

表12 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影響關系的穩健檢驗結果(替換自變量為捐贈額度)
注:括弧內為t值,?p<0.1,*p<0.05,**p<0.01;為了減少文章篇幅,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在表中省略,如有需要,可提供。
同時,在轉型期的中國,與政府部門關系的好壞對私營企業的短期財務績效有著顯著的影響。以公益為主導的慈善捐贈能夠幫助政府減輕財政負擔,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是企業獲得政府認可、獲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方式。在以“關系”為紐帶、政府干預角色依然舉足輕重的中國情境中,政治關聯企業的公益行為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門的支持與鼓勵,也更容易被官方媒體報道、宣傳,推動其公關工具性的實現。這些至少在短期內都會對私營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有利的影響。
第三,慈善捐贈對組織成長的促進作用會隨著市場的完善而降低。隨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成熟,企業經濟活動和相關信息更多地通過市場途經被公開和曝光。同時,在市場的熏陶下,社會和公眾也能更為理性地區分和對待企業的捐贈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的研究發現,私營企業在現階段對慈善捐贈的定位不夠明確,普遍缺乏將其與企業經營相融合的長期戰略,因而慈善捐贈的工具性會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與完善而受到局限。這一結果也能夠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么2008年王老吉“一億豪捐”、陳光標高調慈善等事件后,一系列利用慈善捐贈作秀的企業被曝光,受到公眾及利益相關者的批判,并引發學術界對這類現象的深度思考。
第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慈善捐贈的績效機制存在顯著差異。總體而言,處于創業期的私營企業由于缺乏公眾信任和社會認可,慈善捐贈能夠積極推動其合法性的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社會責任前移”現象,即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參與到慈善公益活動中。對于成長期企業來說,這種工具性凸顯在獲取并維護企業聲譽、促進企業成長的長期目標中,這一效應對可見性高的企業尤為顯著,但這一機會性行為會隨著市場環境的完善而顯著降低。而成熟企業更聚焦持續發展和轉型問題,獲取合法化及公眾信任不再是其戰略重心,其對慈善捐贈的工具性需求明顯降低,慈善捐贈可能只是維持企業經營穩定的一種方式;尤其對于處于良好市場環境中的成熟企業而言,盲目地動用組織資源進行捐贈投入,有可能得不償失。這一結果說明,目前中國私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參與可能尚未達到與可持續戰略相結合的階段,但也逐漸開始擺脫早期表現出來的隨意性。
(二) 理論價值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發現,本文在中國情境下對學術界一直爭論的“行為-績效”問題做了更深入的探討,闡釋慈善捐贈績效機理的最終目的并非落腳于“捐贈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將慈善捐贈與組織資源、能力以及外部環境相匹配,進而通過結合不同成長階段的戰略目標幫助企業獲得獨特的優勢。在“企業社會責任前移”趨勢的推動下,包括中小企業和新企業在內的經濟組織均無可避免地面臨社會所賦予的責任與角色,如何實現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的平衡是能否持續順應社會期許的關鍵所在。因此,就理論價值而言,本研究超越了對“行為-績效”關系問題的討論,為后續研究從戰略層面探討組織捐贈與環境、資源的匹配奠定了微觀的知識基礎,對研究轉型經濟下的企業戰略和社會責任行為均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從系統角度來看,本文將企業慈善問題放在社會整體的大背景下進行探討,將其慈善需要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社會進步程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等宏觀因素相結合,而對績效機理進行研究的最終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引導和規范企業負責任的商業行為。在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化運動過中,轉型期的中國需要通過更有效的政府引導機制和更嚴格的第三方監督機制保護、推動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商業行為,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的社會責任之路。基于主要發現與結論,本研究為社會范式的演進及相關政府決策提供兩方面的啟示。
首先,必須加強政府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引導,并完善各級政府部門在該過程中的服務角色。在中國,重視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慣性延續到了當今的氛圍建設,對如何以及從哪些方面著手建設、改善軟環境的認知相當匱乏,這也許就是相關政策推廣了近十年卻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之一。經驗表明,政府倡導依舊是慈善市場的最大推手,依賴法律法規、政策引導等正式制度下的強制措施十分必要,這也是中國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中國現階段客觀條件尚難以滿足,若要進一步改善商業環境氛圍、營造良好的商業軟環境,政府必須充分發揮好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服務角色,通過市場機制鼓勵負責任的市場活動與商業行為,鼓勵、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構建良好的支持性和引導性措施,重視并強化營造企業與社會之間的良好互動機制,進而逐步推動企業慈善及社會責任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必須充分發揮社會規范機制的監督作用。推動中國慈善捐贈健康有序地發展是一項需要多方互動的浩大工程,除需要政府正式制度下的管制和引導外,更需要動員公眾、新聞媒介、第三方組織、社會運動者等非正式制度下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監督。政府“一把抓”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正式制度的過度干預使得慈善組織的自主性和自發性難以得到有效發揮,其功能也受到極大的限制,更忽視了諸多非正式制度力量滲透力極強的影響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社會規范機制不僅能夠較好地促進或約束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并且對慈善績效機制的實現、企業慈善的可持續發展有很好的規范作用。因此,隨著市場的進一步成熟、法律法規體系的逐步完善,中國必須推進并充分利用社會的共享價值來規范企業行為,實現慈善捐贈的組織內化,從而穩步建設、完善負責任的商業環境。
(三)研究局限與未來發展方向
本文存在一些有待后續研究改進的不足之處。首先,我們利用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問卷中現有的相關問題及數據從特定側面測量企業的慈善捐贈、組織績效、組織可見性等關鍵變量,如果后續研究能夠針對這些變量制定量表進行驗證性研究,將會提高這些變量的測度準確性。第二,本文的探討主要基于2012年的二手調查數據,而基于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無法充分證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后續研究可以收集長時間的面板數據,進一步驗證、深化本文的研究發現。最后,本文揭示了私營企業慈善捐贈的工具性作用,并嘗試闡釋企業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黑匣子”,但未對其中間機理進行實證檢驗,后續研究應當收集相關的實證數據深入挖掘、驗證該工具性作用產生、傳遞的具體路徑,從而進一步明晰企業慈善參與的戰略意義。
參考文獻:
[1]CARROLL A B.The Four Faces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98,100/101:1-7.
[2]MESCON T S,TILSON D J.Corporate Philanthropy: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Bottom-Line[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29(2):49-61.
[3]TILCSIK A,MARQUIS C.Punctuated Generosity How Mega-Ev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US Communiti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3,0001839213475800.
[4]FRIEDMAN 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N].New York Times.1970,September 13.
[5]JIA M,ZHANG Z.Donating Money to Get Money:The Rol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Stakeholder Reactions to IPO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4,51(7),1118-1152.
[6]MULLER A,PFARRER M,LITTLE L.A Theory of Collective Empathy i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Decis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9):1-21.
[7]VAN CRANENBURGH K C,ARENAS D.Strategic and Moral Dilemma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Heineken in Sub-Saharan Afric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122(3),523-536.
[8]HADANI M,COOMBES S.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olitical Marketplace Contingencies[J].Business & Society,2012,0007650312463691.
[9]KABONGO J D,CHANG K,LI Y.The Impact of Operational Diversity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An Empirical Study of US Compani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116(1),49-65.
[10]TAN J,TANG Y.Donate Money,But Whose? An Empirical Study of Ultimate Control Rights,Agency Problems,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1-18.
[11]AMEER R,OTHMAN R.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A Study Based on the Top Global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08(1),61-79.
[12]WANG H,QIAN C.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Roles of Stakeholder Response and Political Acc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59-1181.
[13]SEIFERT B,MORRIS S A,BARTKUS B R.Having,Giving,and Getting:Slack Resources,Corporate Philanthropy,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J].Business and Society,2004,43:135-161.
[14]CARROLL A B.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497-505.
[15]MITCHELL R K,AGLE B R,WOOD D J.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4):853-886.
[16]LEE M-D P.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ts Evolutionary Path and The Road Ahea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8,10:53-73.
[17]PORTER M E,KRAMER M 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80(12):56-69.
[18]LAGEMANN E C.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The Carnegie Corporation,Philanthropy,And Public Polic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9]SUCHMAN M 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610.
[20]HUSTED B W,ALLEN,D.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7(6):838-849.
[21]SCOTT W R.MEYER J W.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al Sectors[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83.
[22]鐘宏武.企業捐贈作用的綜合解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7,2:121-147.
[23]LAFFERTY B A,EDMONDSON D R.A Note On The Role Of Cause Type In Cause-Related Marketing[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4,67(7),1455-1460.
[24]ROBINSON S R,IRMAK C,JAYACHANDRAN S.Choice of Cause In Cause-Related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2012,76(4),126-139.
[25]VANHAMME J,LINDGREEN A,REAST J.et al.,To Do Well By Doing Good:Improving Corporate Image Through Cause-Related Market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09(3),259-274.
[26]GODFREY P 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4):777-798.
[27]LII Y S,LEE M.Doing Right Leads to Doing Well:When the Type of CSR and Reputation Interact to Affect Consumer Evaluations of the Firm[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05(1),69-81.
[28]RINDOVA V P,WILLIAMSON I O,PETKOVA A P.et al.,Being Good or Being Known: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imensions,Antecedents,An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1033-1049.
[29]CLACHER I,HAGENDORFF J.Do Announcements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eate or Destroy Shareholder Wealth? Evidence From The UK[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6(3),253-266.
[30]FOMBRUN C,SHANLEY M.What’s In a Name? Reputation Building and Corporate Strateg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0,33:233-258.
[31]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
[32]HALEBLIAN J J,MCNAMARA G,KOLEV K.et al.Exploring Firm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entiate Leaders From Followers In Industry Merger Waves:A Competitive Dynamics Perspectiv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33(9),1037-1052.
[33]GUTHRIE D.China and Globalization:The 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M].Routledge.2012.
[34]張建君、張志學.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戰略[J].管理世界,2005,7:74-105.
[35]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36]GAO Y.Government Intervention,Perceived Benefit,and Bribery of Firms in Transitional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04(2),175-184.
[37]STEVENS C E,XIE E,PENG M W.Toward a Legitimacy-Based View of Political Risk:The Case of Google and Yahoo in Chin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10.1002/smj.2369.
[38]LI J,QIAN C.Principal-principal Conflicts under Weak Institutions:A Study of Corporate Takeovers in Chin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34(4),498-508.
[39]WU W,WU C,RUI O M.Ownership and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Evidence from China[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12,18(4),695-729.
[40]THOMAS A S,LITSCHERT R J,RAMASWAMY K.The Performance Impact of Strategy-Manager Coalignmen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7):509-522.
[41]CHEN C J,LI Z,SU X,et al.,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Chinese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29-243.
[42]DIBRELL C,CRAIG J,HANSEN E.Natural Environment,Market Orientation,And Firm Innovativeness:An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1,49(3),467-489.
[43]SHARMA P,SALVATO C.Commentary:Exploiting and 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Over Life Cycle Stages of Family Fir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1,35(6),1199-1205.
[44]Jawahar M,McLaughlin G L.Toward a Descriptive Stakeholder Theory:An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Approa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3):397-414.
[45]陳宏輝、王鵬飛.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廣東省民營企業為例[J].當代經濟管理,2010,8:17-24.
[46]易冰娜.慈善捐贈與企業績效及價值——基于我國民營企業實證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2.
[47]BIGGADIKE E R.The Risky Business of Diversifica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79,57(3):103-111.
[48]張建君.競爭-承諾-服從:中國企業慈善捐款的動機[J].管理世界,2013,9:118-130
[49]Luo X W,Wang D Q,Zhang J J.State or Market: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Voluntary CSR reporting of Chinese Firms[J].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2014.
[50]Su J,He J.Does Giving Lead to Gett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3:73-90.
[51]邊燕杰、邱海雄.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J].中國社會科學,2000,2:87-99.
[52]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本文責編:海洋)
Benefits Embedded in Benevolence?An Empirically Instrumental Analysi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SUI Wen-juan1,2,ZHANG Hui-yu3,CHE Lu2
(1.ChengduResearchInstituteofUESTC,SchoolofManagementandEconomicsofUESTC,Chengdu611731,China;2.ChinaInternationalEngineeringConsultingCorporation,Beijing100048,China;
3.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Why are rational and profit-oriented private firms so generous in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Private Firms in China to explore and disclo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behind such benevolent actions,and further discusses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uch instrumental effects by consider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i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ing economy,philanthropic donations of Chinese private firms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strumental action with benefits embedded in benevolence,and such instrumental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firm growth stage,internal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external environment.These finding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Key words: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onations;instrumentality;firm performance;private firms;growth stage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3-0107-23
作者簡介:眭文娟(1984-),女,湖南永州人,助理研究員,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后,管理學博士。通訊作者:張慧玉。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71202025;71302081;7140216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3YJC630221;14YJC630049)資助。
收稿日期:2015-11-25修回日期:201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