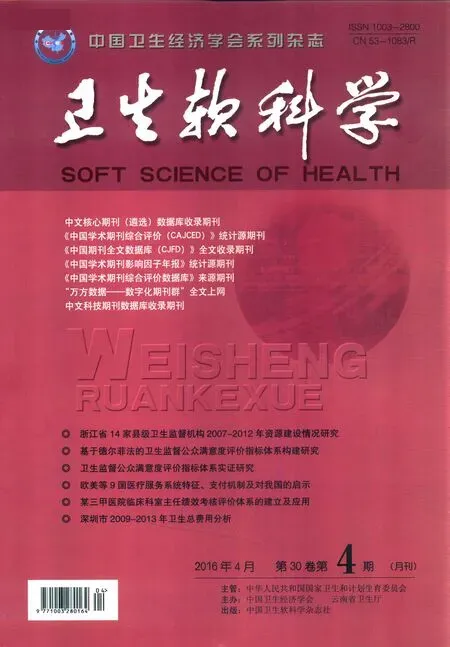歐美等9國醫療服務系統特征、支付機制及對我國的啟示
王海銀,金春林,彭 穎,龔 莉,王 惟,賀淵峰
(1.上海市醫學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上海 200032;2.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上海 200125)
?衛生政策與改革?
歐美等9國醫療服務系統特征、支付機制及對我國的啟示
王海銀1,金春林1,彭 穎1,龔 莉2,王 惟2,賀淵峰2
(1.上海市醫學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上海 200032;2.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上海 200125)
推進醫療支付方式改革、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是當前我國醫改的重要方向。歐美等9個國家在支付機制和醫療服務定價上探索較早,已積累一定的經驗,但由于醫療衛生系統制度及結構不同,需要結合我國實際參考應用。對歐美等9個國家的醫療服系統及支付機制現狀進行描述,分析比較了我國與9國的差異,并提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醫改,特別是支付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醫療系統;支付機制;RBRVS;DRG
近年來,我國醫改不斷深入推進,在全民醫保、基本藥物等制度建設上取得了顯著成績,在破除以藥補醫機制、深化醫保支付方式、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分級診療等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在一些重點、難點問題(如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優化醫療服務支付模式)上尚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已經成為制約當前醫改的重要環節。本文基于國際視角,對歐美9個國家的醫療服務系統特征、醫療服務支付模式進行梳理,同我國進行比較分析并結合實際,提出完善醫療服務改革的政策建議,為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改革提供支撐。
1 歐美等9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特征及費用
醫療服務系統主要由初級醫療和住院服務兩部分構成。其中,初級醫療以私人診所為主,主流運作形式為合伙開業和個體開業。澳大利亞、英國、日本、加拿大和美國以合伙開業為主,韓國、希臘、德國和法國以個體開業為主。住院服務以公立醫療機構和非盈利醫療機構為主,如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德國、法國以公立醫院為主流模式,美國、日本、韓國則以非盈利醫院為主[1]。
注重分級診療建設。9個國家中除英國外均實行自由就醫制度。英國明確限制人群自由就醫,強制實行轉診制度,對經家庭醫生首診的患者給予獎勵。部分國家通過激勵機制引導分級診療。如德國、法國和澳大利亞對通過家庭醫生轉診的患者給予激勵。美國、日本、韓國和希臘尚沒有建立簽約家庭醫生和轉診的激勵機制。另外,希臘對固定就醫的患者進行獎勵,加拿大也強制實施轉診制度。
醫療保障主要有三種主流模式,稅收、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其中,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稅收為主,德國、法國、希臘、日本、韓國以社會保險為主,美國主要為商業醫療保險,覆蓋約58.9%人群[2]。實施層面,英國和澳大利亞實行全民醫療服務制度,加拿大由各省組織實施,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及希臘則有多個保險機構組織實施,韓國為一個保險方承擔實施。
衛生總費用、家庭負擔各國差異明顯。主要可歸為三種類型,韓國、澳大利亞和希臘衛生總費用相對較低,但家庭負擔和藥品比例上相對較高;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和法國衛生總費用居中,家庭負擔、藥品費用也較低;美國衛生總費用最高,但家庭負擔和藥品比例相對較低。運行效率方面,各國平均住院天數平均為7.4天。其中,日本最高,為17.5天;法國最低,為5.6天[3],見圖1。
2 歐美等9個國家醫療服務的支付機制
各國均建立了針對醫生和醫院的兩種醫療服務支付機制。根據醫生和醫院的支付情況,具體可分為四種運行模式。(1)醫生和醫院均以按項目付費(Fee-For-Service,FFS)為主,如韓國。(2)醫生以按項目付費為主,醫院以病種分組付費(Diagnosis-related groups,DRG)為主,如德國、法國、日本、希臘及澳大利亞[4]。(3)醫生以工資、按人頭付費和按項目付費混合模式為主,醫院以DRG為主,如美國和英國。(4)醫生以工資,按人頭付費和按項目付費為主,醫院以總額預算為主,如加拿大。近年來,按服務績效付費(Pay-For-Performance)、按治療事件付費(Episode-Based-Payment Approach)[5-6]在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逐步推廣應用。2010年美國通過《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倡導通過建立可信賴醫療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s,ACOs),將逐步轉變按數量付費的機制為按價值付費模式。當前,按績效付費主要應用于預防和慢性病管理,應用的比例尚不大。下面對FFS和DRG的定價機制及應用情況簡要介紹。

圖1 9個國家2013年衛生費用及平均住院天數
2.1 按項目付費定價機制
包括基于成本的相對價值參數(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RBRVS)和協商制定等兩種策略。其中采用RBRVS的國家包括美國、德國、英國、希臘及韓國等,各項目的相對值(Relative Value,RVU)主要有中央層面協商制定。沒有采用RBRVS的國家主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同相關利益方協商制定,如澳大利亞、日本、法國由中央政府協商制定,加拿大有地方政府協商制定。
RBRVS由美國Medicare 和Medicaid在1992年最早實施,其主要通過制定各醫療服務項目所消耗資源的相對價值點數、變換常數(Conversion Factor,CF),并結合地區調整系數計算得出每一個項目的醫療服務價格。其中,每個RVU值包括工作量點數(Work RVU),涵蓋工作時間,工作強度,技術難度,工作壓力等;成本點數(Practice Expense RVU),涵蓋辦公設備,非技術人員,器械耗材等成本費用;醫療責任險點數(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RVU)三部分,三者的權重分別為48.3%、47.4%及4.3%[7]。變換常數由美國聯邦醫保中心按照每年的財政預算及整體醫療服務量計算得出,即每點的價格。調整因子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計算得出。總的點數值是每個RVU值乘以變換常數和地區調整因子的總和。根據執業地點不同,每個醫療服務項目可有兩個總的RVU值。總的機構點數值(Facility Total RVU)主要指在醫療機構中開展診療獲得的總點值,其成本點值為機構成本點值(Facility Expense RVU);總的非機構點值(Non-Facility Total RVU)主要是指在診所、醫生辦公室等開展診療的點值總額,其成本點值為非機構成本點值(Non-Facility Fxpense RVU)。病人看病一般要分開支付醫生的勞務費用和醫院成本費用。
當前診治專用碼(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CPT)是核算醫療服務費用的基礎,美國醫學會為標化醫療服務,為實際發生的治療、診斷、手術過程設置了一套5位數編碼,約有1萬5千多個點值。具體包括評價和管理代碼、麻醉代碼、手術編碼、放射學代碼、病理學和實驗室的代碼、醫學代碼等。醫生需按照代碼收費,政府則依據代碼收費管理情況進行監管。
2.2 按病種付費機制
按病種付費主要應用于急性住院病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之后在澳大利亞、歐洲等發達國家廣泛使用,近年來墨西哥、泰國、土耳其、南非等發展中國家也先后試點應用。現有幾種不同主流版本,包括美國DRGs(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DRG,HCFA-DRGs),澳大利亞修正版DRGs(Australian refined DRG,AR-DRGs)等[8]。
按病種付費是通過基于疾病、治療費用等特征,將相近的診斷組進行分類,按類別對醫院進行支付的一種模式。病種的分組主要基于患者特征、醫療服務特征及供方特征,具體如年齡、性別、手術類別、疾病診斷、合并癥及并發癥、出院情況等。病種費用測定主要包括三個要素:病種權重、基線費率和調整因子。病種權重是基于資源消耗的不同病種間的相對點值,消耗資源越多權重值越大;基線費率是指每個點值金額,與醫保資金總額和實際運行的總點數有關,每年進行調整;調整因子是指根據地區、醫院級別、病例人群特征等給予相應的調整。每個病種的費用為權重、基線費率和調整因子的乘積。
各國DRG系統設計略有不同。英國和荷蘭通過自主研發形成,德國、法國則通過引入美國、澳大利亞的DRG系統后進行本土化而成。總體來看,歐洲多個國家的DRG系統發展更加完善,具體如在病種分類上更加精細,英國2012年有4400種,法國2300種,而美國僅有750種;在支付范圍上,德國將出院后30d內再住院的仍納入一個DRG內;在特殊病種處理上,法國對高值的藥品、耗材,腎透析等病種進行額外補償,對一些創新技術采用另外機制進行覆蓋;在成本數據測算上,英國將所有NHS系統醫院納入進行測算,為保證數據質量,德國撥付專項經費進行支撐[9]。
3 我國與歐美等9國醫療服務系統、支付機制比較
采用“結構-過程-結果”模型來看,我國醫療服務系統同歐美等9國上均有明顯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 醫療服務供給結構和籌資模式不同
從供給結構上看,歐美等9國醫療系統框架設計多為初級醫療保健和住院服務,門診和住院分開運行。初級醫療主要采用市場化設計,由家庭醫生開設診所運作。家庭醫生和醫院醫生技術能力同質性較高。我國的醫療系統框架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二級醫院和三級醫院。服務提供以公立醫院為主體,民營醫院比重較低。各級醫院提供的服務均涵蓋門診和住院服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的數量較少,家庭醫生同二、三級公立醫院的技術能力差異明顯。從籌資結構看,除美國外,多數國家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險,以及針對特殊人群的安全網設計,均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保障的水平也較高。我國醫保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體,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商業健康保險為補充的醫保制度體系,覆蓋率已達95%以上。但現行的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及新農和保障差距明顯,尤其是新農和非常薄弱,醫療保障的水平尚較低。
3.2 醫療服務運作和支付機制不同
從支付機制上看,歐美等9國門診和住院、醫生和醫院的支付模式不同,醫生以項目付費為主,醫院以DRG為主。我國則未作區分,門診和住院仍以按項目付費為主流形式,按病種付費、按人頭付費及按床日付費的比例較低。從醫療服務運作上看,歐美等9國以家庭醫生為主體的“守門人”模式為主流,多個國家通過建立強制或激勵約束機制來引導分級診療。盡管國外多個國家仍以自由就醫制度為主體,但居民多以首診看家庭醫生,醫療秩序較好。我國實行自由就醫制度,近年來通過醫保支付杠桿、強制實施和醫聯體建設,逐步引導形成分級診療的就醫秩序,加強家庭醫生培養和能力建設,但醫療秩序仍尚未有效扭轉,居民首診多在大型公立醫院,看病難問題突出。
3.3 居民醫療負擔差異明顯
由于我國公立醫院主要依賴醫療收入和醫保補償,醫院通過擴張規模,購買大型醫療設備和使用高新技術等手段,以患者數量和服務項目提成為收益主體,出現了明顯的盈利特征,不同于歐美等9國公立和非盈利醫院。盡管我國衛生總費用比例較低,2013年占GDP的比重為5.6%,但患者支付費用比例較高,2013年個人負擔比例為33.9%[10],“看病貴”問題突出。以美國為例,其衛生總費用最高,但其家庭醫療支出僅占12%,有醫療保險的患者看病負擔較輕。
4 我國醫療服務及支付模式改革的建議
由于我國同歐美等9國醫療服務系統及支付模式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醫療支付改革、醫療服務定價等方面完全照搬國際模式不可行。但通過比較,可以借鑒其好的經驗,結合我國當前醫療服務特征的基礎上,對我國醫改的制度和措施進行完善。對我國醫療服務及支付模式改革的建議如下:
4.1 加強家庭醫生制度建設,推進分級診療
從國際趨勢來看,分級診療是當前較優的服務模式。我國的家庭醫生培養尚處于發展期,家庭醫生供給的數量有限,家庭醫生的技術能力也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患者對社區家庭醫生技術能力的不認可是阻礙分級診療的基礎因素。其次,家庭醫生的人事薪酬制度需要改革,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施的“收支兩條線”制度保障了其公益性,但制約了積極性,家庭醫生的薪酬較二、三級醫院明顯偏低,人員流失嚴重,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缺乏科學有效的家庭激勵約束機制是阻礙分級診療的動力因素。北京放寬醫師“多點執業”、上海居民與“1+1+1”醫療機構組合簽約(1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1家區級醫院、1家市級醫院)、深圳新辦診所不再有距離限制等制度創新,是基于當前實際的有利支撐策略,其效果尚有待于實踐證明。建議政府只有加大對當前社區人事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力度,打破人事、職稱晉升、薪酬待遇等制約瓶頸,才能引導優秀醫療資源到社區。其次,加大家庭醫生學科人才建設,逐步充實基層醫生力量。再次,推廣現有的優秀創新措施,整合現有資源,最終形成雙向轉診、急慢分治的醫療模式。
4.2 切實轉變現有以項目付費為主的支付策略,強化醫療機構成本控制
當前,國際支付方式改革的趨勢是逐步轉變粗放型為精細化管理,轉變由量為基礎到質為核心。研究表明各種支付方式均有優缺點,如按項目付費易使醫生為了增加收入而增加服務數量,按項目付費轉診率較按工資或人頭付費低9%~12%。按人頭支付激勵醫生選擇低風險和病情較輕的人群。按薪酬支付導致缺乏成本控制意識會、病人等待時間長和轉診率較高等[11-12]。按病種付費支付標準過低,會誘導服務項目數量和質量,標準過高會導致浪費。因此,適合本地的混合支付模式將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從國際經驗來看,住院支付主要采用總額預算和DRG,門診主要采用按項目付費和按人頭付費。我國支付方式改革上總體進展緩慢,當前在項目付費和DRG設計上尚需加強,表現為醫生的技術勞務價值明顯偏低,各項目間的比價關系不合理;DRG病種的數量少,缺乏權重和基點費率科學設計,對費用較高的病種和技術缺乏有效手段。因此,建議我國可借鑒國際RBRVS、DRG的思路和數據,通過開展醫療服務價格比價研究和結合當地實際,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的比價關系;引入國際DRG版本,開展試點地區成本測算,形成本地化的權重和基點費率,并結合地區、醫院、人群特征進行調整優化,逐步形成適合我國的按項目付費和病種付費系統,加強醫療機構的成本控制。
4.3 優化衛生費用投入結構和效率,降低個人衛生支出
當前,國際上加強衛生費用控制和優化使用效率是主要趨勢。尤其是美國近年來不斷探索支付方式改革,以降低醫療費用增長速度。近三年來,我國衛生總費用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2012年和2013年分別為13.2%和10.7%,且伴隨著醫療服務需求釋放、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發展,我國的醫療保險基金風險加大,個人醫療衛生負擔將進一步加重。衛生總費用增速過快可能與醫療機構建設擴張、大型醫療設備購置、藥品、耗材等新技術的過度利用及以數量獲取收益的支付機制有關。在醫院的費用構成中,城市醫院占63%,而社區衛生機僅占4.3%。藥品費用占衛生總費用的39.4%,明顯高于國際水平。盡管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例不高,但患者“看病貴”矛盾突出,醫患關系緊張。建議政府在保障衛生費用投入的基礎上,切實提高衛生費用投入及使用效率,優化衛生投入結構。如加強預防體系和基層醫療機構建設,降低藥品費用比例,提高醫療保障水平,鼓勵適宜技術發展等,進一步減輕患者的就醫負擔。
[1] PARIS,DEVAUX M,WEI L.Health Systems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A Survey of 29 OECDCountries[EB/OL].[2015-08-15].http: //dx.doi.org/10.1787/5kmfxfq9qbnr-en.1815-2015(online).
[2] 徐國平,李東華.美國衛生體系面臨的挑戰及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4,(2):32-37.
[3] OECD.Health Statistics 2014[EB/OL].[2015-08-15].http://www.oecd.org/health/health-systems/oecd-health-statistics-2014-frequently-requested-data.htm.2015.
[4] MIRIAM J,SHERRY A.Higer fees paid to US Physicians Drive higer Spending[J].HEALTH AFFAIRS,2011,30(9):1647-1656.
[5] GERARD DE P.paying doctors for performance[J].Eur J Health Econ,2013,(14):1-4.
[6] MILLER HD.From volume to value:better ways to pay for health care[J].Health Aff,2009,28(5):1418-1428.
[7] BALTIC,S.Pricing medicare services:Insiders reveal how it’s done[J].Managed Healthcare Executive,2013,28-30,33-34,36-40.
[8] MATHAUER I,WITTENBECHER F.Hospital payment systems based on diagnosis-related groups:experiences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J].Bull World Health Organ,2013,91(10):746-756.
[9] QUENTIN W,SCHELLER-KREINSEN D,BlUMEL M,et al.Hospital payment based on diagnosis-related groups differs in Europe and holds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J].Health Aff,2013,32(4):713-723.
[10] 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2014中國衛生總費用簡明資料[J].北京: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2015.
[11] GOSDEN T,FORLAND F,KRISTIANSEN IS,et al.Capitation,salary,fee-for-service and mixed systems of payment:effects on the behavior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The Cochrane Library,2007,(4):6-8.
[12] GHOLI V R,MOJAHED F,JAFARABADI M,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 of payment mechanisms on family physicians service provision and referral rate behavior[J].Journal ofPakistan Medical Students,2013,3(1):54-54.
(本文編輯:鄒 鈺)
Characteristics and payment mechanism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ealthcare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WANG Hai-yin1,JIN Chun-lin1,PENG Ying1,GONG Li2,WANG Wei2,HE Yuan-feng2
(1.ShanghaiMedicalTechnologyIntelligenceInstitute(Shanghai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Center),Shanghai200032,China2.ShanghaiHealthandFamilyPlanningCommission,Shanghai200125,China)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medical payment ways and straightening out price of medical service is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medical care reform in China.Some international countries explored early on the payment mechanism and medical service pricing and had accumulated certain experience,while health system and its structure is different,draw lessons from them should according to our actual situation.The paper depict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ine countries’ Medical service system and payment mechanism,the differences with our country was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our country health reform,especially the payment system reform.
healthcare system,payment mechanism,RBRVS,DRG
2015-08-15
10.3969/j.issn.1003-2800.2016.04.007
上海市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循證決策與政策轉化(CMB-CP 14-190)
王海銀(1983-),男,河南安陽人,碩士,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衛生技術評估與衛生政策方面的研究。
金春林(1967-),男,浙江臺州人,博士,研究員,主要從事衛生政策及衛生管理研究。
R197
A
1003-2800(2016)04-02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