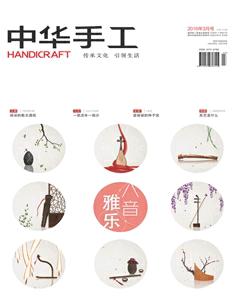徐冰的散點透視
拾二


透視,繪畫的專有名詞,是畫家為了在平面上表達客觀物體,讓畫作具有遠近空間感的技法,而徐冰卻將它用來解讀藝術靈感。“如果把生活看成一幅畫,那么各式各樣的人、千奇百怪的事、無處不在的符號、就構成了畫面的無數個點,而連接這些點的是人們敏銳的思維和對事物的感知能力。”就這樣,徐冰從中國到美國,從傳統到開放,而他的作品也一直緊緊跟隨時代的發展,像是在用透視法勾勒人間百態。
天書地書寫不完
許多人認識徐冰,都是通過他的《天書》,這也是他的成名作。從1987年開始著手,直到1991年才創作完成。徐冰在《天書》里創造了近4千多個漢字,除了標題,整部作品沒有取用一個現成的漢字,而是全部打破漢字原有的筆畫重新組裝成新字。就連徐冰本人,也無法清楚地讀出這些“文字”的發音。但在展覽現場,文字卻是鋪天蓋地地襲來,吊在半空的書卷、在地上鋪排開的線裝書,就連提供給現場的冊子,印著的也都是觀眾看不懂的方塊字。
徐冰回憶起當年閉門刻字的“造字”過程,很享受。他用木版印刷術,雕刻自己造的字,再印刷成書卷,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所以,徐冰認為這套作品,并不是裝置藝術,而是版畫作品。但《天書》又以“書”的形式存在著,更讓觀者費解的是,明明是書,但卻不能讀;看著像書法,但又說是版畫。其實,如果仔細研究,會發現徐冰的作品一直與“書”有著很大的關聯。
1999年,徐冰在旅途中發現,航空公司的安全說明書非常有意思,基本不用文字,僅用圖案,就把安全注意事項傳遞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他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航空說明書、世界各地的標識,甚至是口香糖的包裝……研究了數萬個標識后,徐冰發現,國際上其實很多領域早就有了通用的符號語言,比如天氣、交通、地理、化學、數學。
那一年,徐冰44歲,作為藝術家的他敏銳地感受到符號的創作價值。“它很平等,不管教育水平,也沒有國籍限制,只要有一定理解力和生活經驗的人都可以閱讀。”2012年,徐冰用《地書》建立了一個語言文字的烏托邦,整本書不再是讀不懂的文字,而是沒有文字,但卻可以不用翻譯就在全世界出版,這是以往任何一本書都沒有做到的事。書的內容很簡單:起床、上廁所、吃飯、工作、跟女友聊天、手機、電腦……畫面易懂,搭配及時通訊里常見的表情。徐冰不僅把這些符號語言集結成了《地書》,還讓這本書站了起來,每翻開一頁都是立體的畫面,讀者還可以與書里的許多場景互動。
監控攝像里的楚門
人們常常費力地保護自己的隱私,關掉手機定位、關掉GPS、不在公共平臺曬私照……但打開任何一個網頁,旁邊推送顯示的都是最近時間曾經在淘寶上看過的物品、百度里搜索過的關鍵詞,根據發布的信息計算出的可能感興趣的東西。人們一直在被無形的數據分析著,根本無從逃避,所處之世皆楚門。
2016年年初,在雅昌藝術網徐冰的主頁上出現了一段預告片,名叫《蜻蜓之眼》。宣傳海報上畫著三個女人,尼姑和綠衣女人,眼小鼻塌,面容詭異。但最前面的紅發女人卻格外妖艷,涂滿紅色指甲油的手抓著一條黃色的警戒線。背景畫面灰暗,如果不是“徐冰電影作品”幾個字,也許會讓人誤以為這是一部恐怖片。畫面上另兩行字說明了電影的獨特之處,“首部既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的劇情長片,本片影像全部來自公共渠道的監控視頻。”初看無奇,細思極恐,人們不僅是在被分析著,更是在被拍攝著。
“全世界大約有2億6千萬只攝像頭在24小時的工作著,中國就占了大概60%左右,并且還在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徐冰很冷靜地說著這些數字,“如果將這些攝像頭里的內容,全都保留下來,將是未來的我們看待現在的社會最冷靜、客觀的依據。”因為是無意識地拍攝和被拍攝,所以這些內容比紀錄片更真實。
一直以來,徐冰有著藝術家、策展人、版畫家等多重身份,但導演還是第一次。說是導演,好像也不太貼切,《蜻蜓之眼》并不只是一部普通的影像作品,更像是徐冰對圖案和符號,視覺化、立體化的又一次嘗試。電影里的所有畫面,來自全國各地搜集來的監控視頻,長達數萬個小時,包括各地電視臺播出的視頻以及網絡公開渠道獲得的視頻。“這個過程并不容易,早在4年前我們就開始籌劃,花了大量的時間,因為涉及到法律風險和渠道的問題,也曾一度作罷。一直到2015年,發現各地法制節目和網絡平臺有了越來越多的監控畫面,經過法律與風險的評估,才又重新啟動。”徐冰和他團隊的10多位工作人員一起,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把這些視頻歸類、剪輯以及再創作。
在僅僅4分鐘的預告片里,看不出完整的故事,但會讓觀者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出現在畫面里的人,是我。”徐冰說,“實際上,在過去的幾萬年時間里,發生過太多千奇百怪的事,只是沒有技術來記錄。而現在我花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創作這部片子,是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的事,就這么真實地存在著,而且就在身邊。”
作為藝術品的書
徐冰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在上世紀90年代末移居到了美國。他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動蕩,也感受過上世紀80年代洶涌的新思潮,同時又接受了上世紀90年代移居美國后的不同文化感受。徐冰剛到美國時,曾參觀過一個大型的手制書展覽,展覽上的書,有著各種各樣的材料、天馬行空的印刷和紙張的選擇,尤其是翻動時產生的無限遐想的空間,讓徐冰非常感動。
“中國有很長時間的手制書傳統,但我們卻對這個領域沒有更多地介入和認識,于是我很想把這個形式帶回中國。”手制書,是指的作者用原創的設計和手工的裝幀制作的藝術品圖書。2012年9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迎來了國內首次大規模的國際藝術家手制書展覽——鉆石之葉:百年全球藝術家手制書。展覽上的第一件作品,是捷克小說家卡夫卡的一本書。“卡夫卡留下來的書幾乎沒有,除了幾本名為《沉思》的書。卡夫卡在去世時說要把自己的書都燒掉,但說到《沉思》時,他說這本書可以留幾本。”徐冰介紹這本書的特別之處,“開本不大,版心很小,周圍的‘天頭‘地腳留得特別多,這一點點的特殊,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對書的敬畏。”
在徐冰發起的這場展覽上,匯聚了1913年到2012年100多年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國的手制書,其中包括杜尚的《必須停止胡扯》、安迪·沃霍爾的《安迪·沃霍爾索引》、陳琪的《時間簡譜》……“展覽的效果非常好,對出版、設計、藝術各界都有啟發,但沒有太多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藝術家參加。”徐冰很遺憾。
3年后的2015年,網絡徹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方式,書、雜志更加淡出人們的生活。而這一年,徐冰和他的團隊又一次發起了“鉆石之葉”的全球藝術家手制書展。這一次,他將“藝術家手制書”(Artists Book)定義為“藝術家通過對‘圖書空間的巧思,將文字閱讀與視覺欣賞以及材料觸感,自由轉換并融為一體的藝術”。
這一次,中國的參展藝術家增多,作品也從首屆的不到10件作品增加到了30多件。徐冰也在這次展覽上預測:“數碼閱讀快速取代著紙媒,‘讀者轉型的時代,紙媒書籍最終可能被‘藝術化或成為‘文化代表物。”但翻閱書籍時產生的愉悅感,是數碼閱讀永遠無法創造和取代的,這也許是徐冰的作品多年來一直與“書”有關聯的原因之一吧。
在采訪過程中,徐冰一直強調藝術家的手藝人思維,談起自己的創作過程,徐冰說:“很多藝術家在生活里,都帶有手藝人的性格,一點一點地摸索,這個效果怎么出來,這個材料怎么使用,我們很多時間都是在琢磨這些東西。”徐冰認為藝術家的成功與否并不靠智商,而是是否懂得在所處的時代變革中獲取思維的動力。毋庸置疑,數字時代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但人類的生活感知,直接地觸摸仍然是我們最原始也是最需要的溝通與交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