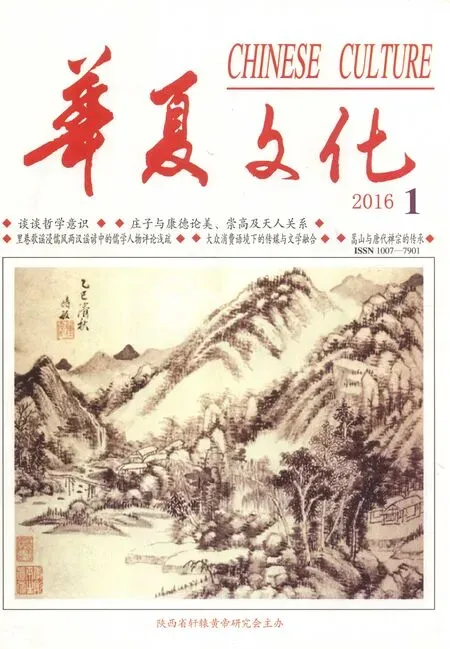論全真道的身體觀及其與儒佛身體觀的比較
□周建強
?
論全真道的身體觀及其與儒佛身體觀的比較
□周建強

全真道的身體觀主要有四假觀與骷髏觀。全真道對身體的這一認識與儒家和佛教既具有相同之處,又存在著差異。研究全真道的身體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全真道對生命的獨特體認以及重視心性修煉的全真精神成仙說。
現代自然辯證法研究認為,人體在本質上是物質、信息與意識的統一體,與生命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體機能的正常活動也是生命存續的重要標志。但全真道卻認為人的自然形體只不過是一種假象,在本質上來說,并非是實在的。這就為不執著人體自然生命的全真修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一
人的自然形體是由哪些組成?是真實無妄還是虛幻的?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全真道從其自身宗教修煉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教祖王重陽在教化馬丹陽時就說:“思算,思算。四假凡軀,干甚廝玩。元來是走骨行尸,更夸張體段。靈明慧性真燦爛,這骨骰須換。”(《道藏》第25冊,792頁)馬丹陽繼承了其師對人自然形體的看法,并作了進一步說明。如《洞玄金玉集》說:“火風地水結皮囊,眼耳鼻舌四魔王。”(第25冊565頁)“西施容,潘安貌。達者觀之,一場失笑。假大風地水成形,終不免坑窖。”(第25冊608頁)此外,其他幾位早期全真代表人物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等也有類似的看法。如譚處端說:“自入玄門戶,寂淡清虛做。靜里披搜四假身,勘破塵行路。”(第25冊858頁)劉處玄說:“亙靈不老,幻軀有數。”王處一也說:“一點靈光無缺漏,四般假物任沉埋。”(第25冊650頁)丘處機則說:“選甚冷熱殘余,填腸塞肚,不假珍羞力。好弱將來糊口過,免得庖廚勞役。裝貫皮囊,熏蒸關竅,圖使添津液。色身輕健,法身容易將息。”(第25冊832頁)可以看出,早期全真人物在對人的自然形體的看法上,盡管表達互有差異,但觀點基本一致。他們都認為人的自然形體并非真實的存在,而是虛幻的。這種看法也深深地影響了一批全真學人。如在全真道發展史上影響較大的尹志平就明確地說:“玉陽大師有言最切,云:‘欲要修行罵假軀’。蓋言使人業根不絕而有死地者,皆為此假軀也。……修行人止是自治,或獨居或與百千人居,亦止自治而已。既明此理,即要人當下承當,不然則來生又如是。”(第33冊171頁)這就意味著在全真道徒看來,人的自然形體并非不重要,而是另有深意。事實上,全真道主張“性命雙修”,先性后命,以性為主的修煉方式。這就要求一方面要“即假修真”,即依靠人的自然形體來修道;另一方面,又恐世人執著于人的自然形體,導致“真靈之性”不顯,從而影響最終的成仙。因此,全真道的“四假觀”就是要破除修道者對人自然形體的過分執著,將他們引向精神成仙的全真修煉。
二
骷髏是指人死后腐爛到最后,只剩下的一副骨頭,是沒有皮肉依附著的整套骸骨。有研究認為,“骷髏”的來源是“髑髏”,在先秦時已普遍使用;兩者又皆與“鬼”同源。“髑髏”之“髑”的發音本與“骷”同,后來卻發生了變化,便又造了“骷”字,以順應民間保留的讀音。(康保成:《補說〈骷髏幻戲圖〉——兼說“骷髏”、“傀儡”及其與佛教的關系》《學術研究》2003年第11期)這是“骷髏”的本義及其詞匯史來源。全真道在對外宣教時也多次使用含有“骷髏”的詩詞及畫作。如教祖王重陽在《自畫骷髏圖》中說:“此是前生王害風,因何偏愛走西東。任你骷髏郊野外,逍遙一性月明中。”(第25冊245頁)弟子馬丹陽在《嘆骷髏》中說:“攜筇信步,郊外閑游。路傍忽見骷髏,眼里填泥,口內長出臭蕕,瀟灑不肯重說,更難為,再騁風流。想在日,勸他家學道,不肯回頭。恥向街前求乞,到如今,顯現白骨無羞。”(第25冊631頁)其他全真早期弟子基本也都有類似的觀點。如劉處玄說:“早早悟骷髏,命清免九幽。”(第25冊429頁)丘處機也說:“蓬頭垢面,不管形骸貧與賤。抱樸頤神,恬淡無憂樂本真。冰姿玉體,到了難逃沉土底。子羽潘安,泉下枯髏總一般。”(第25冊,841頁)可以看出,這是早期全真道幾位宗師借用“骷髏”來表達他們對人自然形體的一種認識,即“骷髏觀”。為什么會有這種認識?“骷髏”既然與“鬼”有關,意指人自然形體死亡后一種恐怖而又可憐的樣態。因此,全真道使用“骷髏觀”就是為了在人們心中引起強烈的震撼與恐懼,以便誘使他們及時修道,遠離死亡。另外,這也與他們不執著肉體的全真修煉有關,將四假凡軀與死亡的骷髏聯系起來,從而強化他們對人自然形體“四假”的認識。
以上我們分析了全真道對人自然形體的認識。可以說,四假觀是全真道人體觀的基本認識,骷髏觀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識。當然,無論是作為對人自然形體認識的四假觀,還是骷髏觀,在早期全真道中可以說比比皆是,但在全真道發展成熟以后則出現得較少。這是否意味著全真道對人自然形體的認識已經發生改變?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全真道對人自然形體認識的削弱或者改變,反而恰好說明全真道的四假觀和骷髏觀已經深入教團,成為其基本認識之一。因為在教團初創時,為了凸顯不執著自然形體的全真修煉,全真宗師自然需要通過“四假觀”與“骷髏觀”有意強化他們的認識。但在教團發展成熟以后,這種“強化”逐漸變得多余,自然也就無須再度強調,而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
全真道對人自然形體的認識與儒佛二家既有著明顯的差異,又具有諸多相似之處。首先,感覺器官與肢體是人的自然形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先賢很早就從功能性的角度關注了這一現象,并認為人的自然形體是實實在在的。這是儒家與全真道對人自然形體認識的重要區別。但從另一方面來講,雖然儒家認為人的自然形體實有,要愛護好自己的身體,但為了成就“仁”的品格,追尋儒家之“道”,有時也要不憐惜自己的身體,勇于獻出生命。這是因為儒家要實現其理想中的“道德人”,亦即“君子”的人格。而要實現“道德人”,成為“君子”,就必須通過對人的自然形體的不斷塑造來完成。正如有學者所說,儒家重視身體,但是關注的重心卻不是我們純粹生理意義上的肉體,對于生老病死、日常飲食、保養身體等問題和人的生理需求,沒有忽略,但也僅僅是簡單涉及,而且往往是在對“禮”的討論中言及,是作為道德踐履的一部分來加以注意的(格明福、徐蕾:《儒家“身體”正名》《中州學刊》2011年第6期)可見,人的自然形體在儒家那里并不是目的,僅僅是實現“道德人”的工具而已。這與全真道“即假修真”確是十分相似,二者都不執著于人的自然形體。其次,佛教認為,人是由“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而成,其中的“色”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物質概念,具有質礙、變壞、顯現等性質,具體來說則由地、水、火、風“四大”構成;而其他受、想、行、識四蘊則是“色”(人自然形體)的心理活動和精神現象。這就是說,在佛教看來,人的自然形體是暫時的,當五蘊聚合的條件不存在時,也就消失了其存在性。即便五蘊聚合時,這種存在也只不過是“假名”,沒有實體。可以看出,佛教也認為人的自然形體并非是真實的存在,只不過是“假名”而已,這與全真道對人體的認識相同。對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假名”人體,佛教“十二因緣”則作了精致的解說,認為這一切都緣于“無明”(愚昧、不明佛法)。“無明”會使人產生各種“業”,從而遭受輪回之苦。要想跳出輪回,就需要普修佛法,證得佛理,獲得解脫。因此,“假名”的人體便在這解脫路上取得了主體地位。可以看出,雖然佛教與全真道都不執著于人的自然形體,但為了獲得宗教的理性目標,卻無一例外地都借助于人的自然形體來實現,這是二者的相同之處。而二者最大的區別便是宗教目標的不同,全真道“即假修真”,從而成仙;佛教則要“不執覺悟”,從而成佛。
四
總之,人的自然形體與生命緊密相關,而生命問題又是古今中外宗教家和人文學者討論的重要議題。(高新民:《宗教本質新解》《學術論壇》2004年第1期)作為道教革新派重要代表的全真道更是立足其神仙信仰,順應傳統道教肉體成仙理論與實踐困境的時代發展要求,在繼承傳統道教生命觀的同時,創造性的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生命觀。但它對生命的認識又是建立在身體觀的基礎之上。因而,深入研究全真道的身體觀不僅是理解生命觀的前提,更是理解全真道精神成仙說的關鍵。
(說明:本文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課題號:14YJC760037)
(作者: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郵編73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