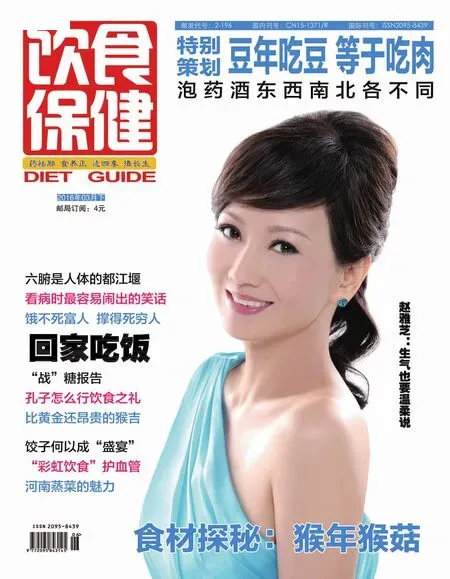孔子怎么行飲食之禮
文/晉如
?
孔子怎么行飲食之禮
文/晉如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龔鵬程教授認為中國的禮本身就起源于飲食,所以這一段就是講孔子在飲食中體現出來的禮。
首先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我們今天的理解可能跟孔子當時的意思并不一樣,這其實是說,孔子吃飯并不追求特別地精美,食物并不追求特別地精美、精細。如果飯的味道不好,已經變餿了,或者說這個飯有點夾生,那么魚味道變了,是不會吃的。一個菜如果做得它的色香味的色,色、香都不對,味也不對,都不會去吃。如果說他的食物不是當時因令的,那么也不會去吃,因為古人他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就是順應上天,順應天時,會認為如果說我們的食物是反季令的,這有可能就是對人身體很不好的,所以中醫有一個觀點,就是你一定要吃當季令的食物,這個是非常有道理的。
割肉割得不方正,那么就不吃,因為古代它這個禮,它很多細節都表現在分肉這方面,你割得不方正,說明你這個分的人你的心就是有問題的,我為什么要吃?因為我們吃東西,內心里面要含著一顆感恩的心,因為這些東西它是上天所給予的,所以我們在后面還會講到在祭祀的時候,一定是要表現出一種感恩的心態。
那古人,他吃不同的肉,他會蘸不同的醬。所以如果說用的醬跟他要吃的肉不匹配,也不會吃。醬的用途是干嘛的呢?醬實際上的用途是便于消化。所以不同的肉,醬是帶有一點腐化物,帶有一點腐化的作用的,這種腐化的東西,不同的肉有不同的微生物進行腐化,所以一定是要得其醬,雖然這個是我們今天科學的解釋,但是孔子在當時也可能長期的經驗總結,也可能本身就是一種儀禮的要求。北京,我經常去吃一家特別好吃的狗肉鋪子,他們那個狗肉就專門有一種醬,就叫狗醬,那個狗肉是白水把它給煮了以后,就蘸著那個狗醬吃,簡直太好吃了。我每次吃都會想起孔子的這句話,“不得其醬,不食”。
即使肉有很多,但是吃飯還要以五谷雜糧為主,因為中醫認為,最有營養的東西,最能讓你飽,能夠養你的東西,是什么呢?是植物的種子,五谷雜糧就是植物的種子,所以它是最能讓你有力氣,最能讓你生命得以延續的,所以一定是多吃飯,少吃肉。現在的80后、90后呢,往往是多吃肉、少吃飯,這對身體是很不好的。
孔子大概是一個酒量很大的人,所以關于酒量的問題,他就沒有說要人怎么樣少喝酒,他說酒量是看個人,只要你喝酒之后不會有行為反常的舉措,那都可以。我的酒量其實并不好,但是我的自控能力很強,就是我不管喝得再醉,但是我的行為從來沒有失態,我可能會下來以后躲到廁所里哇哇就忍不住就吐了,但是在酒桌上從來沒有我喝醉酒以后說錯話,從來沒有說喝醉酒以后做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這個我還是非常地自得的。
在外面買的酒、外面買的肉脯是不會吃的,因為擔心它不清潔。齋戒的時候會把葷的菜給撤掉,蔥、蒜之類的,但是卻不會把姜給撤掉,因為姜雖然它有辛辣之氣,但是它不葷,它的氣味是很清的,是非常清新的,所以它反而是讓那種骯臟污穢的那種氣息,讓你惡心的氣息它有一種消除的作用,所以不會撤掉姜食。我每次去飯館吃飯,我第一個要求就是不要放蔥蒜,但是點菜的人往往會跟食堂交代不放蔥姜蒜,我說我什么時候說不放蔥姜蒜了?姜和蔥蒜能是一回事嗎?
所以孔子吃再好吃的東西,他也不會吃得過量,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自控能力,而往往是現在有很多的人以吃貨自居,這樣的人,他往往是缺乏自控能力的。
他作為大夫,他會參加魯國國君的祭祀,叫做“助祭”,一起參與叫助祭。助祭以后,魯國的國君就會分賜給這些大夫一些祭肉,這些肉回來以后,他馬上趕緊就把它給分給鄉黨鄰里,分給家人,大家一起把它給消滅掉,不能夠讓它過夜。這個古人的解釋是說神給你的一種恩惠,不能拖得太久,你要盡早地享用它。而自己家的祭肉,祭祀祖先的這些祭肉,不能超過三天,放三天那是沒法吃的了。當然,從衛生的角度講是這樣,那么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儒家的宗教性的角度來講,它會強調的是三天以后的,都已經是鬼吃過的了,神鬼吃過的了,你不能再吃了。
吃飯時候,不跟人說話,那么睡覺的時候就不會說夢話,這其實講的也很有道理。中醫講“胃不和則臥不安”,你的胃里面不舒服,你睡覺是睡不舒坦的,你會做噩夢,你可能會說夢話,會磨牙。那胃怎么會和呢?就是你吃飯的時候,你吃得太急,你吃飯的時候不專心,你總是去分心,現在的孩子吃飯的時候還要看電視,吃飯的時候跟別人說話,不專心地去消化,去享受食物,最終必然就會把胃給害得壞了。所以,“食不語、寢不言”,這句我的理解他并不是說吃飯的時候不跟人說話,睡覺的時候不說話,而是說這是一個有先后關系的——吃飯的時候你不跟別人說話,你睡覺的時候就不會說夢話。這也有中醫的理論作為支撐的。
孔子在家,吃的是非常粗礪的飯食,只有菜羹,那么羹呢,它的做法,是把肉、菜切碎了,和著米糝子一起煮,后來演變成和淀粉一起煮,這就叫做“羹”。古人是在每次飲食的時候,會把各種吃的飯菜拿出一點點來,放到盛飯食物的籩和豆的中間空地上,那個時候也沒有桌子,就是案上。所以,孔子他即使是吃非常粗礪的飯菜,也會拿出一點來,以表示出對于古代最先發明飲食的,讓我們今天吃到這么美味的食品這些人的懷念、追念,一定是像齋戒一樣地恭敬。這個“瓜”是一個通假字,通必須的“必”,因為在古代必須的“必”的篆書的寫法跟這個瓜是比較接近的。
席不正,不坐。
那么這一章,圣人的心,一定是要擺放得正,所以這個席子如果不正,他就不會坐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