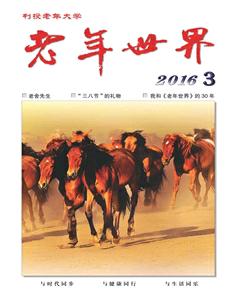我在于鳳至身邊的日子
孟芳琳
?
我在于鳳至身邊的日子
孟芳琳
盡管過去了將近30年,但有一幅暗淡的畫面卻始終定格在我的腦海中:疏星點點的深夜,在美國洛杉磯好萊塢的山上,一幢平層別墅里,我攙扶著下肢幾近癱瘓的老太太去了趟廁所。回到床上,老太太再也睡不著,倚靠著床頭,失神的眼睛蒙著一層白翳,空洞地注視著窗外無邊的黑夜。
我知道,她已經這樣眺望了快50年。她能望到太平洋的彼岸嗎?床頭燈下,稀疏的白發微微顫動,我知道她此刻心潮難平。她在想什么?當年東北大帥府的錦繡繁華?九一八事變的鐵馬冰河?還是陪伴丈夫在溪口、沅陵的幽禁歲月?
她就是于鳳至。像一顆來自遠方的彗星劃過夜空,在行將隕落的時刻,發出最后一道耀眼的光芒。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人生軌跡與她有了交集。
面試
1987年9月中旬,我辭去上海財貿干部管理學院的教職,只身一人到美國洛杉磯的加州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碩士學位。剛下飛機的時候,口袋里只揣著當時外匯管制只允許兌換的47美元。
因為白天要上課,所以我必須盡快找到一份夜間上班又能提供食宿的工作。翻遍當地的華文報紙,總算在角落里發現一則招聘啟事:好萊塢山華裔老人急征管家、夜間護理,提供食宿,月薪600美元。
第二天一早,我便迫不及待地請朋友送我去面試。

繁忙的101號高速公路途經著名的好萊塢玫瑰碗露天音樂劇場。車從旁邊一條叫巴瀚的小街出來,便拐上了迂回曲折的山間小路。兩邊茂密的樹林、扶疏的花草,掩映著一幢幢精致的別墅。車到山頂,停在一幢乳白色的平層別墅前,門牌是:雷克瑞治路2904號。
開門的是一位中年婦女鄭太太,她操一口臺灣腔國語,領我進了餐廳。餐桌旁的輪椅上坐著一位頭發雪白的老太太,皮膚白皙,形體消瘦,看上去有80多歲,因為白內障,眼神顯得有點茫然,但精神不錯,緊閉的嘴唇透露出幾分威嚴。
她看著我,開始發問,一口純正的東北口音:“你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是的,從上海來的。”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這下我頭暈了。我怎么知道她是誰呢?便搖搖頭。
“我是張太太!”
張太太是誰?我更暈,只好小心翼翼地問:“請問您是哪位張太太?”
“這你都不知道?”她顯然有些不快,“張學良,你知道不?”
哇!我恍然大悟,連忙說:“張學良將軍?當然知道。那您老就是,于——鳳——至?”
她這才滿意地點點頭。后來我知道,她十分在意“張太太”這個稱呼,即使1963年與張學良離婚后,她仍然堅持要別人稱她為“張太太”,以至于那個姓鄭的管家雖夫家姓張,按道理也應該叫“張太太”,但于鳳至不容許她叫“張太太”。所以我們都管那個張太太叫鄭太太。
接下來的面試就容易些了。老太太再發問:“你讀過大學嗎?”
“讀過。”
“哪所大學畢業的?”
“復旦大學。”
老太太略一沉吟,又說:“復旦大學?沒怎么聽說過。”
幸虧我對母校的歷史有所了解,否則如今在中國名列前茅的大學被她如此一說,豈不冤枉?原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復旦確實名氣不大,它的蛻變是1952年院校調整之后的事了。
她看看我的窘相,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說:“我可是讀了東北大學文法科的。”
我苦笑一聲,心里想:那是自然的,東北大學不就是你老公創辦的嗎?
“好吧,大學不怎么地。那么英文懂嗎?劍橋大學怎么說?牛津大學怎么說?寫下來。”她把餐桌上的紙筆推到我面前。
呵呵,這可難不倒我。當我把寫好的紙片送到她面前,她端詳著,嘴角露出笑容,說:“你被錄取了!”
悲情
跟老太太的臥室相通的一個小房間就是我的臥房,只要老太太床頭的鈴聲一響,我就必須立刻起身,攙扶她或是上廁所,或是擦身,或是喝水。平時她的起居飲食倒十分簡單,早餐總是牛奶、面包。中午和晚上就更簡單,因為牙口不好,永遠都是豬骨頭熬的濃湯放在冰箱里凍著,需要時挖幾勺,放些菠菜、西洋菜等綠葉蔬菜加熱熬爛,這樣就著面包吃。所以那個掌勺的鄭太太基本沒事做,成天關在自己的臥室里讀日語小說。
只是苦了我。老太太晚上睡不著覺,我白天上課再累,這時也只好強打精神坐在床邊陪她聊天。
老太太最喜歡聽我說大陸的老百姓至今還牢記張將軍,牢記張夫人。說到“西安事變”,她笑了,話匣子打開了。
于鳳至,字翔舟,父親于光斗早年開燒酒作坊,發跡后富甲一方,任吉林懷德縣商會會長,曾經慷慨資助過被官兵追殺的草寇張作霖。張作霖入主奉天以后,向于光斗面謝,在于府中見到美麗賢淑的長女于鳳至,占了卦帖,說有“鳳命”,便力主為張學良訂下終身。兩人于1916年完婚,其時,張學良只有15歲,于鳳至年長3歲。張學良參與父親的軍機大事,四處征戰,她以長媳身份留守大帥府,協調張作霖幾個夫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內務。待到1928年6 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她毅然挺身而出,與五位夫人一道隱忍悲痛,秘不發喪,巧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周旋,使張學良得以秘密潛回沈陽奔喪,并于無聲中完成東北軍政大權的移交。之后,她又全力支持張學良“易幟”,實現中國統一,并在張學良誘殺楊宇霆、常蔭槐等親日派元老的策劃中,起到他人不能取代的作用。換言之,張學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偉大的建樹,即順利完成東北易幟,結束最黑暗的軍閥混戰時代,于鳳至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這個世界在男人眼里,也許都是權勢和金錢,而在女人眼里,只有一個字:情。從老太太的講述中,我能感受到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因為對張學良這個男人的情義。
有幾天,她的神情顯得十分焦躁,總是叮囑我去門外的郵箱查看有沒有來信。鄭太太告訴我,原來在我到來的前兩個月,即1987 年7月,于鳳至從報紙上看到蔣經國在臺灣宣布解禁,已經有一些國民黨老兵前往大陸探親,她頓時眼前一亮:被蔣介石幽禁了50年的張學良應該可以徹底獲得自由了吧?于是,她立刻托人寫信寄到臺灣。信中,她向張學良傾訴了40多年的分離相思之苦,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見一面。這是兩人于1963年離婚后的第一次通信,深情款款,不能自已;囑愿切切,只盼歸鴻。
9月底的一天,我在郵箱里見到一封從臺灣來的信,筆力十分蒼勁。應該就是了!我興奮地跑回房,將信交給了正坐在餐桌旁的于鳳至。
我能夠看見她面部表情的變化。驚喜,激動,用顫抖的手直接撕開信封,都等不及我取來拆信刀。但瞬間,我發現她的面部表情又變了,雙唇緊閉,嘴角拉了下來。訝異,難以置信,憤怒,失望,悲傷……她又反復看了幾遍,便將信紙揉成一團,扔進桌旁的垃圾桶。
是什么樣的信能激起如此的軒然大波?我撿起信紙,展開一看,一張白紙上只有50來個核桃大的字:鳳至姐:
謝謝你的來信。感謝上帝,我的一切都很好。更感謝主,領導我在他里面有喜樂平安。愿上帝祝福你,愿你在他里面有恩惠平安。
漢卿手啟
九月二十一日
就是如此的簡單、平淡,那40多年海天曠隔的傾訴呢?相期此生再見的回應呢?當初的那些海誓山盟呢?什么都沒有!
我能感覺到她那顆充滿希望的心被徹底燒毀了。連續幾天,她失神地坐在輪椅里,只是茫然地看著前方。
我知道,她此刻一定是回想起“西安事變”發生后,遠在英國的她別離兒女,萬里赴難,趕到浙江奉化去陪伴已被關押的丈夫。
她一定是回想起,在湖南沅陵幽囚的歲月,張學良寫給她的那首詩:
卿名鳳至不一般,
鳳至落到鳳凰山。
深山古剎多梵語,
別有天地非人間。
她也一定是回想起,1964年張家派人從臺灣到洛杉磯,帶來張學良要求離婚的協議書,理由是張加入了基督教,教會不允許一夫多妻,他希望給身邊的趙四以名分,讓于鳳至退出。她極度憤怒地拒絕,當即給遠在臺灣的張學良打電話,要親自聽他的解釋。張學良讓她自己選擇,說:“我們永遠是我們。”這一句話像符咒,讓她徹底繳械,同意離婚。因為這句話讓她以為,她與張學良在生死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夫妻之情是牢不可破的,而婚姻只是一紙名義。為了換得漢卿更好的生存狀況,她連命都可以不要,還怕離婚嗎?
接下來的日子,能明顯看到老太太的身體衰弱下去,空洞的眼神里埋藏著深深的悲情。
魂歸
好在她的長孫女康妮經常過來。康妮就住在旁邊那幢于鳳至為張學良、趙四購置的別墅里。她一來總是懷里抱著貓,身邊跟著一群大大小小的狗,平添許多生氣。
于鳳至生過4個孩子。最小的兒子張閭琪12歲就夭折了,長女張閭瑛住在舊金山。長子張閭珣,后來去臺灣治病,1986年死在臺北榮總醫院。二兒子張閭玗給于鳳至擔任私人秘書,幫母親料理財務,領一份薪水。閭玗因車禍死于1981年,享年62歲,他育有二女一子,二女兒泰瑞、兒子萊斯利,因住得遠,都跟于鳳至來往不多。長女就是康妮,中文名張居偊,她只比我年長10歲,所以共同話題就比較多。她知道我的公公嚴北溟教授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便托我求字。當一幅墨寶跨洋過海寄到時,康妮特地請人精裱,配制鏡框,懸掛于客廳墻上。我白天上課,傍晚搭乘公交車到山腳下,徒步上山還有一段路,康妮還主動提出每天開車在山腳下接我。
對這祖孫二人,我始終懷著深深的感恩之情。
兩年后,我因為轉學而離開了于府,但康妮一直跟我保持聯系,每年都照例收到她寄來的圣誕賀卡。可是自2003年以后,就再也沒有了她的音信。我打電話過去,也成了奇怪的空號音。我知道康妮在1990年老太太去世后繼承了遺產,之后變賣了山上的別墅,搬到很遠的一個叫羚羊谷的地方,因地址不詳,無處查詢。歲月流逝,時光漸漸沖淡了心里的疑慮,只是偶爾會想起,康妮還好嗎?
2014年2月,我偶然讀到一本書,是國內張學良研究專家趙杰先生所撰的《張學良在美國的最后歲月》。文中提到,作者幾年前去好萊塢福樂園祭掃于鳳至的墓,發現旁邊有一個新增的墓位。作者寫道:“也許他(她)感受到長輩的寂靜和寂寞,現在由自己來填補空格了。金屬鑄就的墓碑上顯示著康斯坦斯·張的生卒年月,1945—2004。”
看來作者并不知道這個墓碑下埋的是誰,連性別是“他”還是“她”也不能確定,但是我在剎那間意識到,這是康妮!康斯坦斯正是康妮的名字。怪不得自從2003年以后就再也沒有收到她的圣誕卡,原來她早已離開人世,享年只有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