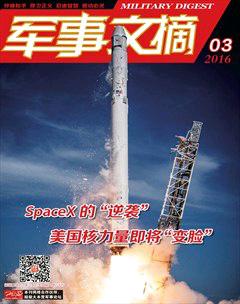試析毛澤東戰略評估理念與方法
易本勝
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是我們用來研究指導戰爭的馬克思主義“望遠鏡”和“顯微鏡”,也是我們研究其戰略評估理念與方法的源頭活水。如果說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那么毛澤東戰略評估理論與方法也是可以這樣“說明”的。依此推斷,其戰略評估的核心理念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實質也是“一分為二”,而且其中對立的統一性是相對的,對立的斗爭性是絕對的。研究表明,美軍凈評估主要考察處于競爭/對抗中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實體相互作用的狀況,其核心理念與方法的形成在不自覺中也運用了對立統一規律,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有類似之處。雖然二者并不對等,但做此比較有助于凈評估的“再中國化”和“通俗化”,有助于新形勢下戰略評估理論的構建。
全面分析,比較評估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說:“在20世紀30年代里,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的顯著特點是善于作敵我情況的對比。”這話是很有見地的。如,《論持久戰》對中日雙方及其盟友的軍事、政治、經濟、技術裝備、人員素質等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比較分析。從關鍵詞出現的次數看,“軍事”21次、“技術”19次、“政治”85次、“經濟”37次,可見其評估內容之全面;“比較”10次、“對比”13次、“敵我”29次、“相對”24次、“日本”187次、“中國”302次,中日比較多達100多處,足見比較項目之多和功夫之深。再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摸熟了自己的部隊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的部隊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很明顯,他強調不僅要靜態對比,而且要就敵我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和結果進行分析,實質是考察雙方對抗的狀態。從美國國防部官方的凈評估術語看,它是“對決定國家相對軍事能力的軍事、技術、政治、經濟和其他因素的比較分析,”也是強調多學科因素的比較分析,關注的不是某一方,也不是涵蓋雙方的細目清單,而是雙方相互作用的態勢和趨勢。

正反分析,對抗評估
研究指導戰爭既要充分看到各種有利條件,又要充分看到前進中可能的困難和問題。搞清敵我競爭/對抗的實際情形,不能把敵方估計得過高而把己方估計得過低,或相反。對此,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或戰斗的雙方是成群的武裝著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事實上,“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規律發生出來的”。如,他在《論持久戰》中明確講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無獨有偶,美國國防部前部長邁爾文·萊爾德也曾有類似表達,他講到:“簡單說來,凈評估與總體力量計劃一起,告訴我們現在在哪里,將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們如何才能到達。全面地說,凈評估就是比較分析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阻止或者有可能阻止我們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軍事、技術、政治和經濟因素是什么;一個是可以獲得的或可能獲得的、促進我們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因素是什么。”前句強調己方在敵我競爭/對抗中的所處位置、未來目標和實現途徑;后句強調前進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旨在搞清戰略資源,進而為戰略匹配。顯然,其基本精神與“正反分析、對抗評估”是一致的。
平衡分析,趨勢評估
平衡分析的本質是比較分析或不對稱分析。經過比較,平衡則對稱、不平衡則不對稱。其目的在于找到敵我雙方的不對稱及其發展趨勢,以便加以發展和利用。在《論持久戰》中,“平衡”或“不平衡”出現13次、“趨勢”出現5次。比如,“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按照美國凈評估辦公室原主任馬歇爾的話說,凈評估是“對美國與對手在國家安全領域某方面進行的比較分析”,是“從地緣政治和軍事使命的角度,對軍隊態勢和軍事平衡進行評估”。“其要旨不僅僅在于評估當前形勢,更重要的是預見潛在的長期趨勢”。顯然,其理念與方法也無外乎“比較”“平衡”和“趨勢”。

毛澤東不同版本的(倫持久戰)
優勢分析,競爭評估
軍隊作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敵我雙方爭奪主動權的過程,戰爭力量的優劣是主動與被動的客觀基礎,由于其中各種因素的構成和發展不平衡,因而優劣、強弱間而有之。這就給戰爭指導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對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統計《論持久戰》中關鍵詞的出現次數發現:“優勢”74次、“劣勢”42次、“優劣”13次、“強弱”17次,雖然“機會”只有3次,但“乘機”之“乘”出現7次之多,而“危險”也出現了5次。其他著作也有類似情況,可見毛澤東運用了競爭優勢分析技術。其實,凈評估的核心理念與方法也是競爭優勢分析。臺灣學者潘東豫在《凈評估:全面掌握國家企業優勢》中就明確指出,凈評估作為“策略規劃過程中的一環,是國防規劃者自企業界引進的一種國家安全戰略分析技術,與現行產業界所流行的SWOT(優勢、劣勢、機遇和威脅)分析,并無二致。”
本質分析,動因評估
本質分析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研究事物內部最底層的驅動因素。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此前,他在《實踐論》中也講到:“看事情必須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分析方法。”“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些都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凈”的過程,反映出對“凈”結果的追求。研究發現,馬歇爾在1972年8月也有類似表達:“國家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在不同競爭中美國所處的位置。他們對我們所處的相對位置以及有何種趨勢或因素可以影響到它很感興趣。更進一步說,了解上述因素和趨勢產生的原因,顯得極端重要。”這明確強調了凈評估的關鍵在于搞清競爭態勢的優劣或強弱(是什么),及其決定因素(為什么)和深層作用機理(為什么的為什么),旨在追求最終的“凈結果”。
狀態分析,能力評估
作為競爭狀態評估,戰略評估主要表現為能力評估。無論是在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都非常關注敵對雙方力量對比轉化的問題,強調針對戰略能力進行評估。比如:“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美國學者菲利普·卡爾博爾博士也有同樣看法,他在《為國防部長服務的凈評估及戰略發展:初期的形成及對未來的啟示》中寫道:“對我最至關重要的凈評估似乎是:美國和蘇聯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長期的政治、軍事競爭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樣的?”不僅如此,毛澤東和馬歇爾都強調對于“能力”的三個層次考察:一是由種類、數量等決定的物質力;二是由結構比例與匹配狀態決定的結構力;三是由運用方式、方法和時空決定的行動力。
質量分析,綜合評估
軍事上的發展變化,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量變的漸進性和質變的突發性的有機統一。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體現了量變和質變兩種狀態。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分析戰爭三個階段的變化,就是把握戰爭從量變到質變的典范。其戰略評估是從定性到定量再回到定性的綜合集成,經過了兩次認識的飛躍。事實上,毛澤東不僅擅長定性分析,也非常強調量化分析。他特別指出:“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應該說,我軍的定性分析比較成熟,美軍的定量分析有些過頭,但是最后都要走到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上來。當年,美軍的凈評估就因早期系統分析僅重“量化”因素而忽視“非量化”因素,逐步發展出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替代方法。
場景分析,推演評估
場景分析就是借助假定場景(想定、構想)條件和對抗推演過程所進行的敵我交互作用的分析與評估。有效避免一廂情愿,必須考察這種“行動-反應”的過程及結果。毛澤東常以棋局來比喻這種互動。如,“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再如,“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又如,“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研究表明,美軍及其智囊機構常用“蘭德戰略評估系統”和“聯合一體化應急模型”等工具進行兵棋推演。“恐怖的海峽”和“空海一體戰”理論都是這種兵棋推演的產物。不過,毛澤東的棋局更似高級棋手間沒有棋子和棋盤的“口弈”,而且他一人扮演了紅、藍、綠、白多方角色,并以戰爭實踐來驗證。

所不同者主要有四點:一是階級立場不同。毛澤東代表無產階級立場,馬歇爾等代表資產階級立場。二是背景條件不同。毛澤東軍事辯證法主要是在國內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軍事斗爭和抗日戰爭時期中日兩國的對抗中形成的;馬歇爾的凈評估方法主要是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的斗爭與對抗中研究敵對雙方的對比和相互關系。三是深廣程度不同。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更為高遠、寬廣、精深,因而更為抽象,科學性、藝術性也更強;馬歇爾的凈評估方法則聚焦于戰略評估領域,更為具體、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四是發展趨勢不同。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研究在東方“文、史、哲”氛圍特別是在我長期和平環境中,哲學化傾向明顯(盡管這并非毛澤東的本意);而凈評估方法在西方“數、理、化”氛圍特別是美重實務而輕理論的傳統下,呈現工程化趨勢。
責任編輯:彭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