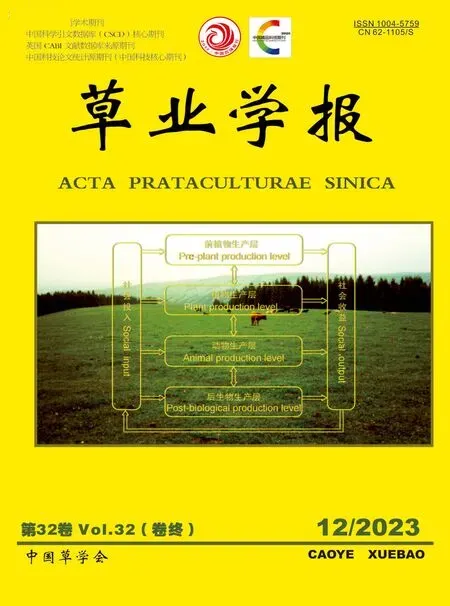暖季草場(chǎng)不同放牧方式對(duì)牦牛藏羊生產(chǎn)力的影響
馮斌,楊曉霞,劉文亭,劉玉禎,呂衛(wèi)東,張振祥,孫彩彩,周沁苑,王芳草,于澤航,董全民
(青海大學(xué)畜牧獸醫(yī)科學(xué)院,青海省畜牧獸醫(yī)科學(xué)院,青海省高寒草地適應(yīng)性管理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三江源區(qū)高寒草地生態(tài)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青海 西寧 810016)
當(dāng)前,放牧仍然是高寒草地最重要的利用方式之一,合理的利用方式對(duì)維護(hù)高寒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shí)也是協(xié)調(diào)生態(tài)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的重要舉措,在保護(hù)好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同時(shí),可提高牧民的經(jīng)濟(jì)收入[1]。20 世紀(jì)中后期,由于人為的超載放牧,高寒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完整性一度被破壞,生態(tài)系統(tǒng)調(diào)節(jié)功能喪失,高寒草地發(fā)生了嚴(yán)重的退化,草地生產(chǎn)力和生物多樣性降低[2]。近些年,由于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戰(zhàn)略的實(shí)施,特別是高寒草地放牧管理措施的優(yōu)化,使得草地退化的趨勢(shì)被逆轉(zhuǎn),退化草地得到了治理和修復(fù),并已取得極大的成效[3-4]。當(dāng)前,全球氣候變化和放牧對(duì)高寒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的威脅仍然巨大,作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生態(tài)系統(tǒng)脆弱,一旦功能喪失,修復(fù)周期和修復(fù)成本都是巨大的[5]。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和生產(chǎn)力的維持與草地群落生物多樣性密切相關(guān)。研究放牧與家畜的互作關(guān)系,既可以掌握草地群落對(duì)放牧的響應(yīng)規(guī)律,同時(shí)也有助于了解家畜在放牧條件下的生長(zhǎng)性能。研究認(rèn)為放牧強(qiáng)度不當(dāng)易造成草地群落發(fā)生逆向演替,輕則降低草地的生產(chǎn)力,改變草地的物種組成和群落結(jié)構(gòu),重則導(dǎo)致草場(chǎng)嚴(yán)重的沙化、荒漠化或退化為黑土灘[6-7];短期禁牧或休牧可以有效提高草地的生產(chǎn)力,長(zhǎng)期禁牧對(duì)草地有相反的作用,影響草地返青從而增加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的概率[8-9];而中度放牧對(duì)維護(hù)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健康、群落結(jié)構(gòu)穩(wěn)定和生產(chǎn)力維持具有重要的作用[10-11],中度放牧干擾假說(shuō)被認(rèn)為是維護(hù)草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機(jī)制之一[12-13]。
家畜對(duì)草地的影響,源于其取食、排泄和躺臥等行為過(guò)程,不同類(lèi)型家畜形態(tài)、營(yíng)養(yǎng)需求、生理特性或行為特征差異較大,對(duì)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各有不同[14]。長(zhǎng)期單一的放牧模式可能改變?nèi)郝涞奈锓N組成,影響牧草營(yíng)養(yǎng)成分及其可消化性,草地的產(chǎn)量和品質(zhì)也會(huì)影響家畜的生長(zhǎng)。草地的草產(chǎn)量和牧草品質(zhì)是評(píng)價(jià)草地資源的重要指標(biāo),草產(chǎn)量的高低影響草地承載力,品質(zhì)的好壞則會(huì)影響家畜的生產(chǎn)性能和生命活動(dòng)[15-16]。青藏高原氣候惡劣,牧草生長(zhǎng)期短,處在不同生長(zhǎng)期的牧草,其營(yíng)養(yǎng)成分存在季節(jié)動(dòng)態(tài)變化[17-18],對(duì)不同區(qū)域牧草消化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高寒牧區(qū)6-8 月牧草消化率較高,可以有效滿(mǎn)足家畜生產(chǎn)性能的需求,枯黃期牧草品質(zhì)降低,補(bǔ)飼是提升放牧家畜生產(chǎn)性能的重要措施[19]。
牦牛起源于青藏高原,是一種適應(yīng)高寒極端氣候條件的物種,被稱(chēng)為“高原之舟”[20];藏系綿羊由盤(pán)羊演化而來(lái),長(zhǎng)期生活在高寒地區(qū),能夠很好地適應(yīng)高原地區(qū)寒冷的氣候條件[21]。在中度放牧的基礎(chǔ)上將不同種類(lèi)的家畜進(jìn)行混合放牧的多樣化家畜放牧方式,可以直接或間接增加草地資源的異質(zhì)性以及增加草地物種擴(kuò)散和隨機(jī)干擾過(guò)程,有利于提高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多樣性和營(yíng)養(yǎng)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14]。大型草食動(dòng)物可以基于其體型優(yōu)勢(shì)[22-23],在草地當(dāng)中實(shí)現(xiàn)較高的采食量[24],并實(shí)現(xiàn)以排泄為主的養(yǎng)分長(zhǎng)距離運(yùn)輸[25],進(jìn)而調(diào)節(jié)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26],而草地的構(gòu)成及產(chǎn)量反之又影響著家畜的生長(zhǎng)和生產(chǎn)。本研究利用青藏高原特有家畜—牦牛、藏羊,基于高原常見(jiàn)的牦牛單牧、藏羊單牧和牦牛藏羊混牧等放牧方式,以探討:1)暖季不同家畜組合放牧對(duì)牦牛、藏羊生長(zhǎng)的影響;2)不同家畜組合放牧對(duì)家畜采食量和牧草營(yíng)養(yǎng)的影響,以期為高寒草地合理放牧模式的制定和放牧牦牛、藏羊的科學(xué)補(bǔ)飼提供基礎(chǔ)數(shù)據(jù)和理論依據(jù)。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qū)域概況
青海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組成部分,分布著廣袤的天然草地,是重要的畜牧業(yè)基地,由于青藏高原獨(dú)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條件,培育了高原特有的畜種——牦牛、藏羊。本研究試驗(yàn)樣地位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縣西海鎮(zhèn)內(nèi)(36°55′13″ N,100°56′22″ E,海拔3000~3100 m),該地區(qū)年均降水量為400 mm 左右,年日照時(shí)數(shù)為2580~2750 h,年均溫1.5 ℃,土壤類(lèi)型主要以高山草甸土為主。由于地處高原氣候較為寒冷,全年牧草生長(zhǎng)季較短,該地區(qū)牧草在5-6 月開(kāi)始返青,7-8 月進(jìn)入牧草生長(zhǎng)盛期,9-10 月進(jìn)入枯黃期。該地區(qū)天然草地以放牧牦牛和藏羊?yàn)橹饕睦梅绞剑饕躁笈文痢⒉匮騿文粱蜿笈2匮蚧炷恋男问竭M(jìn)行冬(冬春)夏(夏秋)兩季輪牧[27]。
1.2 試驗(yàn)設(shè)計(jì)
不同家畜組合的放牧試驗(yàn)開(kāi)始于2014 年,在基況較為均一的天然草地設(shè)牦牛單牧(only yak grazing,YG)、藏羊單牧(only Tibetan sheep grazing, SG)、牦牛藏羊1∶6 混牧(yak and Tibetan sheep grazing mixed as 1∶6, MG1∶6)、牦牛藏羊1∶4 混牧(yak and Tibetan sheep grazing mixed as 1∶4, MG1∶4)和牦牛藏羊1∶2混牧(yak and Tibetan sheep grazing mixed as 1∶2,MG1∶2)5 個(gè)試驗(yàn)處理,每個(gè)處理設(shè)有3 個(gè)重復(fù),共有15 個(gè)放牧小區(qū)(表1)。放牧強(qiáng)度為中等強(qiáng)度,該強(qiáng)度與區(qū)域內(nèi)當(dāng)前天然草地利用的強(qiáng)度基本一致。放牧試驗(yàn)在植物生長(zhǎng)的暖季6-10 月進(jìn)行,牧草利用率保持在50%左右,由于受試驗(yàn)小區(qū)面積所限,為保證放牧強(qiáng)度適中,每月在放牧小區(qū)的放牧?xí)r間平均為10 d。

表1 放牧試驗(yàn)設(shè)計(jì)Table 1 Grazing experiment design
試驗(yàn)家畜選擇同齡公牦牛12 頭、公藏羊42 只,牦牛為1.5 歲亞成體,體重為(100±5) kg,藏羊?yàn)? 歲亞成體,體重為(30±2) kg。1 頭牦牛干物質(zhì)的日采食量約等于3 只藏羊干物質(zhì)的日采食量,對(duì)試驗(yàn)各小區(qū)面積進(jìn)行換算,以保證各放牧小區(qū)放牧強(qiáng)度一致。放牧期間對(duì)各放牧小區(qū)家畜不進(jìn)行補(bǔ)飼,每日只對(duì)各小區(qū)蓄水槽補(bǔ)充家畜所需的飲用水即可。此外,在放牧前對(duì)家畜進(jìn)行投藥驅(qū)蟲(chóng),以確保家畜在放牧期間的正常采食[28]。
1.3 數(shù)據(jù)測(cè)定
在2020-2022 年進(jìn)行家畜生產(chǎn)性能和家畜采食量的測(cè)定。每年首次放牧是在牧草返青期的后期進(jìn)行,時(shí)間為6 月15-25 日,稱(chēng)為牧草返青期;第2 次放牧是在牧草生長(zhǎng)盛期進(jìn)行,時(shí)間為7 月20 日-8 月10 日,稱(chēng)為牧草生長(zhǎng)期;第3 次放牧是在牧草枯黃期進(jìn)行,時(shí)間為9 月20 日-10 月10 日,稱(chēng)為牧草枯黃期。每次放牧前和放牧后對(duì)牛羊進(jìn)行空腹稱(chēng)重,為減小牛羊在稱(chēng)重當(dāng)日采食帶來(lái)的誤差,稱(chēng)重時(shí)間均選在稱(chēng)重當(dāng)日的清晨進(jìn)行。通過(guò)扣籠法測(cè)定家畜采食量,每個(gè)放牧小區(qū)放置3 個(gè)1 m×1 m 的扣籠用于測(cè)定家畜采食量,并且將2020 年8 月采集到的牧草進(jìn)行中性洗滌纖維、酸性洗滌纖維和粗蛋白的測(cè)定[29]。
家畜生產(chǎn)性能相關(guān)指標(biāo)計(jì)算公式如下:1)日增重:不同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放牧后和放牧前放牧家畜體重的差值與放牧?xí)r間(d)的比值即為家畜的日增重。2)暖季增重:各個(gè)放牧?xí)r期增重之和即為試驗(yàn)的暖季增重。3)單位面積家畜增重:P=W×S[30],W為家畜暖季增重(weight gain in warm season),S為各放牧處理暖季放牧率(warm season grazing rate),P為單位草地面積的放牧畜群總增重(productivity per unit area)。
1.4 數(shù)據(jù)分析與處理
利用Excel 2019 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理,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 對(duì)各放牧方式下家畜暖季增重、家畜日增重、單位面積家畜生產(chǎn)力、牧草營(yíng)養(yǎng)及家畜采食量進(jìn)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結(jié)果以平均值±標(biāo)準(zhǔn)誤的形式表示。運(yùn)用Duncan 法進(jìn)行處理間的多重比較,并采用皮爾森相關(guān)系數(shù)法對(duì)家畜暖季增重與各牧草生長(zhǎng)期牛羊日增重進(jìn)行相關(guān)性分析。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放牧方式對(duì)牦牛增重的影響
綜合2020-2022 年試驗(yàn)結(jié)果,不同放牧方式利用草地對(duì)牦牛在各個(gè)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的日增重?zé)o顯著影響,各處理間的差異不顯著(P>0.05);3 年的試驗(yàn)結(jié)果表明在不同的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放牧對(duì)牦牛的日增重有顯著的影響,結(jié)果顯示牦牛日增重在牧草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顯著高于牧草枯黃期(P<0.05)。2020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牦牛暖季增重為YG>MG1∶2>MG1∶6>MG1∶4,2021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牦牛暖季增重為YG>MG1∶6>MG1∶2>MG1∶4,2022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牦牛暖季增重為MG1∶6>YG> MG1∶2>MG1∶4,盡管各處理間差異并不顯著(P>0.05),但結(jié)果顯示YG 使得牦牛暖季增重在各處理中最高,MG1∶4 使得牦牛暖季增重在各處理中最低(表2)。

表2 不同放牧方式下牦牛日增重和暖季增重Table 2 Average daily weight gain and weight gain in warm season of yak under different livestock assembly
2020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牦牛單位面積增重為YG>MG1∶2>MG1∶6>MG1∶4,2021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YG>MG1∶6>MG1∶2>MG1∶4,2022年的結(jié)果顯示:MG1∶6>YG>MG1∶2>MG1∶4,盡管各處理間差異并不顯著(P>0.05),但各年際的結(jié)果均顯示YG 使得牦牛單位面積增重在各處理中較高,MG1∶4 使得牦牛單位面積增重在各處理中最低(表3)。

表3 單位面積牦牛增重Table 3 Yak productivity per unit area (kg·hm-2)
牦牛暖季增重和牧草生長(zhǎng)季的各個(gè)時(shí)期的牦牛日增重的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顯示,2020 年牧草生長(zhǎng)期MG1∶6 牦牛日增重和牦牛暖季增重顯著正相關(guān)(P<0.05),2022 年牧草枯黃期MG1∶6 牦牛日增重和牦牛暖季增重顯著正相關(guān)(P<0.05),其余各處理牦牛日增重與牦牛暖季增重?zé)o顯著相關(guān)關(guān)系。綜合3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牦牛暖季增重與牦牛在各個(gè)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的日增重并無(wú)顯著相關(guān)性(表4)。

表4 不同放牧方式下牦牛暖季增重與牧草各生長(zhǎng)時(shí)期牦牛日增重的相關(guān)性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weight gain during warm season and average daily weight gain of yak during pasture growth season under different livestock assembly
2.2 放牧方式對(duì)藏羊增重的影響
綜合3 年試驗(yàn)結(jié)果,在各個(gè)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不同放牧方式利用草地對(duì)藏羊的日增重并無(wú)顯著的影響,各處理間的差異不顯著(P>0.05);3 年的試驗(yàn)結(jié)果表明不同的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放牧對(duì)藏羊的日增重有顯著的影響,2020 年藏羊日增重為牧草生長(zhǎng)期>返青期>枯黃期,2021-2022 年藏羊日增重為牧草返青期>生長(zhǎng)期>枯黃期,且藏羊日增重在牧草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顯著高于牧草枯黃期(P<0.05)。連續(xù)3 年的暖季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2020 年藏羊暖季增重為MG1∶2>MG1∶4>SG>MG1∶6;2021 年藏羊暖季增重為MG1∶2>SG>MG1∶4>MG1∶6;2022 年藏羊暖季增重為SG>MG1∶6>MG1∶4>MG1∶2,各年際藏羊暖季增重并無(wú)顯著差異(P>0.05)(表5)。

表5 不同放牧方式下藏羊日增重和暖季增重Table 5 Average daily weight gain and weight gain in warm season of Tibetan sheep under different livestock assembly
連續(xù)3 年的暖季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2020 年藏羊單位面積增重為MG1∶2>MG1∶4>SG>MG1∶6;2021 年藏羊單位面積增重為MG1∶2>SG>MG1∶4>MG1∶6;2022 年藏羊單位面積增重為SG>MG1∶6>MG1∶4>MG1∶2,但各處理間均無(wú)顯著差異(P>0.05)(表6)。

表6 單位面積藏羊增重Table 6 Tibetan sheep productivity per unit area (kg·hm-2)
藏羊暖季增重和牧草生長(zhǎng)季的各個(gè)時(shí)期的藏羊日增重的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顯示,2020 年牧草生長(zhǎng)期MG1∶4 藏羊日增重和藏羊暖季增重顯著正相關(guān)(P<0.05),牧草枯黃期MG1∶6 和MG1∶4 藏羊日增重與藏羊暖季增重顯著正相關(guān)(P<0.05);2021 年牧草返青期SG 藏羊日增重和藏羊暖季增重極顯著正相關(guān)(P<0.01);2022 年牧草返青期MG1∶2 藏羊日增重和藏羊暖季增重顯著正相關(guān)(P<0.05),牧草枯黃期MG1∶6、MG1∶4 和MG1∶2 藏羊日增重與藏羊暖季增重存在顯著或極顯著相關(guān)關(guān)系(P<0.05 或P<0.01)。綜合3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藏羊暖季增重與藏羊在各個(gè)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的藏羊日增重并無(wú)顯著相關(guān)性(表7)。

表7 不同放牧方式下藏羊暖季增重與牧草各生長(zhǎng)時(shí)期藏羊日增重的相關(guān)性Table 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eight gain in warm season and average daily weight gain of Tibetan sheep in each growing season of pasture under different livestock assembly
2.3 放牧方式對(duì)牧草營(yíng)養(yǎng)、家畜采食量和單位面積家畜增重的影響
牧草各營(yíng)養(yǎng)成分測(cè)定結(jié)果表明,牧草酸性洗滌纖維含量為MG1∶4>SG>MG1∶2>YG>MG1∶6,其中MG1∶4 與YG 和MG1∶6 差異顯著(P<0.05),中性洗滌纖維含量為YG>MG1∶6>MG1∶4>MG1∶2>SG,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P>0.05),粗蛋白含量為MG1∶2>MG1∶4>SG>YG>MG1∶6,其中MG1∶2 與MG1∶6 差異顯著(P<0.05)。暖季整個(gè)放牧期單位面積家畜采食量為MG1∶2>MG1∶6>SG>YG>MG1∶4,但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P>0.05)(表8)。

表8 不同放牧方式對(duì)牧草營(yíng)養(yǎng)和家畜采食量的影響Table 8 Effects of different livestock assembly on vegetation nutrition and feed intake
各處理單位面積家畜增重結(jié)果比較表明,2020 年單位面積家畜增重為YG>MG1∶2>SG>MG1∶6>MG1∶4,2021 年單位面積家畜增重為SG>YG>MG1∶2>MG1∶4>MG1∶6,2022 年單位面積家畜增重為SG>MG1∶6>YG>MG1∶4>MG1∶2,3 年單位面積家畜平均增重為SG>YG>MG1∶2>MG1∶6>MG1∶4,其中SG 與MG1∶4 差異顯著(P<0.05)(表9)。

表9 單位面積家畜增重Table 9 Livestock productivity per unit area (kg·hm-2)
3 討論
3.1 不同放牧方式及牧草不同生長(zhǎng)時(shí)期對(duì)牦牛暖季增重的影響
環(huán)境、營(yíng)養(yǎng)和放牧管理方式是影響牦牛生產(chǎn)力發(fā)揮的關(guān)鍵因素,家畜生長(zhǎng)最基礎(chǔ)的物質(zhì)源于牧草的營(yíng)養(yǎng)供給,充足優(yōu)質(zhì)的牧草可以有效地提升家畜的生產(chǎn)性能[31]。個(gè)體未達(dá)到成熟之前,牦牛體重隨年齡的增加而逐年增加,一般暖季增長(zhǎng)較快,而在冷季則有所減輕[32]。在牧草生長(zhǎng)季,牧草品質(zhì)由優(yōu)變劣,牧草消化率從返青期、生長(zhǎng)期到枯黃期逐漸降低[17-19,33]。3 年的研究表明,牦牛日增重在牧草返青期、生長(zhǎng)期到枯黃期逐漸降低,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生長(zhǎng)期牧草的粗蛋白、粗纖維等物質(zhì)顯著不同,特別是在枯黃期牧草營(yíng)養(yǎng)降至最低;此外,過(guò)了秋分日之后草原晝夜氣溫均顯著下降,盡管不會(huì)嚴(yán)重影響牦牛的代謝,但始終不利于牦牛生產(chǎn)性能的發(fā)揮,且使較多的能量損耗在機(jī)能維持方面,這也是導(dǎo)致在牧草的枯黃期牦牛日增重呈負(fù)增長(zhǎng)的重要原因。從3 年放牧的總體情況來(lái)看,牧草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對(duì)牦牛的日增重存在顯著的影響,表明在這兩個(gè)時(shí)期不同放牧處理間牧草總體的營(yíng)養(yǎng)價(jià)值存在顯著差異。研究認(rèn)為家畜由于在形態(tài)、生理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導(dǎo)致其采食方式和營(yíng)養(yǎng)需求明顯不同,且形態(tài)和生理差異越大,對(duì)草地多樣性的影響越大[14]。由此可知,中度放牧條件下,家畜的組合方式或組合比例多樣化的放牧方式會(huì)影響草地的群落結(jié)構(gòu),進(jìn)而影響草地生物量和飼用價(jià)值。那么在牧草的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各放牧處理間的差異就較為顯著,就牦牛暖季生產(chǎn)力而言,綜合比較連續(xù)3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不同放牧方式對(duì)牦牛暖季增重并無(wú)顯著的影響,這也與牦牛暖季增重和牦牛在牧草各生長(zhǎng)時(shí)期日增重并無(wú)顯著相關(guān)性的結(jié)果相一致。多樣化家畜放牧理論認(rèn)為,放牧強(qiáng)度適度的情況下,不同家畜組合會(huì)增加放牧草地資源的異質(zhì)性從而改變?nèi)郝涞亩鄻有裕瑢?dǎo)致草地更高的復(fù)雜性[14],可以認(rèn)為多樣化家畜放牧最終會(huì)對(duì)群落結(jié)構(gòu)造成影響,群落結(jié)構(gòu)的改變也必將影響家畜的生產(chǎn)力,但目前這樣的上行效應(yīng)或下行效應(yīng)的周期多長(zhǎng),且中間是否存在滯后效應(yīng),即多樣化放牧改變了草地群落結(jié)構(gòu),而草地如何影響家畜生產(chǎn)力的發(fā)揮仍待探究。
3.2 不同放牧方式及牧草不同生長(zhǎng)時(shí)期對(duì)藏羊暖季增重的影響
同樣粗放式放牧條件下藏羊生產(chǎn)力的發(fā)揮也會(huì)受到環(huán)境、營(yíng)養(yǎng)和放牧管理方式等因素的影響[34-35]。藏羊快速生長(zhǎng)的時(shí)期是哺乳期和哺乳后期,并且此階段對(duì)藏羊后期的生長(zhǎng)也會(huì)產(chǎn)生影響[36]。溫度對(duì)藏羊的生長(zhǎng)具有重要的作用,5-11 月的溫度適宜也是牧草的生長(zhǎng)季,是藏羊生長(zhǎng)和發(fā)育的關(guān)鍵階段[34-35,37]。從連續(xù)放牧3 年的試驗(yàn)結(jié)果來(lái)看,在整個(gè)牧草生長(zhǎng)季,藏羊在牧草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日增重高于枯黃期。研究表明,藏羊在5~20 ℃的條件下生長(zhǎng)良好,高于或者低于這個(gè)溫度范圍都易引發(fā)藏羊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不利于藏羊的生長(zhǎng)[34,36]。比較各牧草生長(zhǎng)期藏羊的日增重,結(jié)果表明同一牧草生長(zhǎng)期并不會(huì)顯著影響各放牧處理下的藏羊日增重。研究認(rèn)為,藏羊基于其消化系統(tǒng)和營(yíng)養(yǎng)需求,在采食過(guò)程中易選擇高營(yíng)養(yǎng)低次生代謝產(chǎn)物的牧草[38],具有廣食性,在中度放牧條件下,食源充足,藏羊在不同處理下各牧草生長(zhǎng)期日增重并無(wú)顯著差異。就藏羊暖季生長(zhǎng)而言,綜合比較連續(xù)3 年的放牧試驗(yàn)結(jié)果,SG 和MG1∶2 混牧有利于藏羊增重,盡管在各個(gè)牧草生長(zhǎng)期各處理間的藏羊日增重并無(wú)顯著差異,但從整個(gè)暖季增重的結(jié)果來(lái)看,SG 和MG1∶2 混牧有利于維持藏羊最大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揮。就總體而言,藏羊暖季增重與各牧草生長(zhǎng)期藏羊日增重并無(wú)顯著相關(guān)性,主要在于各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藏羊日增重差異并不顯著。
3.3 不同放牧方式對(duì)牧草營(yíng)養(yǎng)、家畜采食量和單位面積的家畜生產(chǎn)力的影響
青藏高原牧草生長(zhǎng)季短,季節(jié)性強(qiáng),全年牧草供應(yīng)不均衡[39]。牧草營(yíng)養(yǎng)品質(zhì)是草地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的重要指標(biāo)之一,家畜的生長(zhǎng)發(fā)育與牧草品質(zhì)的優(yōu)劣密切相關(guān),放牧促進(jìn)了牧草的更新,有利于延緩牧草的木質(zhì)化進(jìn)程,增加牧草的粗蛋白含量,減少粗纖維的形成,提高牧草的消化率[15-18,40-41],故牧草返青期、生長(zhǎng)期的營(yíng)養(yǎng)品質(zhì)優(yōu)于牧草枯黃期。多樣化家畜放牧理論認(rèn)為[14],放牧多種家畜利用體型差異、營(yíng)養(yǎng)需求差異和采食特點(diǎn)等方面的差異,可以增加草地的異質(zhì)性,進(jìn)而改變草地群落的組成和營(yíng)養(yǎng)成分。對(duì)各放牧處理下牧草營(yíng)養(yǎng)測(cè)定結(jié)果表明,放牧方式對(duì)草地營(yíng)養(yǎng)成分并未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家畜產(chǎn)生顯著的擇食性在于草地牧草種類(lèi)較為豐富,特別對(duì)于優(yōu)勢(shì)物種而言,研究區(qū)域可食性?xún)?yōu)勢(shì)物種較為單一,可能是牧草營(yíng)養(yǎng)未產(chǎn)生顯著差異的原因,亦或放牧?xí)r間尺度遠(yuǎn)遠(yuǎn)不足以對(duì)草地群落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各放牧方式下整個(gè)放牧?xí)r期的家畜單位面積采食量并無(wú)顯著差異,也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和放牧強(qiáng)度一致性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對(duì)牦牛和藏羊營(yíng)養(yǎng)需求相關(guān)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藏羊喜食高營(yíng)養(yǎng)和低次生代謝物植物,而牦牛則可忍受營(yíng)養(yǎng)相對(duì)較低但生物量較高的植物[38,42],這可能是單一家畜放牧下藏羊單位面積增重優(yōu)于牦牛的原因。綜合分析3 年的放牧試驗(yàn)表明,就暖季增重和單位面積家畜的生產(chǎn)力而言,YG、SG 和MG1∶2 將有效地提高草地牧草利用率,可在中度放牧強(qiáng)度下增加草地的畜產(chǎn)品產(chǎn)量。
4 結(jié)論
高寒草地在中度放牧利用下,對(duì)家畜生產(chǎn)力的影響,既存在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的差異,又存在家畜類(lèi)型的差異,還存在放牧方式的差異。研究結(jié)果表明,就牧草生長(zhǎng)時(shí)期而言,在牧草返青期和生長(zhǎng)期牦牛和藏羊的日增重顯著大于牧草枯黃期;就家畜生產(chǎn)力而言,在不同放牧方式下牦牛暖季增重在YG 最高,在MG1∶2 和MG1∶6 相對(duì)較高,藏羊暖季增重在MG1∶2 中最高,在SG 和MG1∶4 相對(duì)較高,單一家畜放牧單位面積增重SG 較高,牦牛和藏羊2種家畜混合放牧為MG1∶2 較高。基于以上試驗(yàn)結(jié)果,建議當(dāng)?shù)啬翍?hù)在日常的家畜生產(chǎn)過(guò)程中,以中度放牧為基礎(chǔ),采用SG 單牧或MG1∶2 混牧的形式進(jìn)行放牧生產(chǎn),同時(shí)在牧草枯黃期減少家畜數(shù)量并對(duì)放牧家畜進(jìn)行精料補(bǔ)飼;同時(shí)建議牧戶(hù)修建棚圈,在牧草枯黃期開(kāi)始使家畜在夜間回棚圈休息,減少家畜由于夜間為維持體能的能量損耗,以提高草地的畜產(chǎn)品產(chǎn)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