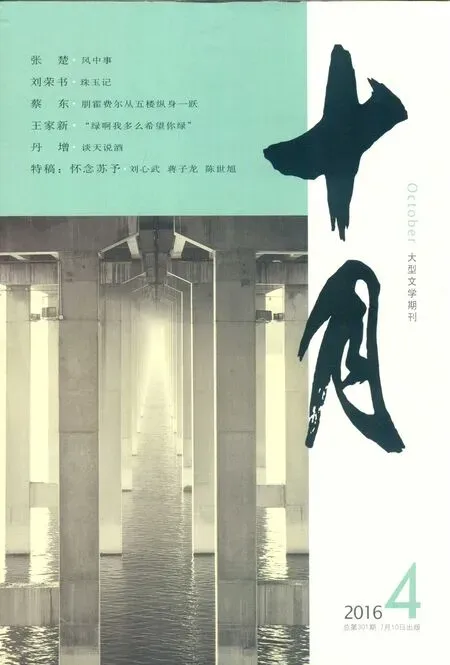考古
李敬澤
他坐在臺階上,望下去,天下熱鬧。國家博物館的內庭如此高曠,設計者的本意是讓人懾于自己的小,收起來,低下去,正心誠意。可現在,這里是盛大的集市,人群洶涌,誰顧得天高地厚,到處跑著亢奮的孩子,跟著疲憊的家長。
放假了,國博比國貿熱鬧。緩緩站起來,右膝硬著,但不再刺痛。他下樓走向南館。《絲綢之路與俄羅斯民族文物》在南館三樓,他想,他們本該把這個展覽放在北館,而《海上絲綢之路畫展》倒應該在南館,畫的都是往昔的廣東和南洋。
他剛在畫展的開幕式上講完了話。那些畫讓他想起以前看過的18、19世紀西方人在遠東留下的速描或版畫,波濤、船舶、廣州十三行或澳門的街景。不同的是,那時,我們被觀看,而現在,一個中國畫家變成了觀看者。
——這當然是至關重要的轉變。他加重了語氣:這意味著中國正在重新界定自己的歷史和未來。
話說完了,不溜出來還等什么。他不是一個盡職的聽眾,當然,他知道,自己的話其實也沒人要聽。南館的三樓明顯清靜了,走到展廳門口,卻被一身黑衣的博物館小姐攔住:收費的啊。
哦。三十塊。摸出錢遞過去,小姐小臉一揚:那邊!
那邊是收款臺。交了錢,拿了票,他覺得膝蓋又疼起來。
展廳里寥寥幾個人,他有一眼沒一眼地轉著,想了想為什么好好一個姑娘,一張嘴收費就活像一個衙役,顯然,在上意識或者下意識里,她是把收費準入當成了一項權力。而且國博的制服能不能別這么黑和酷,看看人家俄羅斯各民族的衣裳,撐在架子上,關在櫥窗里,隨時會破窗而出,跳舞。
他端詳了一會兒頓河哥薩克的服飾,想象了一下格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婭穿上衣裳的樣子,忽然想到,這展覽和絲綢之路真沒什么關系。是的,展廳進門有一張圖,一條線蜿蜒橫穿俄羅斯南部,從西伯利亞到伏爾加河到里海,這是絲綢之路的北路,而這個展覽不過是排列著沿線各民族的服裝和用度。他想,穿著這些衣裳的人,他們并不知道他們所生息的地方是絲綢之路。他們的空間被重新命名,然后他們的生活被賦予新的意義。
——當然,這個展覽一定是中方策劃的。世界正被重新整理。
其實,中國人本來也不知道絲綢之路。一代一代的人走在路上,貿易、求法、征戰,但他們并不知道那是“絲綢之路”,對他們來說,那只是自家的命,是世間的緣與苦。直到拉鐵摩爾造出了“絲綢之路”這個詞,直到斯文赫定寫了《絲綢之路》那本書,大漠風煙、酷熱苦寒、白骨和血汗,都有了一個名字,隱隱閃光的、柔軟華美的名字:絲綢之路。
像沙丘一樣柔軟,他忽然想起80年代曾經看過日本NHK拍攝的紀錄片《絲綢之路》,目瞪口呆、心馳神往;喜多郎的配樂魅惑綿長,當年他買了盒帶,日日播放,抽絲一般,在腦子里繚繞,快繞出一個盤絲洞了……
必須感謝拉鐵摩爾,給他發一噸絲綢。他贈予我們一個好詞,這個詞讓我們以另外一種全球視野看待我們的歷史,重新發現和整理我們的記憶和經驗。邊塞和窮荒本是天下盡頭,是邊緣和界限,現在,由于這個詞,界限被越過,你必須重新想象中國,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種歷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來。
老馬告訴他,這是范仲淹的慶州。
他知道。來之前他百度了甘肅慶陽,知道今之慶陽便是古之慶州。他正在慶陽的街上狂走,他必須讓手機上微信運動的顯示步數達到一萬,然后沮喪地看著居然還有瘋子達到了一萬五、兩萬甚至三萬。
老馬說:他在這兒寫了《漁家傲》。
是的,這個領兵的文人,他祖籍蘇州,在山東度過了慘淡童年,然后讀書、做官,他可能從未想過有朝一日他會成為一個帶兵的人,來到這偏荒的慶州,殺伐決斷,看著人因他的命令而死,血流于黃土,孤兒寡母哀哭。
老馬走得從容,幾乎是邁著方步了。他是本地人,他安穩地走在從小走到老的地上,晚上剛喝了幾杯酒,老馬忽然對著空曠的街朗聲誦起《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誦罷,老馬向我一指,笑道:這是你們京城來人的牢騷!
——北宋康定二年,1040年,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出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延州知州,次年改知慶州。延州乃延安,慶州為慶陽,由陜北到隴東,文雅風流的大宋面對著血氣方剛的西夏的挑戰,在儒者范仲淹的對面,是馬如龍、刀如風的李元昊。
范仲淹頂住了。宋以后,書生領兵,最成功者曾國藩。范文正比不了曾文正,但也絕非紙上談兵的書生,他定得住心,吃得了苦,最終把戰線穩定在慶、延一線。不曾退卻,已是僥幸。
他必須在慶州站住,他身后是萬里江山、天下安危。但他的心卻是一座封閉的孤城,此來身是客,欲歸無留意,抬望眼,看衡陽雁去——站在甘肅慶陽,他的目光追隨雁陣,一直飛到湖南衡陽,那里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第一峰,名為回雁,南飛之雁至此回還。在中古華夏,大雁也飛不出人的世界觀,雁止處便是天盡頭。范仲淹之心從極北飛到極南,劃出他的天下的界限,這就是他不得不守的孤城,端坐城中,便是中原、開封。
范仲淹去過衡陽嗎?他不知道。他只知,范仲淹并沒有去過岳陽,卻應好友滕子京之請寫了一篇《岳陽樓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那天,在老馬家里,他看著墻上那幅地圖——這里便是慶州慶陽,縱馬南下即是長安西安,當年周人便是由此路下了岐山;慶陽東去為延州延安,陜甘寧邊區,所謂甘,就在慶陽;而由慶陽向西,是固原,是六盤山,正是當年西夏南端,成吉思汗北伐西夏,死于此山,而1936年,毛澤東于此山吟出《清平樂》:“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雁仍是范仲淹所望的雁,但望斷了、驀然回首,前邊原來是浩浩蕩蕩的新天新地。
宋人的天下小。宏遠如范文正,他的天下也是小。范仲淹心里的天下,向西向北都不曾越過固原,向南甚至不越衡山。對大宋朝的文人來說,最殘酷的迫害就是把他發往廣東,再狠一點,置之死地,那就是海南島。
老馬取出一本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翻給他看:“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首,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
歐陽修的取笑正點出了《漁家傲》的詞氣窮酸。范文正畢竟文人,他的全部教養都使他做不出“元帥之詞”,他注定沒有一個統帥所應具有的冷酷專注的求勝意志,他在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時忍不住沉吟并且玩味這種沉吟,當他終于在1043年回到開封,榮升宰相時,他一定是如釋重負。
——不,老馬,我知道你最看不起文人酸軟,但你不能這么看范仲淹。這世上多少見花落淚的文人卻不憚于毀滅世界,而鐵血的武士也可能在天地不仁中自有一份慈悲。問題不在這里,我寧可相信,歐陽修的這個“窮”指的不是格調,說的是詞中天下的狹小、胸襟的逼仄——當然,也許我錯了,歐陽修和范仲淹大概共享著同一種天下觀,我要說的是,不管歐或范怎么想,他們的“天下”不過是困守中原,如此之小、如此之“窮”,越來越小,越來越“窮”,直剩下“殘山剩水”,直剩下寥寥酸儒困于天地一角、汲汲于“華夷之辨”!
從慶陽到蘭州,飛于天,下瞰黃土高原。深溝中、巨塬上,所有平坦的地方都被開墾、種植。按老馬的說法,此地是上古農業的發源地之一,考古發掘中,幾乎所有旱地作物的種子都有發現。
拉鐵摩爾是對的。他想,你飛在天上,看著這自古相傳的田地,你就會明白,所謂邊地、邊塞、邊疆,不僅是、甚至主要不是政治和軍事的界限,不僅是分隔、沖突和征戰,這里是生活區域,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相遇和共處的地帶。這里的人們有自己的歷史,有繁盛自足的日子,這種歷史和日子并非僅僅由遠方的某個中心頒布和書寫,在這里,不僅有白發的將軍和思鄉的征夫,這里還有農夫、牧人、商賈、僧侶,他們共同構成了歷史的和生活的主體。
為什么范文正公就看不到呢?
莽莽蒼蒼——他想,范仲淹至少不曾從天上看見這山河大地。他需要的不是一只大雁而是一架飛機,在飛機上他就會知道,這大地上的每個點,落下去便是中心,南與北、中心與邊緣本來是相對而言。
當然,即使駕駛著飛機可能還是想不清楚這個問題。他忽然想起圣埃克絮佩里,這偉大的飛行員,他屬于人類最早一批職業飛翔者,而且還是個文人。
他不記得是在《夜航》還是在《人的大地》里,圣埃克絮佩里眉飛色舞地講了一段八卦,關于法國殖民者如何收服那些桀驁剽悍的北非穆斯林酋長。據圣埃克絮佩里說,辦法很簡單,殖民當局把酋長們帶到法國地中海邊的尼斯觀光旅游,下了船放眼一望,酋長們就懵圈了、呆住了,信念就動搖了:如果這些法國人是邪惡的異教徒,那么,真主為什么把這么美好的地、這么多的水和綠樹賜予他們?
聽上去像是一個毀滅性的問題。
圣埃克絮佩里說,法國真的就此收服了很多酋長。
他對著圣埃克絮佩里笑了。這“小王子”的作者,真是天真可愛。他后來在戰爭中下落不明,假如他還活著,假如他活到現在,他就會明白他是多么輕率,他會看見,尼斯的血在流淌。
至少,你必須確信,每一個地方都自有一顆秘密的心臟。
自宋以后,中國書生就不再具有漢唐胸襟、帝國視野。他們的天下越來越小,而且他們看天下的視角只有一個,就是京城。不管他們身在哪里,他們都是心在京城,都是從京城、從文明的中心地帶遙望著此地。
——一邊說著,一邊心虛著。他現在是在人民大學,一個史學重鎮,在人大高談歷史,這是多么狂妄。好在,他的聽眾是中文系的學生。
他在講《作為方法的邊地》,他希望在“一帶一路”的視野下重新認識我們的歷史和文化。他知道,他正在無恥地越出他的知識范圍。
是的,如馬前潑水,有些錯無法挽回。有時他會想起1980年,他本可以選擇成為歷史系或考古系學生,當然,還有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后來的傳媒大學的招生人員跑到他家里,說你應該去我們的播音系。
播音?那不就是念稿子嗎?
父母大人一臉的輕蔑。好吧,你們以后終于知道你們做了什么決定,你們就這么扼殺了一個白巖松啊。
至于歷史或考古,兩個北大考古系畢業生連想都懶得想,我們家還缺挖墓的了?
于是,他成了中文系的學生。他一直覺得這是一個錯誤。也許,對一個摩羯座來說,真正可做的永遠是尋求確切的知識,而不是研究人們如何發脾氣或者鬧情緒。他常常會為別人的種種脾氣和情緒而暗自羞愧。他想,我們對世界所知如此至少,因為少,我們才相信自己真理在握,才敢于任性,我們只不過是一輩子全力以赴地證明自己是多么好多么可憐或可愛。
然后,在蘭州,他不得不對著很多人談論詩歌。他坐在翟永明和歐陽江河旁邊。他想,他對詩真的沒什么可說,坐在這兩位旁邊就更不能說了。
健談的歐陽救了他,歐陽忽然提到一個詞:“未來考古”。
等等,讓我來!——他想他至少可以談談這個“未來考古”,雖然他根本不知道“未來考古”是個什么鬼,但是,至少這里還有一個“考古”。
現在讓我們想象一下,幾個人來到未來,他們是考古隊員,他們已經身在千年萬年以后,那時我們電腦里流動和儲存的東西已經消失無蹤——別跟我說它們將永世長存,我1994年電腦里的東西都已經找不回來。
所以,對這些未來的考古學家來說,我們和二里頭文化或者良渚文化沒有什么差別,他們要想獲得關于現在的知識,唯一能夠憑依的依然是殘留的、確切的物質。
于是,問題就全在于他們能挖到哪兒了,一個工廠?一座辦公樓?或者挖出此時我們所在的這個金城劇院?
——我們希望如此,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對我們的文明有一個比較體面的認識。但是,千年萬年后的事誰能擔保呢?萬一他們挖到一個廢品收購站或者一個垃圾掩埋場呢?我們會為此感到羞澀和沮喪,而他們,那些考古隊員們一定是欣喜若狂。因為,恰恰在這里,在我們認為我們的生活中最不重要的地方,他們發現了被我們遺忘的秘密,發現了我們從來想不到要留給后人、告訴后人的那些事。
或者說,我們的面目,可能最終是由那些我們認為不重要的事物所塑造的。
他忽然想起斯坦因在《沙埋和闐廢墟記》里記下的一段奇遇,他在尼雅附近一處流沙半掩的古代住宅區的廢墟里掘開了一個垃圾堆——是真正的垃圾堆。實際上,我們常常忘記,除了墓葬,人們的城池或聚落通常都是因戰爭或天災或遷徙而主動放棄的,不管什么原因,人們總是會盡力收拾帶走他們認為珍貴的東西,而把垃圾堆留給后人。
斯坦因的垃圾堆大概屬于公元3世紀西晉武帝時期,他在其中收獲頗豐,“三個漫長的工作日,我聞夠了許多世紀后依然刺鼻的臭氣,也吞進了大量的幸虧如今已經死掉的古代細菌。”但是,他翻出了一批寫在山羊皮和木牘上的佉盧文文書,其中一塊木牘有兩枚封印,一枚是漢文篆字,一枚是希臘神像……
他注意到主持人正在意味深長地看他,哦,跑題了。
好吧,今天的主題是“西部詩歌”。但是這和“未來考古”密切相關。問題在于,我們借以界定自己的那些東西往往出于我們對自己的誤解,或者說,我們的自我想象常常不過是根深蒂固的幻覺。而那些被我們棄置在垃圾堆里的雜物,那是我們最真實的生活經過消化之后的剩余,是我們生活的根基所在。誰知道我們在未來會被如何言說?比如范仲淹曾身在甘肅,他帶兵打仗,在這里待了一年,但是,一年之久,他看到的是刀兵和生死,他完全沒有看到這里人們的家常日用。如果你回到大宋,你見到范仲淹,你問他何處是絲綢之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腳下這條路原來也是另外一條路。
所以,何處是“西部”?西部是不是從洛陽或者開封或者北京指認出來的西部?從外面對這個廣大的區域作出文化、歷史和地理的復雜界定——但再復雜也注定是簡單的。比如,史學界有人劃了一條漠河-騰沖線,這條線以東是農耕文明占壓倒性優勢的地區,包括朝鮮、日本和越南,這條線以西是農耕文明和游牧、草原文明相互沖突和影響的地區。對不對姑且不論,但這也提醒我們,當我們把西部定義為傳統中原文化的保留地和后花園時,這里是否存在知識上的盲區?更不用說把西部和原始、蠻荒簡單地聯系在一起。這些究竟是外部指認的結果還是我們身在此地的自我發現,還是我們身在此地,但不自覺地反復進行著自我的外部化?
好吧。不說了。
他站在國博展廳,看那些畫。他喜歡那艘船,紅頭船,那是清代乾嘉年間的潮汕海船,專為遠航暹羅而造。船艏和桅桿漆成紅色,繪著大魚之眼。那就是一頭巨大的紅魚。
南海有魚。大魚去處,天下隨之伸展。
那一年,范仲淹在慶州,行至一條河邊,這個蘇州人看到了碧水清流,心甚樂之,但是,陪同的當地官員對領導說:“此水不好,里面有蟲!”
范仲淹答曰:“不妨,我亦食此蟲也。”
所謂“蟲”,原來是魚。范仲淹當然吃魚,但慶州人不知有魚,亦不吃魚。直到五六十年代,陜甘人也不大吃魚。他記起一位老先生曾經笑談,當年第一次自陜來京,面對松鶴樓的松鼠魚,心中驚詫惶恐,竟不知如何下手。他想,這不食魚的習俗恐怕來源深遠,當年慶州、延州“羌管悠悠”,藏羌之風浩蕩,而藏族人本不吃魚。
現在,他站在這里,看著這條船。船上都是些什么人呢?船主,他們通常屬于一個世代以航海貿易為業的家族;船員,他們很可能都是潮汕同鄉。風濤險惡,同族和同鄉將相依為命。他們的船上是否有一個文人?范進不曾中舉而上船做了賬房?他是否會記下船上那些事?他是否知道,那些事比朝廷里帝王將相經略天下的偉業重要得多?
當然,沒有。范進寧死也不會上船。夏蟲不可語冰,他不知道南方海中有大魚。
1936年,國破家亡之際,雷海宗先生發表《斷代問題與中國文化的兩周》,在他看來,“元明兩代是一個失敗與結束的時代。”然后他寫道:
在這種普遍的黑暗中,只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漢族閩粵系的向外發展,證明四千年來唯一雄立東亞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絕境。內在的潛力與生氣仍能打開新的出路。鄭和的七次出使,只是一種助力,并不是決定閩粵人南洋發展的主要原動力。鄭和以前已有人向南洋活動,鄭和以后,冒險殖民的人更加增多,千百男女老幼的大批出發并非例外的事。有的到南洋經商開礦,立下后日華僑的經濟基礎,又有的是冒險家,攻占領土,自立為王。后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華僑與中國酋長。漢人本為大陸民族,至此才開始轉換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說是尤其寶貴難得的水陸兩棲民族。(《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14,第142-143頁)
——膝蓋劇痛。他想,這就是每天一萬步的結果。他的腿本不是用來走路的。他的腿本是依著馬背和馬腹的弧度生長。他的前世,那個匈奴人或鮮卑人,立馬陰山,他看著大地向南展開,如風如電,直到地之盡頭,海之北緣,然后,他下馬,撲向浩無際涯的藍水。
這個夏天,游于南洋。
責任編輯 季亞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