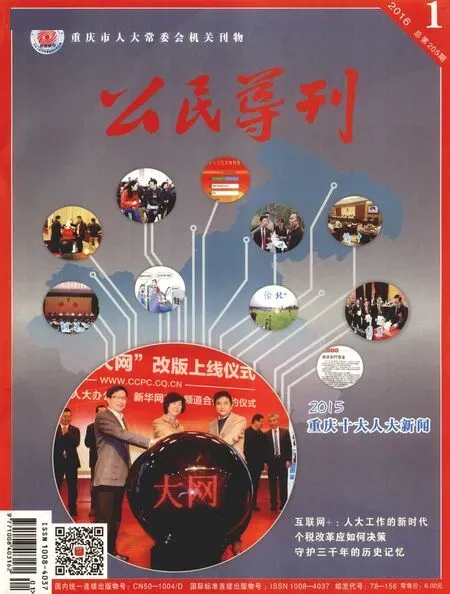沙坪學燈
楊耀健
提起沙坪壩,便覺得一陣書香撲鼻而來。
翻檢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它早已榜上有名。
文化一直是沙坪壩區(qū)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熱詞。
重慶作為戰(zhàn)時的首都。抗戰(zhàn)時期,隨著全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的轉(zhuǎn)移,諸多領域的大師級人物,以及名揚中外的泰斗級人物都云集沙坪壩區(qū),沙坪壩成為著名的文化區(qū),盛極一時,蜚聲中外。
1938年。重慶沙磁文化區(qū)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個創(chuàng)舉,是中華民族現(xiàn)代精英文化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中大眾文化的結(jié)合,優(yōu)秀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的結(jié)合,充分體現(xiàn)了愛國民主、科學、進步的繼承和發(fā)展。
傳火傳薪要有能人
沙磁文化區(qū)的基石和脊梁是重慶大學。1933年10月,重慶大學從菜園壩臨時遷址到沙坪壩,進入校園映入眼簾的是中西合璧的理學院大樓,古色古香的圖書館。大操場那邊,文學院和農(nóng)學院大樓拔地而起。籌備委員溫少鶴多年后回憶說,那天他盯著理學院大樓,好似崇拜圣跡那般。
重慶大學首任校長由劉湘兼任,他忙于軍政,委托副校長甘典夔主持校務。甘典夔振興過川東師范學校,頗有辦學經(jīng)驗。有人對他說,辦公立學校則功成身退,助私立學校則不為已謀,可謂“竹籃打水一場空”,殊不足取。甘典夔一笑置之,事后對家人說:“我之關注教育事業(yè),旨在培養(yǎng)人材,獲得機會即當奮力而為,或奠基,或扶助,自盡其心,但能具有成效,于愿已足矣。”
重大初創(chuàng),文理科并存。文學院長李公度與學生見面,掏出一張紙條念與學生聽,這是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后,光緒皇帝痛定思痛后所擬圣旨,至今仍覺振聾發(fā)聵。他希望學生時時自警,發(fā)奮讀書,富國強兵。
理學院院長何魯,留法歸國,曾就職于多所高校,被譽為數(shù)學泰斗。他在講授幾何學時,著重于幾何的證題法和軌跡、作圖的分析法,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使學生如飲甘霖,一點不感到枯燥。
沙坪壩的第二所高校是四川鄉(xiāng)村建設學院,1933年創(chuàng)辦。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舊中國,溫飽尚且難以解決,這里就要搞鄉(xiāng)村建設,其理念大大超前。
面對種種質(zhì)疑和冷嘲熱諷,院長高顯鑒我行我素,以社會為教育場所,以生活為教育中心,有序開展掃盲、衛(wèi)生、民眾講演、農(nóng)事推廣及社會調(diào)查。斯時,每晚到磁器口地藏寺學院本部聽課的民眾,多達1400人,比城里的晚會還嘈雜。
沙坪壩的第三所名校是南開中學,開辦經(jīng)費由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募集而來,抗戰(zhàn)前夕開學。
校長喻傳鑒是留美學生,從天津到重慶辦校。他對教師要求嚴格,不稱職者就算至親好友也要解聘。對學生,則要求獨立思考。他認定,所有的唯唯諾諾,所有的孤陋寡聞,所有的夜郎自大,在南開都不能生存。
中央大學遷址重慶
抗戰(zhàn)爆發(fā),外地遷到重慶的高等及專科院校共25所,其中遷到沙坪壩的就有16所。沙磁區(qū)的學校,無論從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無疑都走在全國前列,成為引導學界的大纛。其中,中央大學聲譽卓著。
1937年8月,中央大學從南京遷渝,連教學實驗用的動物也一并帶來,可謂“雞犬不留”。中大校長羅家倫有個觀點,在過去的漫長歲月中被忽略了的事,如今被提到了國家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劃上,民族要復興,教育尤其應加強。
中大遷渝后,本埠各界大力支援,重慶大學慨然以該校松林坡校區(qū)借與中大營建新校舍。到l0月中旬,中大師生及圖書設備陸續(xù)抵達重慶,新校舍尚未修好,師生暫借兩路口川東師范駐足。
羅家倫熱心教育,1938年夏在重慶各大報刊登中央大學招生廣告,既招收各院系新生,也招收轉(zhuǎn)學插班生。華北及江浙不少中斷學業(yè)的大學二三年級學生,因而有機會轉(zhuǎn)入中大,在重慶完成大學學業(yè)。
羅家倫說:“我們現(xiàn)在不要談什么奪取民眾。我們要奪取時間,奪取知識,奪取技能,奪取訓練。我希望在沙坪壩訓練的這支軍隊,能成為民族復興的軍隊。”
遷址的中大由在南京時的l500多學生規(guī)模,發(fā)展成具有7院37系、3500多名學生,成為國內(nèi)系科比較完備、國際公認學術(shù)水平較高的大學。
莘莘學子云集重慶
充裕著文化氣氛的重慶召喚著全國的學子。
淪陷區(qū)的學生來了,西北后方的學生來了,云南、貴州的學生來了,四川偏僻山鄉(xiāng)的學生來了……
中大、重大、湘雅的校園,固然沒有未名湖的波光塔影,臨湖軒的古樸素雅,燕南園的曲徑通幽,卻被心有靈犀的抗戰(zhàn)學子公認為“風景這邊獨好”。須知,八年中,一大批抗戰(zhàn)學子正是在這里被陶冶出來的。
的確,在莘莘學子心目中,沙坪壩不僅僅是一座可供深造的綠島,還是一朵可燃心志的紅云。
入夜,各校圖書室、宿舍的燈光交相輝映,難怪當年重慶報刊征求“陪都八景”,“沙坪學燈”理所當然入選。
沙坪壩的白天更熱鬧,不乏大師大儒,著長衫的是徐悲鴻、拄杖徐行的是馬寅初、慷慨陳詞的是粱漱溟、誨人不倦的是陶行知。翦伯贊、鄧初民、侯外廬、胡風任過客座教授,郭沫若、焦菊隱、陳白塵講過課,張伯苓、朱家驊、葉元龍奔走教育,更有周恩來、鄧穎超常到校園走動,帶去鼓勵與囑托。
戰(zhàn)火中的學子,交出了圓滿的答卷。
1941屆中大醫(yī)學系學生張伯毅,后來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航空系學生馮元禎、土木系學生易家訓,后來都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1942屆地理系畢業(yè)的陳正祥,后來成為聯(lián)合國世界農(nóng)業(yè)地理委員會主席……這樣的學生還多,難以枚舉。
這是偶然的嗎?不!這是全民愛國的本能驅(q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