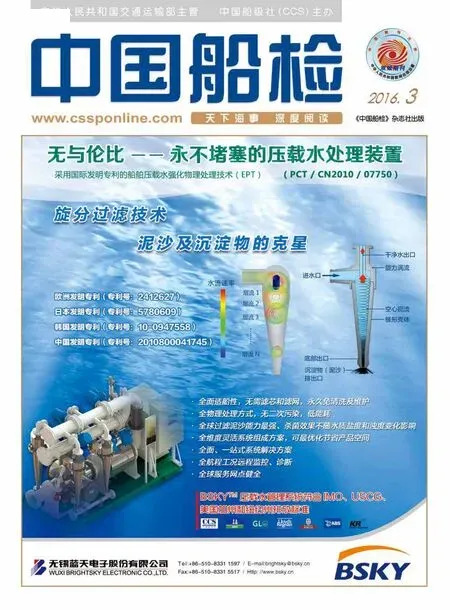馬士基3E大船是怎樣被打入冷宮的
上海海事大學

2015年11月,馬士基航運宣布停航一艘18270標箱的3E級新船,不久之后又宣布暫時放棄6艘19630標箱型(3E二代)船的訂單。這些行動標志著自2011年馬士基訂造3E級船所開啟的新一輪集裝箱船大型化趨勢遭遇了重大障礙。預計2016年18000標箱型以上集裝箱船數量增幅,將從2014年的276.7%下降至38.2%。不僅如此,而且在今后幾年內,或許不會再有18000標箱以上船的新訂單。那么,馬士基3E大船究竟是怎么被打入冷宮的?
平均單位艙位造價比同類船高出兩成
馬士基和其他承運商開始從市場上撤回他們最大和最昂貴船舶的行動表明當前形勢的嚴峻程度,全球經濟增長疲軟,船舶運力大量過剩,以及運價再創歷史新低。
Alphaliner在其評述中說:“在通常情況下,承運商總是努力讓他們最大的船保持營運狀態,但是當所有貿易航線上幾乎都處在運力過剩狀態的時候,他們除了封存最昂貴的資產外,已經別無選擇。”馬士基做出封存3E大船這一痛苦抉擇的原因,應該有跡可循。
在2011年初訂造3E級船的新聞發布會上,馬士基航運前任首席執行官柯林稱,用3E級船運輸集裝箱的成本要比現役的和在訂造中的1.3萬~1.6萬標箱船低26%左右。3E級船的燃油消耗水平比當時行業平均水平低50%左右,比馬士基在役的15550標箱的E級船低20%左右,從而使這些新船成為有史以來最環保的船舶。因此,3E級船是當時世界上一種成本效益最高、能源最節省和對環境最友好的集裝箱船系列。
馬士基的首批10艘18270標箱的3E級船是在2011年2月訂造的,每艘造價1.9億美元,第二批10艘同類型船每艘1.85億美元。加權平均每箱位造價為10263美元。
兩年以后,中海集運率先響應,于2013年4月訂造5艘容量為18400標箱船,每艘造價1.366億美元。平均每箱位造價為7424美元。3E級船的平均每箱位造價比中海集運高38.2%。即使按照馬士基的發言人所說的“幕后價格”每艘1.6億美元計算,平均每箱位造價為8758美元,也比中海高18%。
克拉克森集裝箱船新船造價指數研究報告指出,從馬士基2011年2月簽署3E級船訂造合約至2013年4月中海集運發布訂造公告,克拉克森集裝箱船新船造價指數下降22%之多。
3E級船的引進為馬士基注入巨大的短期容量優勢。從長期來看,其他運營商在訂造新的18000標箱時成本基礎更低。其后不可避免的是,給那些運營商在實現每標箱更低的成本方面以優勢。這就是中海集運及后續跟進的船公司在單位造價方面的“后發優勢”。在2015年,中海集運大船投入營運,這兩套船舶在亞歐航線上相遇。中海大船的平均單位箱位造價優勢遙遙領先于馬士基3E級船。此外,市場上越來越低的期租船費率進一步打壓了3E級船的生存空間。或許,這是馬士基決定停航一艘3E級船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長期來看,1.8萬標箱船由于其在單位箱位成本方面的優勢而必將成為未來亞歐航線的主流船型。而3E級船在單位艙位造價方面的劣勢將使馬士基相對于其他承運人的競爭優勢有所降低。其他競爭者的這種后發優勢可能會一直維持到下一代容量更大的船舶被訂造的時候。
馬士基的3E級新船尚未出廠,身價已貶值兩成。其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為市場波動、船廠饑渴、造價陡降等客觀因素造成的船舶精神磨損,但是主觀因素不可回避,即沒有能夠把握好最佳造船時機。
艙位利用率走低是兌現規模經濟效益的障礙
馬士基宣稱,3E級船的單位艙位成本比14000標箱船的成本低500美元,每標箱功率需求大幅降低40%,節約效果明顯。
然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巨型船舶的影響》(The Impact of Mega Ships)報告對馬士基超大型集裝箱船的影響提出了質疑。報告認為,只有7%的節省源于規模經濟的結果。其他的節省都是降低航速和提高發動機效率的結果。
自2000年以來,集裝箱船隊運力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全球運力大約每七年增加一倍。結果是在2015年全球集裝箱船隊運力達到2000萬標箱,是2000年全球總運力的四倍。盡管運力過剩在運輸業不是新現象,但是以這樣的頻率發生則反映了行業的結構特征。2011年馬士基首次訂造3E級新一代集裝箱船之后,大多數航運公司都意識到必須趕上大型船舶的競賽。羊群效應使得集裝箱船運力過剩更加嚴重。船舶規模的不斷增大更進一步加劇了運力過剩。

圖1 船舶大型化趨勢與世界貿易海運量增長的不相關性(1996~2015)
過去幾十年里,世界級集裝箱船隊運力的發展與全球貿易發展和實際需求逐漸脫節。在1996到2007年期間,世界海運貿易的增長與集裝箱船的平均容量平行發展,但是之后出現了背離,主要是因為集裝箱載貨能力依舊以過去同樣的路徑增長,沒有能夠按照2007到2010年的海運貿易的疲軟發展進行調整(圖1)。根據麥肯錫在2015年的計算,運力供給與運力需求之間大約有20%的差距,而且這一差距至少將持續到2019年。運力過剩的后果是運價走低,侵蝕班輪運輸行業的利潤。
利用規模經濟的一個前提是船舶利用率不降低。否則,船越大,艙位成本就越高。根據格里姆斯塔和諾伊曼拉森《巨型集裝箱船的規模經濟效益能夠量化計算嗎?》一文的觀點,相對于一艘滿載的14000標箱船,一艘18000標箱船要實現成本節約,其艙位利用率至少要達到91%。
然而,實踐證明,艙位利用率不可能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由于大型船只的大規模訂造造成了運力過剩,因此,全球船隊的總體利用率必然下降,由此就可能沒有任何成本優勢可言。當前,由于運力過剩導致運價低迷和艙位利用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馬士基對大船的停航和撤單就不足為奇了。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特別是歐洲經濟還沒有走出困境,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降,因而亞歐航線市場缺乏充足的貨源,班輪公司要達到這樣高的艙位利用率有一定困難。這時,3E級船的規模經濟優勢就會轉化為劣勢,首當其沖被打入冷宮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馬士基首席執行官施索仁承認,不排除今后停航更多3E級船的可能性。
集裝箱船大型化的成本優勢走向疲弱
大型船舶在海上實現了規模經濟效益,但在陸地創造了更高的單位成本。碼頭不經濟的影響體現在碼頭營運商盈利能力的下降,這將最終導致承運人的碼頭成本增加。
研究大型集裝箱船成本優勢的一個關鍵要素是船的大小和處理成本之間的關系。所謂處理成本,是指在運輸鏈中處理這些大型集裝箱船舶的其他相關費用。隨著船舶變大,每標箱的船舶成本減少,而處理成本增加。這兩條曲線的加總即為總運輸成本。問題是我們目前正位于曲線中的什么位置,如果集裝箱船變大,它們會在曲線中怎樣移動。
相比于第一代15000標箱規模的船舶,19000標箱規模的現代船舶能提供顯著的成本節約。但是,其中至少55%~60%的節約額來自于慢速航行的優化。
幾十年前與船舶大型化相關的成本節約是相當可觀的,但是隨著船舶規模越來越大,成本節約的幅度也在降低。有關研究顯示,在船舶大型化的早期,在船舶規模升級到5000標箱以前,單位成本的節約主要是通過船舶容量的增大來實現,大致每單位標箱成本節約額的一半以上來自于船舶大型化。但是超過5000標箱容量之后,成本節約的規模就會變得越來越少。分析證實,成本節約額降低的趨勢與新一代集裝箱船舶的引進同步。據估計,在假設航速一定的情況下,從15000標箱規模的船舶到現在最新的19000標箱船的單位成本節約額,同先前由5000標箱船到15000標箱船的單位成本節約額相比,只有后者的1/6~1/4。顯而易見,自從新一代巨型船舶問世以來,成本節約的幅度隨著船舶規模的增大而降低。顯然,集裝箱船大型化的成本優勢正逐漸走向疲弱。

圖2 船舶成本與運輸成本的關系
大船在燃油成本方面的優勢也受到銷蝕。本世紀初,由于油價飆升,燃油成本占班輪公司經營成本的比重從20%~30%直線上升到60%以上。至2011年雖有所回落,但仍在40%至60%之間。在過去十年中,班輪公司應對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的主要措施是慢速航行和船舶大型化。這兩項策略已經讓他們大大降低平均每個集裝箱每海里消耗的燃油量。
然而,自2014年以來,國際油價經歷了“大跳水”。紐約油價和布倫特油價2014年6月時一度沖高至每桶107.26美元和115.06美元,此后逐步走低。12月26日兩者的收盤價分別為每桶54.73美元和59.45美元,幾近“腰斬”。2015年在震蕩中不斷走低,至2016年初在每桶35美元上下波動。油價跌雖然會降低船舶成本,但馬士基的成本優勢也被削弱了。
過去幾年,馬士基就改進燃油效率一直在進行技術和資金投入,以往燃油在成本占比大時,3E級船的慢速航行和節能措施的強大優勢特別明顯。但現在燃油成本在經營成本中的占比越來越低,提高燃油效率的收益無法補償前期研發和設備方面的投入,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3E級船在能源效率方面的優勢就被銷蝕殆盡。
大船對保險能力的挑戰
據業內專家辛吉誠分析,隨著集裝箱船主尺度的增加,船舶結構強度、船體剛性、應力集中和韌性疲勞等問題更加突出,這大大增加了船體結構失效的風險。與此同時,超大型集裝箱船由于體型過于笨重,操縱難度較大,在航行中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也較高。從現有的統計資料看,超大型集裝箱船發生碰撞事故的概率比中小型船舶要高出40%左右。加之超大型集裝箱船的配載貨物數量龐大,一旦發生海損,后果相當嚴重。
2013年,商船三井旗下容量為8000標箱的“MOL Comfort”輪在印度洋斷裂,由此引發的巨額海損理賠問題,使國際海事保險業開始重新審視船舶大型化導致的額外風險。
主要由于以下兩個原因,大型船舶增加了事故潛在損失的風險。一方面,由于缺乏移除大型船舶殘骸的救援設備和技術能力,對于現存的最大集裝箱船事故殘骸救援的成本會增加。當事故發生地距離岸基設施較遠時,目前在世界上很少有適合的船廠來拖拽和修理這類大船。對于保險公司來說,這些情況下的費用不能精確的定義。
另一方面,對于貨主來說,他們的貨物所蒙受的風險隨著船舶容量的增大而呈線性關系同步增大。可以預計,一艘20000標箱船的沉沒所造成的貨物價值損失將是10000標箱的船舶沉沒所造成損失的兩倍。用一艘大型船只運輸貨物,比拆分為一些更小的船承擔的風險更大。此外,涉及更大型船舶的供應鏈風險正在上升。對于大型船舶的可保險性和一旦發生事故后潛在的共同海損成本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據德國學者Allianz《2015年安全與航運回顧》(Safety and Shipping Review 2015)一文的假設,一艘19000標箱集裝箱傾覆并沉沒,可能造成的損失會高達10億美元。另一種發生機會很低的情景是一艘超大型船與一艘稍小的船相撞,如果施救打撈的位置很困難,總成本可能會超過20億美元。假設所有都可能做到的話,估計要花兩年多時間來打撈事故中沉沒的19000標箱船上的所有集裝箱。
保險公司在簽訂巨型船舶保險合同時正在變得更加謹慎小心。為了避免事故的風險,國際造船規則正在變得更加嚴格。由于這類事件目前為止沒有發生過,因此很難估計它們對于保險市場的影響。而且,由于目前船舶保險市場不太景氣,所以,即使可以假定存在這些風險,但是它們通常并不包括在風險保費的條款中。

國際救援能力和保險能力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必然導致3E級船保險費率的大幅上漲,從而使船舶的營運成本大幅增加。這也會成為作出3E級船停航決策時的一個考慮因素。
港口基礎設施和營運設施尚未準備就緒
OECD的《巨型船舶的影響》報告認為:“班輪公司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建造超大型集裝箱船,因此要求班輪公司投資港口擴建并非不合理的建議。港航業在當前的貿易環境下需要做出改變,采取某種措施是必要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應該加強合作,這種合作也應包括風險共擔。”
OECD的報告認為,集裝箱承運商要求公共部門來補貼航運業的船舶大型化計劃是不合理的。即使公共部門補貼公用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效益也應該惠及消費者。該報告指出:“大型船舶的主要受益者是集裝箱航運公司,但大船助推了船舶運力過剩,從而降低了航運公司的運價和利潤率。用這種間接的方式,大型船舶有助于降低海上運輸成本,從而使托運人和消費者受益。”
班輪公司由于推行船舶大型化獲取規模經濟而受益良多,然而同時卻給港口當局和碼頭運營商帶來種種問題。他們不得不調整航道、港池、碼頭岸壁和門式起重機,這些在成本方面增加的幅度比班輪公司受益的幅度更大。
承運商巨頭利用大船在同樣的時間在一個港口同時吞吐數千個集裝箱時,創造出港口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大高峰時段,致使托運人遭受船舶延誤和嚴重的港口堵塞。
由此產生的費用由港口運營商和港口管理當局承擔,即大部分由公眾來承擔。然而,港口運營商、港口管理當局以及公眾并沒有因為大船而得到額外的收益,因為運輸集裝箱的總量不受運輸船舶大小的影響。有時甚至是相反的情況:一些港口當局為了抓住超大型集裝箱船,甚至為它們提供折扣港口費率。
最近馬士基對大船的停航和撤單表明,班輪公司也未能從這一輪船舶大型化獲益。真正享受大船“紅利”的是三家韓國造船廠、比利時和荷蘭的幾家疏浚企業和一家占主導地位的中國起重機制造商——振華港機。顯然,船舶大型化帶來的是全球港口、碼頭營運商和班輪公司三方俱損的結果。即使那些并未真正享受到低運價的托運商,也遭受到班輪公司航班延誤和港口擁堵等種種負面影響。這是一個悲劇。
有些地方的公共政策刺激大型船舶的發展,但這似乎對公眾并沒有很多好處。這實質上是對大型船舶的一種公共補貼。
一艘滿載的3E級船要求港口的進港航道和泊位前沿的水深達到16米。在北歐主要港口中,容許3E級船全天候滿載進出港的只有鹿特丹港和威廉港。
船舶容量增大而將船長維持在400米,意味著碼頭起重機的配置密度無法增加,船時效率也就難以提高。如果碼頭生產率水平沒有提高,那么,即使基礎設施能夠接納更大的船舶,大船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不會變成班輪公司的真金白銀。
新一代大型船舶從決定訂造到新船交付的時間間隔,同基礎設施為適應大船而制定工程決策到實際建成的時間間隔,兩者之間有巨大的落差。此外,陸上的各種設施和建筑物投資昂貴而且不可轉移,而船是可以靈活部署的流動資產。
問題是,為什么公共實體應該承擔創造超額的碼頭處理能力來適應大型船舶高峰時段陡增的運量和船舶共享協議造成混亂的成本?
不但基礎設施,而且營運設施的建設也有一個滯后期的問題。例如,3E級船寬59米,露天甲板上可并排放置23列集裝箱。然而,據報道,目前全球只有深圳鹽田、丹戎佩拉帕斯、阿爾赫西拉斯、鹿特丹和威廉港五個港口能夠允許3E級船滿載進出。這就是說,在世界大部分港口,18270標箱的3E級船只能裝載15000~16000標箱,艙位利用率只能達到82%~87.5%。
港口基礎設施和營運設施建設的滯后,打壓了3E級船的艙位利用率,限制了規模經濟效益的兌現,大船的優勢就轉變為劣勢,“下架”也就成為意料中事。船舶封存雖然也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但也許是一種額外成本最小化的選擇。
船舶大型化進程遭遇公共部門的“狙擊”
2014年,亞洲的港口擁堵已達到20多年來最糟糕的水平。而在美國,2014至2015年間出現了嚴重的港口擁堵問題。盡管各個港口的擁堵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它們共同存在的一個相同的原因是巨型輪船在各個港口必須裝卸的箱量陡然增加。隨著相同時間內進入堆場的集裝箱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港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它們必須確保這些大船在港停留時間仍然和以往一樣,盡管不得不努力在每一小時內處理大幅度增加的集裝箱量。
從營運設備方面來說,提高泊位的船時效率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同時也要考慮其中的商業因素。對港口和碼頭營運商來說,這不僅意味著必須配置“高大上”的船岸起重機,而且必須確保具備充足的勞動力,而這樣的專業化勞動力是需要付出高成本的。那么,問題就再次歸結為班輪公司是否愿意為這些額外的費用買單。
船舶規模不斷增加,船寬和吃水每額外增加一米,港口為此所做的必要準備也在增加,不僅是起初需要疏浚,還包括后期要繼續維護航道的水深不變。
這使得主要來自公共財政的用于港口基礎設施開發的投資和總體經濟回報越來越不成比例。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實體結構,包括造船基礎、航道工程和港口建設。所以,船舶大型化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只是使得班輪公司享受到單位艙位成本降低的優勢,而船舶規模的不斷增大卻導致基礎設施和營運設備的成本日益增加。
公共資源的投入只是為了讓那些有能力投資大型船舶的班輪公司相比于他們的競爭者擁有成本優勢。因此可以說,這些競爭成本大部分是由公共部門負擔的,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由公共財政贊助的有利于大航運公司的扭曲了的競爭。然而,由公共財政來補助航運公司巨頭升級船型缺乏合理性。
這就是為什么仍有新船訂單的原因。雖然從航運公司的角度來看,考慮到運力供給已嚴重過剩,這些訂單已沒有意義。
然而,航運聯盟的影響力對碼頭公司會產生不利影響,比如2M聯盟將占有亞-歐航線超過30%的市場份額,這將使航運公司在與碼頭進行合同談判時處于非常強勢的地位。要讓班輪公司為港口追加投資買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盡管有業內專家認為,不斷增加船舶容量可能有違經濟規律,船舶大型化趨勢也因種種原因而暫時受挫,但是,目前沒有跡象表明這一趨勢已達終點。可以預言,一旦氣候回暖,承運商和造船廠向23000標箱至30000標箱的馬六甲極限型船“沖刺”的進程將會重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