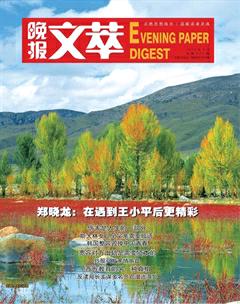西方教育的另一種真相
盛斯才
我國的中小學教育一直面臨課業(yè)負擔太重、學生壓力太大、學習有效性差等指責,一些到過歐美發(fā)達國家的人,通常都會感慨其教育的寬松——隔三岔五的假期、三點鐘就下課的學校、近乎于游戲的課堂以及老師們體貼耐心的鼓勵……這些信息的散布和傳播,讓人情不自禁地覺得,在歐美讀書太輕松、太容易、太簡單了。
然而,久居美國、深入觀察美國教育的研究者,卻得出了幾乎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發(fā)現(xiàn):美國小學確是下午3點放學,但幾乎只有黑人的孩子直接回家了,而大多數(shù)白人和華人的孩子,都背著書包、拿著樂器,去了各種輔導班。在美國,一個不去輔導班補課、不花大價錢去學習才藝、不參加社會活動去豐富自己履歷的孩子,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名牌大學。
在西方社會,孩子們的確可以有一個開心、幸福的中小學,但“更少的學習、更多的游戲、更寬松的管理”,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想要躋身社會精英階層,你需要更好的自律、更多的課外輔導與公立教育之外更多的社會資源。西方教育實際上通過一個寬松的過程,偷偷地完成了社會分層。歐美的中小學生確實可以不承受任何壓力,但在快樂幾年之后,大多數(shù)的孩子或者去社區(qū)大學再混幾年,或者直接去找些底層的體力工作度日,或者直接開始拿失業(yè)補助,在街上閑逛。著名作家龍應臺曾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一個叫提摩的孩子,從小愛畫畫,在氣氛自由、不講究競爭的德國教育系統(tǒng)里,他一會兒學做外語翻譯,一會兒學做鎖匠,一會兒學做木工。畢業(yè)后找不到工作,18歲就失業(yè)了,到41歲仍舊失業(yè)。因為沒有工作,所以也沒有結婚,和母親住在一起。可是,他的母親已經(jīng)快80歲了。
西方真正的一流大學是什么樣子呢?央視《世界著名大學》制片人謝娟曾帶攝制組到哈佛采訪。到哈佛大學時,是半夜2時,可讓他們驚訝的是,整個校園燈火通明,餐廳里,圖書館里,教室里,還有很多學生在看書。
在真正的名校,學生的壓力是很大的。在哈佛,見到最多的就是學生一邊啃著面包一邊忘我地在看書。一個北大女孩說,她在哈佛一個星期的閱讀量相當于她在北大一年的閱讀量。即使這樣,哈佛平均每年有大約20%的學生會因為考試不及格或者修不滿學分而休學或退學,而且淘汰的20%的學生的考評并不是期末才完成,而是每堂課都要記錄發(fā)言成績,平均占到總成績的50%,這就要求學生均勻用力、不能放松。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說:“中國大學生的生活相比之下太輕松了。我們總是說,中國的孩子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實,在美國一些著名的中學里,高中的學習同樣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學的時候,也經(jīng)常學到半夜。在美國,隨著年齡的增長,一點點加大學習的任務。到了大學時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須是吃苦的。而中國的孩子到了大學,卻一下子放松下來了。他們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國大學生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所以,美國的高層級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
由此可見,以“減負”為訴求的教改可能是一個過于膚淺的結論。一些人常拿英美公立學校來做素質(zhì)教育的模板,強調(diào)快樂學習,強調(diào)減負,結果只能造成公立教育在內(nèi)容上的縮水,質(zhì)量上的下降。這實際上只會逼迫家長們在課外時間投入更多的資源,而無力購買教育資源的孩子則越來越難以通過自己的勤奮在課堂上彌補這種資本上的差距。國外一些嬉鬧散漫的所謂現(xiàn)代公立教育,其實不過是政府提供的最低標準公共產(chǎn)品。我們不能把這些標準當作中國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把這樣的表象當作西方教育的真相。
(司機摘自《雜文月刊·原創(chuàng)版》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