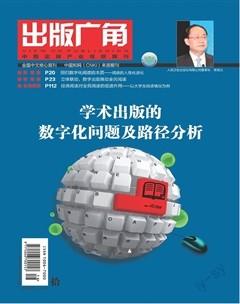試析教材策劃編輯服務(wù)醫(yī)學(xué)教育的途徑
【摘要】因醫(yī)學(xué)模式的轉(zhuǎn)變、公眾健康需求的日益增加等原因,醫(yī)學(xué)教育在不斷地變革。作為新時(shí)代的醫(yī)學(xué)教材策劃編輯,在不斷提升個(gè)人職業(yè)素養(yǎng)與業(yè)務(wù)能力的同時(shí),還要加強(qiáng)服務(wù)醫(yī)學(xué)教育的理念,挖掘深層次需求,切實(shí)為作者、讀者、院校、行業(yè)提供優(yōu)質(zhì)的醫(yī)學(xué)教育服務(wù)。
【關(guān)鍵詞】教材策劃編輯;醫(yī)學(xué)教育;服務(wù);途徑
【作者單位】成麗麗,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有產(chǎn)品就有服務(wù),服務(wù)是產(chǎn)品的延伸,當(dāng)然,服務(wù)自身也是一種無(wú)形的產(chǎn)品。出版兼具文化功能與商業(yè)功能,比一般物質(zhì)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具有更多層次、更復(fù)雜內(nèi)容,同時(shí),出版業(yè)的市場(chǎng)化和日趨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對(duì)策劃編輯工作的要求越來(lái)越高。因此,在工作實(shí)踐中,編輯除了要注重編輯業(yè)務(wù)、編輯技藝創(chuàng)新,還要注重提升服務(wù)理念,提高服務(wù)品質(zhì),充分發(fā)揮出版的社會(huì)功能。
醫(yī)學(xué)是一門(mén)實(shí)踐性很強(qiáng)的應(yīng)用性科學(xué)專(zhuān)業(yè)。因醫(yī)學(xué)模式的轉(zhuǎn)變、公眾健康需求的日益增加等原因,醫(yī)學(xué)教育在不斷地變革。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既是職業(yè)教育的一部分,又是醫(yī)學(xué)教育的組成部分,是發(fā)展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重要基礎(chǔ)。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作為醫(yī)學(xué)行業(yè)出版社,主動(dòng)服務(wù)于政府主導(dǎo)、行業(yè)指導(dǎo)、企業(yè)參與的職業(yè)教育辦學(xué)機(jī)制,依托行業(yè)組織,在推動(dòng)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改革發(fā)展方面做了大量開(kāi)創(chuàng)性的工作。筆者根據(jù)多年出版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材的工作經(jīng)驗(yàn),將服務(wù)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途徑概括為緊跟政策導(dǎo)向、深入契合需求兩個(gè)方面。
一、緊跟政策導(dǎo)向
2014年6月23—24日,國(guó)務(wù)院召開(kāi)了全國(guó)職業(yè)教育工作會(huì)議。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的《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chēng)《決定》)及教育部等六部門(mén)印發(fā)的《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體系建設(shè)規(guī)劃(2014—2020年)》,全面提出了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指導(dǎo)思想、基本原則、目標(biāo)任務(wù)和重大舉措,理念先進(jìn)、主題突出、責(zé)任明確,對(duì)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做了頂層設(shè)計(jì)。政策是方向標(biāo),新的政策給新一輪的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所以,做好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服務(wù)首先要有敏銳的政策嗅覺(jué),其次要能夠深入解析各項(xiàng)政策并用于指導(dǎo)實(shí)際工作。當(dāng)前職業(yè)教育還不能完全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需要,結(jié)構(gòu)不盡合理,質(zhì)量有待提高,辦學(xué)條件薄弱,這是目前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現(xiàn)狀。在“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背景下,我們要將選題策劃、編輯出版、市場(chǎng)推廣、教育服務(wù)等功能集于一體,為衛(wèi)生職業(yè)院校提供優(yōu)質(zhì)教材和全程教學(xué)科研服務(wù)。
二、深入契合需求
1.教材建設(shè)方向與教學(xué)改革相契合
深化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改革,需要始終堅(jiān)持實(shí)踐“以服務(wù)為宗旨、以就業(yè)為導(dǎo)向、以崗位需求為標(biāo)準(zhǔn)”的職業(yè)教育辦學(xué)新理念。現(xiàn)代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正在進(jìn)一步把以教師為主體的傳統(tǒng)觀(guān)念轉(zhuǎn)變到以學(xué)生為主體的現(xiàn)代教育觀(guān)念上來(lái);把重理論、輕實(shí)踐轉(zhuǎn)變?yōu)槔碚撆c實(shí)踐并重;把以知識(shí)傳授為主線(xiàn)轉(zhuǎn)變?yōu)橐阅芰ε囵B(yǎng)為主線(xiàn)。教材是教學(xué)內(nèi)容的載體,是為教學(xué)目標(biāo)服務(wù)的。教材建設(shè)是專(zhuān)業(yè)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保障,深化專(zhuān)業(yè)教學(xué)改革就要將專(zhuān)業(yè)教學(xué)改革與教材建設(shè)兩者緊密結(jié)合,教學(xué)改革成果要充分體現(xiàn)在教材中,教材又是教學(xué)改革成果推廣的重要載體。因此,策劃編輯需要認(rèn)識(shí)到,教材開(kāi)發(fā)應(yīng)與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的改革相輔相成、互相促進(jìn)。在日常工作中,策劃編輯首先需要及時(shí)將教學(xué)改革的有效成果、先進(jìn)方法、新穎內(nèi)容在教材中反映出來(lái),同時(shí),積極關(guān)注衛(wèi)生職業(yè)院校教學(xué)改革新動(dòng)態(tài),為衛(wèi)生職業(yè)院校量身定制教改類(lèi)創(chuàng)新教材,進(jìn)一步幫助學(xué)校促進(jìn)教學(xué)改革的深化,比如我們根據(jù)院校需求定制了器官系統(tǒng)整合教學(xué)教材、“項(xiàng)目制”教學(xué)教材等。
2.教材立體化與培養(yǎng)現(xiàn)代衛(wèi)生職業(yè)人才目標(biāo)相契合
現(xiàn)代衛(wèi)生職業(yè)人才需具備扎實(shí)的專(zhuān)業(yè)基礎(chǔ)理論和基本知識(shí),更重要的是要有較強(qiáng)的實(shí)踐動(dòng)手能力。教材立體化建設(shè)應(yīng)運(yùn)而生。立體化的教材作為整合教育教學(xué)資源、優(yōu)化教育要素配置的途徑,是一種新型的整體教學(xué)解決方案,改變了過(guò)去單一的紙質(zhì)教材、書(shū)本教材那種過(guò)分重視知識(shí)傳授而忽視能力培養(yǎng)的教育弊端,為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策劃編輯在開(kāi)發(fā)紙質(zhì)教材的同時(shí),要注重開(kāi)發(fā)配套的以學(xué)科課程為中心的多媒體、多形態(tài)、多用途、多層次教學(xué)資源和教學(xué)服務(wù),包括網(wǎng)絡(luò)增值服務(wù)、電子教案、素材庫(kù)、網(wǎng)絡(luò)課程、試題庫(kù)等,以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為本,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幫助學(xué)生加強(qiáng)技能訓(xùn)練,充分利用圖書(shū)資料和聲像資料進(jìn)行學(xué)習(xí)。
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衛(wèi)生職業(yè)教材立體化建設(shè),已在教材編寫(xiě)、內(nèi)容呈現(xiàn)、教學(xué)服務(wù)等方面全面推進(jìn),服務(wù)于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學(xué)水平的提升和教學(xué)手段的現(xiàn)代化,推動(dòng)衛(wèi)生職業(yè)院校信息化教學(xué)水平的提高。目前出版的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材已全部配套網(wǎng)絡(luò)增值服務(wù),內(nèi)容豐富,包括原理動(dòng)畫(huà)演示、操作視頻、教學(xué)PPT、知識(shí)拓展、練習(xí)題等,并且可由作者提供新內(nèi)容不斷更新補(bǔ)充。除此之外,傳統(tǒng)的紙質(zhì)教材與現(xiàn)代的數(shù)字教材、慕課各有優(yōu)勢(shì)、各有側(cè)重,互為補(bǔ)充、有機(jī)融合。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部分?jǐn)?shù)字教材已經(jīng)上線(xiàn),通過(guò)數(shù)字教材與慕課、題庫(kù)平臺(tái)、數(shù)據(jù)庫(kù)、教學(xué)管理平臺(tái)等進(jìn)行充分整合,旨在提升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學(xué)水平和教學(xué)手段的現(xiàn)代化水平,與院校師生的管理、教學(xué)、學(xué)習(xí)需求密切結(jié)合。
3.全方位綜合服務(wù)與深層次需求相契合
策劃編輯要把每一套教材、每一本教材當(dāng)成一個(gè)項(xiàng)目、一個(gè)產(chǎn)品來(lái)做,服務(wù)理念要貫穿編輯出版的全過(guò)程,同時(shí)深層次挖掘需求,努力做到全方位服務(wù)。
(1)教材出版服務(wù)
定制教材:一方面,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材的選擇目前還沒(méi)有完全科學(xué)、統(tǒng)一的選用機(jī)制,多數(shù)職業(yè)院校采用專(zhuān)業(yè)帶頭人擇書(shū)制度,不同學(xué)校所選用的教材版本不盡相同。另一方面,不同地區(qū)的教學(xué)水平有所差異。這就要求策劃編輯要對(duì)院校情況加以分析與區(qū)別,針對(duì)不同地域、不同學(xué)生需求來(lái)制訂教材開(kāi)發(fā)方案。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在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區(qū)開(kāi)發(fā)了與地區(qū)教學(xué)實(shí)際相結(jié)合,突出區(qū)域疾病譜特點(diǎn)的區(qū)域教材。
及時(shí)供應(yīng):眾所周知,教材區(qū)別于其他類(lèi)型圖書(shū)的一大特點(diǎn)是季節(jié)性較強(qiáng)。每年兩個(gè)學(xué)期開(kāi)學(xué)之前,是教材(包括市場(chǎng)銷(xiāo)售和學(xué)校訂書(shū))的發(fā)行高峰期。因此,策劃編輯必須提前計(jì)劃好教材的整個(gè)出版周期,把握各流程進(jìn)度,保證及時(shí)供應(yīng)市場(chǎng),滿(mǎn)足學(xué)校需求。
(2)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
作為專(zhuān)業(yè)的醫(yī)學(xué)教育出版機(jī)構(gòu),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出版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材的一個(gè)重要目的是,促進(jìn)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各學(xué)科體系的發(fā)展和完善,提高師資水平,推動(dòng)專(zhuān)業(yè)人才隊(duì)伍培養(yǎng)。教材出版后,策劃編輯需盡快進(jìn)行有效回訪(fǎng),收集使用反饋信息,并結(jié)合教材的出版、使用,組織一系列促進(jìn)人才培養(yǎng)的活動(dòng)。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本著全程服務(wù)的理念,不斷創(chuàng)新服務(wù)機(jī)制,提高服務(wù)質(zhì)量。在通過(guò)專(zhuān)業(yè)教師培訓(xùn)會(huì)議、技能比賽、說(shuō)課比賽等活動(dòng)做好教學(xué)、師資培訓(xùn)的同時(shí),成立了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發(fā)展聯(lián)盟,在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材體系建設(shè)、教育模式改革、教學(xué)方式與辦學(xué)模式創(chuàng)新、教材建設(shè)水平等方面積極展開(kāi)合作與研究;建立并使用“全國(guó)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研究發(fā)展基金”支持教學(xué)等相關(guān)項(xiàng)目、課題工作;開(kāi)展形式多樣的“人衛(wèi)社杯”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教學(xué)相關(guān)活動(dòng);積極探討與校企合作建立實(shí)習(xí)基地,重視雙師型隊(duì)伍建設(shè),堅(jiān)持職業(yè)教育“校企合作、工學(xué)結(jié)合”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努力搭建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的專(zhuān)業(yè)建設(shè)、師資培養(yǎng)、課教改革高端服務(wù)平臺(tái)。
總的來(lái)說(shuō),開(kāi)發(fā)產(chǎn)品直接創(chuàng)造了出版社的利潤(rùn),而服務(wù)意識(shí)的提升在潛移默化中樹(shù)立了出版社的品牌形象。作為新時(shí)代的醫(yī)學(xué)教材策劃編輯,我們需要在“做中學(xué),學(xué)中思,學(xué)中做”,不斷提升個(gè)人職業(yè)素養(yǎng)與業(yè)務(wù)能力,與時(shí)俱進(jìn),加強(qiáng)服務(wù)醫(yī)學(xué)教育的理念,切實(shí)為作者、讀者、院校、行業(yè)提供優(yōu)質(zhì)醫(yī)學(xué)教育服務(wù)。
[1]夏登武,劉慶穎.解讀現(xiàn)代編輯的服務(wù)理念[J].出版科學(xué),2006(01).
[2]尹博,劉曉晶.教輔圖書(shū)策劃之我見(jiàn)[J].編輯之友,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