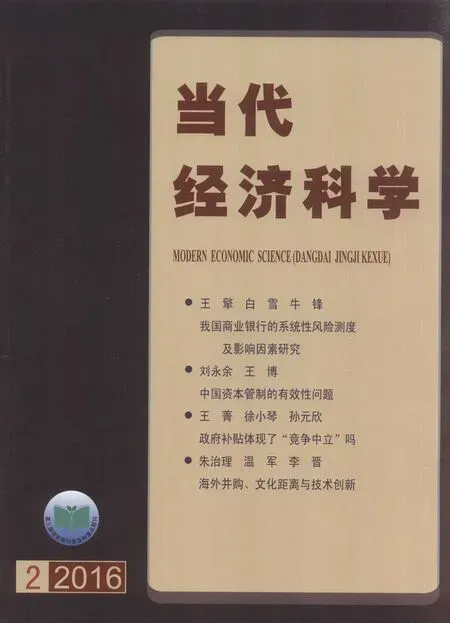超額現金持有、管理決斷權與投資扭曲——財務柔性視角下剩余負債能力的影響效應研究
董 理,茅 寧
(1.上海海事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上海 201306;2.南京大學 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
超額現金持有、管理決斷權與投資扭曲
——財務柔性視角下剩余負債能力的影響效應研究
董理1,茅寧2
(1.上海海事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上海 201306;2.南京大學 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摘要:本文基于財務柔性理論審視和分析投資扭曲行為的成因及其影響因素,引入管理決斷權作為關鍵調節變量,重點考察在剩余負債能力不同時,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關系的影響效應有何差異。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大比管理決斷權較小時,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表現出比總體更強的正相關關系;反之,無論管理決斷權大小,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因此,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不再是傳統代理理論演繹的線性正相關關系,財務柔性理論可以對此給出符合企業實際財務行為的合理解釋,同時也明確了管理者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關鍵詞:超額現金持有;管理決斷權;投資扭曲;財務柔性;剩余負債能力
一、引言
投資扭曲是企業實際投資偏離了預期內的正常投資,沒有達到最優投資水平的一種投資行為[1]。由于投資決策是事關企業生存和成長的核心財務決策,偏離正常投資的投資扭曲行為必須引起我國企業的高度重視[2]。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企業的投資扭曲?現有研究主要從代理理論的視角來進行解釋,認為管理者利用企業超額現金持有謀取私利的動機,直接導致了投資扭曲行為的發生。超額現金持有是企業在滿足了正常的交易動機與預防動機所需現金之外的可以被管理者自由支配的現金額度[3]。因此,超額現金持有越多,投資扭曲程度就越大。
但是,代理理論視角的研究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第一,單純從超額現金持有給企業提供了資金來源的角度分析其對投資扭曲的影響效應,沒有考察企業投資行為的實際決策者——管理者在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根據高階理論,企業是由管理者經營管理的,企業所有的決策和行為都是管理者選擇判斷的結果。而管理決斷權(managerial discretion)代表了管理者對企業經營決策發揮影響力的行為空間[4],正是可以體現管理者在企業決策中關鍵作用的核心變量[5]。企業的投資扭曲行為說到底是管理者通過手中的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進行支配、抉擇的結果。也就是說,管理決斷權會影響超額現金持有和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第二,忽視了影響管理者決策的重要因素——財務柔性(financial flexibility)[6]。財務柔性是指企業以低成本獲得融資來源的能力和及時應對未來未預期的現金流或投資機會變化的能力[7]。財務柔性理論認為,保持財務柔性是管理者制定各項財務決策時的首要考慮因素,超額現金持有和剩余負債能力是財務柔性的兩個主要來源[8]。剩余負債能力是指企業實際選擇的負債率小于資本結構理論預測的杠桿率值,通過保持負債能力來創造的財務柔性[9]。Arslan等研究指出,單獨分析超額現金持有這一種財務柔性來源與投資行為間的關系不符合企業財務實踐,因為企業事實上是通過兩種途徑來獲得財務柔性的,要深入洞察財務柔性對財務決策的影響,就必須同時考慮財務柔性的兩個來源[10],剩余負債能力存在與否會對管理者選擇判斷如何使用超額現金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本文從財務柔性理論視角出發,引入體現管理者關鍵作用的變量——管理決斷權,考察剩余負債能力不同情況下,管理者在擁有不同的管理決斷權時,是否會使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
本文可能的貢獻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在財務柔性視角下考慮剩余負債能力的影響情況,分析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更加符合企業財務實踐;二是將管理決斷權作為關鍵變量引入到研究中來,能夠更細致地刻畫出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實際關系。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自Fazzari等[11]提出投資對現金流敏感度的問題以來,現有文獻已證實了現金流越多,則企業的投資支出越多(例如,Hubbard[12];Moyen[13])。在此基礎上,Richardson將投資支出分為由企業成長機會、行業等因素決定的預期投資和非預期投資兩部分,其中非預期投資是企業實際投資與預期投資之間的差值,其大小代表了投資扭曲的程度。他考察了超額現金持有與企業投資扭曲的關系,發現二者是正相關的,即超額現金持有加劇了實際投資偏離正常投資的程度[1]。在此之后,有關超額現金持有導致的投資扭曲行為開始被研究者們所關注,成為近年來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焦點之一[14]。后續的研究,例如Riddick and Whited[15],Denis and Sibilkov[16],以及Baum等[17]等,都從代理理論出發,認為投資扭曲是管理者出于自利動機濫用現金所導致的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不僅會給股東及利益相關者帶來巨大損失,而且有害于企業的價值提升,阻礙企業可持續成長。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例如王彥超[18],楊興全等[19],及張會麗和陸正飛[14]等的研究結果,也都得出了一致的結論。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是強調超額現金持有作為財務資源對投資扭曲的影響效應,并沒有分析管理者利用超額現金進行投資決策時如何進行權衡的。那么,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在其對現金支配和使用的自由度不同時,即其擁有的管理決斷權大小不同時,超額現金持有是否仍會一貫顯著地導致投資扭曲增加?較高的管理決斷權給管理者提供了利用超額現金增加更多投資支出的行權空間,使得企業的投資與否和投資多少、投資項目的選擇以及投資方向的確定等投資決策更加建立在管理者選擇的基礎上。此時,管理者對超額現金持有和投資扭曲之間關系的影響較大。反之,在管理決斷權受到嚴格限制的情境下,管理者的選擇傾向就已經不重要了[20]。這就是說,較低的管理決斷權,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兩種可能性:一是限制了管理者能自由使用財務資源的可能性,即管理者對現金的使用支配權受監控的程度變大;二是限制了管理者能自由地實現個人目標而非企業或股東目標的可能性,即管理者無法隨意通過投資于損害企業價值的項目來為個人謀私利。綜上所述,不考慮其它影響因素時,管理決斷權應當對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
在另一方面,自從DeAngelo and DeAngelo[8]正式提出財務柔性理論之后,研究者們開始認識到,財務柔性問題是傳統公司財務理論與企業實際財務行為之間缺失的關鍵一環[21-23]。財務柔性理論的核心理念有兩個,一是“權衡”,即對于有限的財務資源,管理者要權衡是現在使用還是未來使用;二是“跨期性”,即管理者當前所做的財務決策不僅影響現在,更會影響到未來。只有權衡得當,在使用財務資源的當前財務決策中充分考慮到未來財務資源的需求,才能保證未來能夠抓住投資機會和抵御財務困境。將財務柔性作為首要決策因素的管理者必然會考慮到,有剩余負債能力時,企業同時擁有兩種來源的財務柔性,財務柔性較大;而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企業只擁有超額現金一種來源的財務柔性,財務柔性則較小[10]。
那么,從財務柔性視角出發,超額現金持有之外的另一種財務柔性來源——剩余負債能力的存在與否,是否會影響管理者在投資決策中行使管理決斷權呢?
一方面,如果有剩余負債能力,意味著企業能夠在未來進行負債融資。Chen等的研究表明,企業的剩余負債能力提高之后,可以獲得外部融資,現金持有的價值就會降低,即剩余負債能力可以替代現金持有[24]。Harford等也指出,如果企業有剩余負債能力的話,對未來再融資風險的擔心程度就很小;反之,未來不能通過債務再融資,就要通過保留或增加現金持有來滿足未來的投資需求[25]。實際上,在企業既持有超額現金,又有剩余負債能力時,增大了財務柔性從而減少了管理者決策對于資源可得性的依賴性,從實現的能力和環境條件方面給管理者提供了實現個人偏好動機的緩沖池[26]。Steensma and Corley也認為,較大的財務柔性會促進管理者決策的冒險性行為[27]。因此,剩余負債能力與超額現金持有的同時存在,滿足了企業財務柔性需要,使得管理者對于未來融資可得性的顧慮減小,不管是出于謀取私利的目的,還是因為現金持有的價值較小,管理者現在都可以放心大膽地利用超額現金進行投資支出,超額現金持有導致投資扭曲的傾向性增大。管理決斷權較大時,管理者能夠將這個傾向性變為現實決策,超額現金持有的增多會進一步導致投資扭曲的程度增大。但是,管理決斷權較小時,管理者對于現金支配使用的權力空間較小,超額現金持有導致的投資扭曲程度比管理決斷權較大時顯然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意味著企業事前用盡了負債能力,不可能再在事后(未來)通過負債進行融資來滿足投資需求。Jenson指出,企業的事前負債需要事后通過現金流去償還本金和利息,所以事后能從現金流中保留現金的能力也越小[28]。可以說,由于不存在剩余負債能力,且從未來的現金流中獲得超額現金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未來抓住投資機會和避免財務困境只能更加依靠于現有的內部資金。而且,沒有剩余負債能力,事實上表明,企業已把未來的財務風險轉移到了現在[29],包括償還事前債務以及未來無能力再融資的雙重財務風險。Hoberg等為此提出,財務柔性的考慮在企業遇到風險時最為重要。也就是說,為了避免未來出現財務困境時無法避險,以及避免未來投資機會出現時,不得不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而放棄,管理者必須現在就考慮未來的財務柔性[23]。另外,一些債務還從協議上限制了企業的一部分資本支出,較多的事前負債會抑制管理者的自利行為[30]。因此,對管理者來說,就算管理決斷權較大,可以自由支配現金,但是超額現金的使用只會進一步惡化企業已經不充分的融資能力,增大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所以,最佳的做法是將現有的超額現金保留在企業內部,降低財務風險,而不是用于投資支出。無論管理決斷權大小,超額現金持都不會導致投資扭曲的出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和假設2。
假設1:企業既持有超額現金,又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大比管理決斷權較小時,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強。
假設2:企業持有超額現金,但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無論管理決斷權大小,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三、 研究設計
(一) 變量設定
投資扭曲的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超額現金持有作為主要解釋變量,管理決斷權、是否有剩余負債能力作為調節變量,這四個變量是本文的關鍵變量。因為它們都是不能被直接觀測到的指標,必須通過代理變量進行間接測量。
1.超額現金持有的度量
借鑒Dittmar and Mahrt-Smith[31]及楊興全等[19]等的研究方法,用回歸模型(1)的殘差項測定超額現金持有。在模型(1)中,因變量Cash表示企業第t年的現金持有水平。自變量分別為表示企業第t年的資產規模(Asset),負債水平(Lev),凈營運資本水平(NWC),現金流回報率(Cfratio),資本性支出(Cap),成長性(TobinQ),股利支付傾向(Payer)。Industry和Year分別代表對行業和年份的控制。企業實際現金持有水平與通過模型(1)得到的現金持有水平擬合值之間的差值大于零時,說明企業持有超額現金(CFF)。
Casht=α0+α1Assett+α2Levt+α3NWCt+α4Cforatiot+α5Capt+α6TobinQt+α7Payert+Industry+Year+εt
(1)
2.管理決斷權的度量
借鑒蘇文兵等[32]、Dong and Gou[33]的研究方法,利用職位權、報酬權和運作權三個代理變量,取三個值的正態標準值的均值來測定管理決斷權(MD)的大小。
職位權代表了管理者在企業中法定權力的大小。董事會清晰而嚴密的監控會使高管人員的行為空間受到較大限制,但是當董事會的警惕性變弱時,對高管人員的監控同時變弱[34]。Hayward and Hambrick[35]證實了,當董事長和總經理雙職合一時董事會的警惕性最弱,此時高管人員可獲得更大的行為空間。所以,用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設置的狀況來測量職位權,總經理兼任董事長的,變量取值為1;總經理兼任副董事長的,記為0.5;總經理既不是董事長也不是副董事長的,記為0。
運作權代表了管理者可以支配企業資源的自由程度。當企業擁有更多資源時,傾向于有更多的空間來放任地從事探索性行為,更多的資源也給予了管理者更大的行為空間[5]。在企業擁有的不同類型的資源里,營運資金對于企業獲得可持續的競爭性利益非常重要,是企業資產中能夠決定企業經營管理活動能否順利開展的基礎。所以,用企業年營運資金與年營業收入的比值來測量運作權,該值越大則表示管理者在經營管理中可控制的資源越多,運作權越大。
報酬權代表了管理者的薪酬水平,能夠體現企業對其決策風險的補償和其對自身薪酬設定的影響力,反映了管理者在經理人市場上的個人職業價值及其與利益相關者談判的比較優勢。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參照李維安等[36],用企業前三名薪酬最高的高管薪酬的均值取對數進行測量,該值越大則表示管理者的報酬權越大。
3.剩余負債能力的度量
借鑒Marchica and Mura[9]的方法,用回歸模型(2)的殘差項測定剩余負債能力。在模型(2)中,因變量Lev表示企業第t年的負債水平,自變量為表示企業第t-1年的負債水平(Levt-1),第t年的行業負債水平中位值(Indlev),成長性(TobinQ),資產規模(Asset),有形資產水平(TANG),總資產收益率(ROA),非債務稅盾(NDT)。Year代表對年份的控制。企業實際負債水平與通過模型(2)得到的負債水平擬合值之間的差值小于零時,說明擁有剩余負債能力,設為虛擬變量(SDC1_dev),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Levt=α0+α1Levt-1+α2Indlevt+α3TobinQt+α4Assett+α5TANGt+α6ROAt+α7NDTt+Year+εt
(2)
4.投資扭曲的度量
借鑒Richardson[1]、王彥超[18]及張會麗和陸正飛[14]的研究,用回歸模型(3)的殘差項測定投資扭曲的程度。在模型(3)中,因變量Inv表示企業第t年的實際投資水平;自變量分別為代表企業第t-1年的資產規模(Asset)、負債水平(Lev)、成長性(TobinQ),現金持有水平(Cash)以及第t-1年的實際投資水平(Invt-1),股票回報率(Return),企業年齡(Age)。通過模型(3)得到企業投資水平的擬合值,即為企業的正常投資水平,而模型的殘差大小則代表了投資扭曲程度。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整個童年里我總以為所有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樣靜默、隱忍,是一具具慘白干枯的軀干,沒有面孔又無聲無息。等稍長大些,每每看到同學和來接他們的父母合家歡樂的模樣,意識到自己的迥異所帶來的痛苦和羞恥。天黑后,我悄悄潛入墓地,扶住他的墓碑流淚,在我身邊聚集起瑩綠竄動的鬼火牽引我抵達未知的境遇,泥土掩埋了不會衰老的軀體,我撿回這具顱骨放置于床頭,就會在淚眼婆娑的睡夢中與飽滿健康的父母相見。”我無法預知猝不及防的死亡。
Invt=β0+β1Assett-1+β2Levt-1+β3TobinQt-1+β4Returnt-1+β5Aget-1+β6Casht-1+β7Invt-1+Industry+Year+εt
(3)
此外,參考楊興全等[19]及張會麗和陸正飛[14],將管理費用率(GLFY)和其它應收款(QTYSK)作為控制變量,用以控制來自大股東操控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
各變量的定義和計算方法,詳見表1。
(二)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2005-2011年在我國滬深兩市A股市場上市的企業為總體樣本,數據來源是CCER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這一特殊事件,為保證樣本的有效性,本文以2008年為中心點,選取了前三年和后三年的上市企業財務數據。同時剔除了金融類企業,剔除了各年度ST類企業,剔除了2004年及以后上市的企業,剔除了財務數據異常的企業。對于數據庫中的缺失值,本文首先通過查找年報的方式補齊,對于年報中也沒有的數據,本文通過取樣本變量平均值的方法替代缺失值。本文共觀察了838家樣本企業。
(三) 研究方法
Invdist=β0+β1CFFt-1+β2MDt-1+β3CFFt-1×MDt-1+β4CFFt-1×MDt-1×SDC_devt-1+β5GLFYt-1+β6QTYSKt-1+Indusrty+Year+εt

(4)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根據本文的研究問題,選取持有超額現金的樣本組進行考察,即企業實際現金持有水平與通過回歸模型(1)得到的現金持有水平的擬合值之間的差值大于零的樣本組。表2給出了本文主要研究變量投資扭曲(Invdis)、超額現金持有(CFF)、是否有剩余負債能力(SDC1_dev)、管理決斷權(MD)及控制變量管理費用率(GLFY)和其它應收款(QTYSK)的描述性統計。各變量根據表1中的變量測度方法計算而得。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分析
1.層級回歸法檢驗
首先,為了檢驗剩余負債能力是否會影響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導致的投資扭曲的調節作用,采用層級回歸法考察三項交互項CFF×MD×SDC1_dev是否顯著異于零。表3給出了回歸結果。
在表3中,模型一是只有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礎上添加了主要解釋變量超額現金持有(CFF),調節變量管理決斷權(MD)的回歸模型,從中可以看出,CFF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但是,管理決斷權(MD)對投資扭曲(Invdis)無顯著影響。

表3 剩余負債能力對管理決斷權調節作用的影響效應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括號里面的數值表示標準差。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礎上添加了超額現金持有與管理決斷權的交互項(CFF×MD)的回歸模型,從中可以看出,CFF×MD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在不考慮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MD)對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即較強的管理決斷權加大了由于超額現金持有而導致的投資扭曲行為。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礎上添加了三項交互項CFF×MD×SDC1_dev。此時,CFF×MD的系數比模型三中的顯著性變弱且系數值變小,而CFF×MD×SDC1_dev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剩余負債能力會影響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導致的投資扭曲的調節作用。
2.分組回歸檢驗
為了進一步判定在剩余負債能力情況不同時,管理決斷權(MD)對于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關系影響作用的具體模式,根據陳曉萍、徐淑英和樊景立[37]檢驗定類變量調節作用模式的方法,進行分組檢驗。
首先,將有剩余負債能力(SDC1_dev=1)的樣本劃分為兩組,分組原則是以該樣本管理決斷權(MD)的中位數(MD=-0.236)為基準,低于中位數(即MD<-0.236)的為一組,高于中位數(即MD>-0.236)的為另一組。然后,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回歸,考察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關系。同理,將沒有剩余負債能力(SDC1_dev=0)的樣本,依據該樣本管理決斷權(MD)的中位數(MD=-0.252)劃分為兩組,一組為低于中位數(即MD<-0.252),另一組為高于中位數(即MD>-0.252)。然后,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回歸,考察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關系。表4給出了該分組回歸的結果。
在表4中,模型一是超額現金持有的全樣本回歸結果;模型二和模型三分別是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小于中位數和大于中位數的分組樣本回歸結果;模型四和模型五分別是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小于中位數和大于中位數的分組樣本回歸結果。可見五個模型均對行業和年份進行了控制。
可以看出:第一,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小的一組(即模型二)的回歸結果顯示,超額現金持有(CFF)的系數比模型一當中的顯著性降低,這說明此時超額現金持有(CFF)對投資扭曲(Invdis)影響效應較小。但是,管理決斷權較大的一組(即模型三)的回歸結果顯示,超額現金持有(CFF)的系數顯著為正,且該系數值大于全樣本回歸(即模型一)中其系數值。這說明,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關系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第二,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小的一組(即模型四)和管理決斷權較大的一組(即模型五)的回歸結果都顯示,超額現金持有(CFF)的系數不顯著。這說明,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無論管理決斷權大或小,超額現金持有(CFF)對投資扭曲(Invdis)都不存在顯著的影響效應。
總之,上述回歸結果顯示,假設1和假設2都得到了驗證:第一,在企業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關系產生顯著的調節作用,即企業既持有超額現金,又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大比管理決斷權較小時,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強。第二,在企業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無論管理決斷權是大還是小,超額現金持有都不能明顯導致投資扭曲,即企業持有超額現金,但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表4 剩余負債能力不同時管理決斷權調節作用分組回歸結果(一)
注:表4中,***,**,*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括號里面的數值表示標準差。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 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參照Arslan等[10]及董理和茅寧[38]的方法,利用企業實際負債水平的中位數來判定是否有剩余負債能力,即低于樣本負債水平中位數的企業視為有剩余負債能力,設為虛擬變量(SDC2_med),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與上述檢驗方法同理,將有剩余負債能力(SDC2_med=1)的樣本劃分為兩組。分組原則是以該樣本管理決斷權(MD)的中位數(MD=-0.179)為基準,低于中位數(即MD<-0.179)的為一組,高于中位數(即MD>-0.179)的為另一組。然后,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回歸,考察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將沒有剩余負債能力(SDC2_med =0)的樣本,依據管理決斷權(MD)的中位數(MD=-0.257)劃分為兩組,一組為低于中位數(即MD<-0.257),另一組為高于中位數(即MD>-0.257)。再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回歸,考察超額現金持有(CFF)與投資扭曲(Invdis)之間的關系。
表5給出了該分組回歸的結果。在表5中,模型一是持有超額現金的全樣本回歸結果;模型二和模型三分別是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小于中位數和大于中位數的分組樣本回歸結果;模型四和模型五分別是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小于中位數和大于中位數的分組樣本回歸結果。五個模型均對行業和年份進行了控制。表5的五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與表4的回歸結果類似。這表明,研究假設依然可以被驗證。

表5 剩余負債能力不同時管理決斷權調節作用分組回歸結果(二)
注:表5中,***,**,*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括號里面的數值表示標準差。
五、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財務柔性理論的視角出發,將管理決斷權作為調節變量,考察了剩余負債能力不同的情境下,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結果發現:在剩余負債能力影響下,管理決斷權對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產生不同影響。企業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決斷權較大比管理決斷權較小時,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表現出比總體更強的正相關關系;而在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無論管理決斷權大小如何,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上述研究結論說明,在高度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下,保持適當的財務柔性是企業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因此,財務柔性是管理者進行投資決策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有剩余負債能力時,未來的財務柔性可以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管理者在對企業的超額現金具有較大支配和使用權時,因為現金持有的價值減小或者謀取私利的目的會促使投資扭曲行為的增多。其結果,導致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的關系表現出比總體更強的正相關關系。相反,如果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未來能否擁有足夠的現金來滿足不可預期的資金需求成為管理者關注的首要問題,無論管理決斷權大小,管理者都不會將持有的超額現金用于非正常的投資行為,因此,超額現金持有與投資扭曲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本文的研究結果為人們從一個新的視角理解投資扭曲的成因,從而更好地管理超額現金持有、提升投資決策效率提供了一個新思路。由于投資決策是“跨期性”決策,并且用來滿足投資需求的各融資方式之間會互相影響[39],如果僅考慮內部資金的可得性,而不考慮外部資金的可得性,將失之偏頗、決策失誤。在沒有剩余負債能力時,管理者必須明確企業不僅無法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資金支持,還有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此時應盡量保持現有的財務柔性來源,即超額現金持有,避免投資扭曲的出現,以防止財務危機發生更遑論抓住未來的投資機會。反之,如果企業既有剩余負債能力,又持有超額現金,就給管理者提供了一個掠奪現金,建造個人企業帝國的溫床,此時加強相應的監控顯得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1]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3): 159-189.
[2]羅紅霞. 提高我國上市企業投資效率的策略[N]. 光明日報, 2014-04-07(5).
[3]Bates W T, Kahle M K,Stulz M R, Why Do U S. Firms hold so much more cash than they used to?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5): 1985-2021.
[4]Hambrick D C, Finkelstein S. Managerial discretion: a bridge between polar views of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7, 9: 369-406.
[5]Hambrick D C.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 updat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2): 334-343.
[6]Almeida H, Campello M,Weisbach M S. Corporate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when future ?nancing is not frictionles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 675-693.
[7]Denis D J. Financial flexibility and corporate liquidity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 667-674.
[8]DeAngelo H,DeAngelo L. Capital structure, payout policy,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 [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2009.
[9]Marchica M T, Mura R. Financial flexibility, investment ability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firms with spare debt capacity [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0, Winter: 1339-1365.
[10]Arslan ?, Florackis C,Ozkan A. Financial flexibility,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crises [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4, 42(2): 211-250.
[11] Fazzari S M, Hubbard R G, Petersen B C.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 Issue1: 141-195.
[12]Hubbard R G. Capital-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 36: 193-225.
[13]Moyen N.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constrained versus unconstrained firm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5): 2061-2092.
[14]張會麗, 陸正飛. 現金分布, 企業治理與過度投資——基于我國上市企業及其子企業的現金持有狀況的考察[J]. 管理世界, 2012 (3): 141-150.
[15]Riddick L A, Whited T M. The corporate propensity to save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4): 1729-1766.
[16]Denis D J,Sibilkov V.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vestment, and the value of cash holding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 247-269.
[17] Baum C F, Caglayan M, Talavera O. The effects of fu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expenditures on firms’ Liquidit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21(3): 459-474.
[18] 王彥超. 融資約束, 現金持有與過度投資[J]. 金融研究, 2009 (7): 121-133.
[19] 楊興全, 張照南, 吳昊曼. 治理環境, 超額持有現金與過度投資——基于我國上市企業面板數據的分析[J]. 南開管理評論, 2010 (5): 61-69.
[20]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Top-management-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3): 484-503.
[21] Denis D J, McKeon S B. Debt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 evidence from pro-active leverage increase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2, 25: 1897-1929.
[22] Bonaimé A A, Hankins K W, Harford J. Financial flexibility, risk management and payout Choice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 Advance Access.
[23]Hoberg G, Phillips G, Prabhala N. Product market threats, payouts,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4, 69(1): 293-324.
[24] Chen T, Harford J, Lin C. Financial flexibility and corporate cash policy [R].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orking Paper, 2013.
[25] Harford J, Klasa S, Maxwell W F. Refinancing risk and cash holding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4, 69(3): 975-1012.
[26] Patzelt H, Shepherd D A, Deeds D, Bradley S W. Financial slack and venture managers’decisions to seek a new alli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4): 465-481.
[27 ]Steensma H K, Corley K G.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s a moderator of theories on firm boundaries for technology sourc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2):271-291.
[28] 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 323-329.
[29] Acharya V A, Almeida H, Campello M. Is cash negative debt? A hedging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7, 16: 515-554.
[30] Stulz R M.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optimal financing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6(1): 3-27.
[31] Dittmar A, Mahrt-Smith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value of cash holding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3: 599-634.
[32] 蘇文兵, 李心合, 徐東輝, 許佳. 經理自主權與R&D投入的相關性檢驗——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10(8): 30-38.
[33] Dong J, Gou Y.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the R&D investment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0, 19: 180 -188.
[34] Crossland C, Hambrick D C. How national systems differ in their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executives: A study of CEO effects in three countr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8): 767-789.
[35] Hayward M L A, Hambrick D C. Explaining the premiums paid for large acquisitions: evidence of CEO hubri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1): 103-127.
[36] 李維安, 劉緒光, 陳靖涵.經理才能、企業治理與契約參照點: 中國上市企業高管薪酬決定因素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 2010(2): 4-15.
[37] 陳曉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證方法(第二版)[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38] 董理, 茅寧. 公司成熟度, 剩余負債能力與現金股利政策——基于財務柔性視角的實證研究 [J]. 財經研究,2013,39(11):59-68.
[39] Almeida H, Campello M. Financing frictions and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und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0,45(03):589-622.
責任編輯、校對:李斌泉
Excess Cash Holding,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The Effect of Spare Liability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Theory
DONG Li1, MAO N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rvey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vestment distortion on the basis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theory. It introduces managerial discretion as a key adjustment variable and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effect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ess cash holding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 when the spare liability capacities are differ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n the enterprises have spare liability capacity and the managerial discretion is relatively large or small,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at is stronger than the general level exists between excess cash holding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 By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relevance exists between excess cash holding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 whether managerial discretion is big or small. Therefore, no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principal-agency theory exists between excess cash holding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 Financial flexibility gives th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hat is in line with enterprises’ actual financial behaviors. Meanwhile, it clearly defines the key roles played by managers in it.
Key words:Excess Cash Holding; Managerial Discretion; Investment Distortion; Financial Flexibility; Spare Liability Capacity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6(02)-0094-09
作者簡介:董理(1980-),女,江蘇省阜寧縣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南京大學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公司財務與金融;茅寧(1955-),江蘇省南京市人,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司財務與金融。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財務柔性、管理者戰略選擇與企業可持續成長”(批準號:71372031),2015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
收稿日期: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