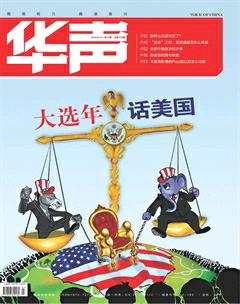加拿大“蹲監者”的忠誠與痛苦
易萱
不少人把日子當“牢”來坐,當“罪”來受。而為了受這種“罪”,他們不惜丟掉國內的工作,甚至割舍親情。
2015年10月,加拿大護照還沒到手,汪巍巍就迫不及待往中國跑。他獲得了一個“回流”機會——加拿大一家企業在北京設立分公司,他成功競聘,成了北京分部市場部總監。
這是一個汪巍巍苦等了六年的回國機會。六年前,他通過一家移民咨詢公司辦理技術移民,登陸溫哥華。他當時對未來生活信心滿滿,正如移民中介對他介紹的,加拿大福利好、環境美、工資高,是個去了就不想離開的宜居勝地。
他萬萬沒想到,現實中,勝地轉眼就變成牢籠。
2014年底,汪巍巍父親被檢查出直腸癌,急需家人照顧,當時,他正在坐“移民監”。為了湊滿留居天數,汪巍巍不得不讓母親獨自帶父親往返于醫院進行化療。那時,他終于明白了那句老話:“父母在,不遠游。”
和汪巍巍類似,許多人對加拿大生活的美好想象并沒能順利照進現實。不少人把日子當“牢”來坐,當“罪”來受。而為了受這種“罪”,他們不惜丟掉國內的工作,甚至割舍親情。
“中國式幽默”
2002年,74歲的張啟益和老伴兒來多倫多定居。最近五六年,張啟益發現周圍出現了很多不想在加拿大呆著的人。他們不少人都在國內經營實業,移民主要目的是“拿身份”和“保證資金安全”,并不想生活在此地。因此,在加拿大的日子,度日如年。聚會時,如何能夠投機取巧地逃避“移民監”和“怎么可以造假自己的納稅證明”倒成了熱門話題。
盡管多倫多在加拿大算是比較現代化的大型城市,但距離那些富人的心理預期還存在相當距離。某次聚會時,一個過來“坐監”的某單位領導問他,“在國內,外出有司機,家里有保姆,看病還可以優先。有點麻煩還可以找朋友解決。你說說在這兒除了能吸點干凈空氣還能干嗎?”
張啟益聽了哭笑不得。“這些人,多一天也不愿意在加拿大呆。”張啟益說,“只想從國家占便宜而不想對國家有一點付出,我都替加拿大政府心寒。”
與張啟益一樣,加拿大語言學家斯蒂夫也對這些人深感疑惑。他本身是個“中國通”,太太也是一位華人,常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的移民。
2016年2月,斯蒂夫受邀參加在列治文舉辦的移民政策調整社區研討會,會上他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中國人的關注焦點都是如何正確理解“移民監”政策的變動。討論時,很多中國人都在問,“(獲得永久居留權規定的)‘五年住兩年到底怎么計算?”斯蒂夫還聽到一對三十多歲的中國夫婦問工作人員:要想符合規定,怎么樣呆最合適?
負責政策解讀的工作人員似乎沒有理解,這對夫婦詢問的是應對“移民監”的技巧。不過,站在旁邊的另一個老人卻提點了他們:“當然是每隔一年回國一次最合適啦。”
這段對話讓斯蒂夫大為震驚。“(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規定稱為)‘移民監,就是對加拿大的一種傷害。”他對太太抱怨。
“拜托,這個詞只是一種中國式幽默。”他的太太回答。
斯蒂夫顯然無法理解這種幽默。他向記者表達疑惑時說,人們在責備加拿大無法“善待”移民申請人時,這些中國移民是否想過對這個國家的傷害呢?
“不忠的加拿大人”
2012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的王茜和老公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她拿下了財務管理碩士文憑和CFA(特許金融分析師)證書,隨后,成功進入了溫哥華一家外資企業工作,并成為財務部主管。
“想做加拿大公民么?那不但要享受公民的權利,也要負擔公民的義務。”王茜說,規避“移民監”都是些黑中介忽悠人的把戲,那些既想生活在中國又想拿外國身份的人更是讓她不屑。
王茜在加拿大的移民日子也并非順風順水。初到加拿大,為了節約生活開支,她和丈夫曾經去政府設立的“foodbank”(食物救濟處)領取食品。大女兒的很多玩具也是在社區回收的。為了進修取得專業執照,她幾乎一年沒買新衣服。
因此,獲得公民身份時刻的喜悅才如此有沖擊力。王茜永遠記得2012年6月24日,“宣誓時,每個人都舉起右手說出自己的名字,輪到我時,我發現自己腦子一片空白,鼻子很酸。”王茜說,自己拿著公民證,笑著流淚。“不吃苦中苦,哪里成得了加拿大人。”
對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斯蒂夫來說,最希望移過來的都是王茜這樣的人——真心實意喜歡這片土地,并且愿意長期居留在此地,為這個國家努力打拼。他很難相信,如果都是坐完“移民監”就走人,那對這個國家又有什么幫助呢?
加拿大向來以身為“最宜居的移民國家”而自豪,但諷刺的是,越來越多的移民卻在取得公民身份后,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加拿大式生活”而移居海外。
總部位于溫哥華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2013年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約有280萬加拿大公民長期居住海外,占國民人口總數的8.8%,比率僅次于英國的9%,全球排名第二,遠高于澳大利亞(4.3%)、法國(3.3%)、中國(2.6%)及美國(1.7%)。在1996年至2006年間,取得加拿大公民資格后移居海外的移民比率,是土生加拿大人的3倍。
根據加拿大官方標準,外來移民登陸國境后五年內從未上交納稅申報單,或雖在前五年內上交,但以后四年或四年以上從未上交的,即被認為是“海外公民”(長期離境)。加拿大人一直將這些移居海外的公民視為“失敗者”或“不忠的加拿大人”。
“忠誠”的代價
對“失敗者”這個標簽,王茜并不那么贊同。曾在加拿大經歷過艱苦生活的她,更清楚移民在這里就業的門檻到底有多高。
“技術移民中絕大部分都屬于有著豐富的‘國內工作經驗而不是‘北美工作經驗。來加拿大如果不重新讀書,能找到體面工作的機會微乎其微。”王茜說,她身邊,在“移民監”期間找到稱心工作的人簡直鳳毛麟角。
張啟益同樣也感到“移民監”帶來的諸多不便。他們這種老來移民者,最難受的是孤獨感。在加拿大一些購物廣場常能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老頭、老太太們每天一早就像上班一樣,走路、坐公車或者被子女送來百貨公司,然后,一起到百貨商場的休息區或者咖啡館聊天。到了晚飯時間,再各自回家。
“實在太村了,開了半個小時車去百貨,連個像樣的牌子都沒有,還不如我們青島這種二線城市的商場”;“什么都聽不懂,太痛苦了,電視也不好看。再呆在這兒非要老年癡呆不可。”抱怨連連的都是些在加拿大生活碰壁的人,他們無法適應環境的改變,另一方面又為了保證永久居留身份或者入籍而強迫自己生活于此。每當聽到這些抱怨,張啟益都煩躁不已。“過得這么別扭,還非要留在這兒。”他不禁小聲嘀咕。女兒則馬上用手戳他后腰,示意他閉嘴。
比一般老年人幸運的是,張啟益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除了這種群體性聊天,他可選的余地要更多一些,比如去社區超市做理貨員。
如今每天早上7:50,他都必須提早來到超市,迎接供貨的運貨司機,上午上班四個小時,下午還有四個小時,每小時的報酬為12加元(約60元人民幣)。他在這里干一天,還比不上以前在國內兼職一小時的收入。不過,張啟益很清楚,在加拿大自己需要的并不是錢。
“記得剛來多倫多時,我在華人超市看到一個83歲的老頭做保潔。”張啟益回憶道,“我問他,這么大歲數怎么還工作,他們給你多少錢一小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