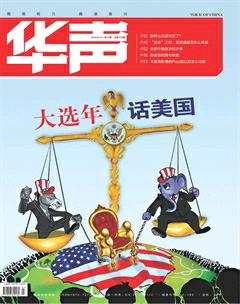明朝倆名臣肝膽相照,但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覃仕勇++張嵚
無論貶損贊譽,張璁有一樣偉業是無可抹殺的:以霹靂雷霆般的手段,仿佛利刀割除腐肉一般的手術,造就了大明朝嘉靖年間的燦爛中興。
明代嘉靖時期的內閣首輔張璁,是整個明朝后半期如雷貫耳的人物。在諸多學者評述中,他常被丑化為逢迎小人,而造就“萬歷中興”的改革巨匠張居正,卻給他至高評語:心儀而癱之贊嘆。
無論貶損贊譽,張璁有一樣偉業是無可抹殺的:以霹靂雷霆般的手段,仿佛利刀割除腐肉一般的手術,造就了大明朝嘉靖年間的燦爛中興。《明經世文編》評曰:功在社稷,莫大于是。
大器晚成躋身內閣
張璁,字稟用,浙江溫州永嘉人,生于明朝成化十一年。他小小年紀就才華橫溢,但悲催的科考路讓嚴重自信的張璁本人痛不欲生。張璁參加了八次科舉,才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榮登黃榜。這一年,張璁已經四十七歲了。
張璁成績慘淡,是個三甲末流,以明朝的官場規則,翰林院庶吉士入閣,理論上全無份,又是個要抱孫子的年齡了,飛黃騰達?好難。
誰知人生的機會,竟來得那么突然:這一年三月,正德帝朱厚燳病死了。正德帝無子,遺詔迎取堂弟朱厚熜為帝,是為嘉靖帝。14歲的朱厚熜驀登大寶,有心追尊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為皇考,從而引發了明朝歷史上著名的“大禮儀事件”。
這次事件表面看來,爭的是皇帝該認誰當爹,但放當時看,其實是新皇帝和老臣子們誰說了算的問題。就在雙方相持不下時,身份不入流的張璁,好比戰場上潛伏叢林的狙擊手,精確地向著與嘉靖帝頂牛的老臣楊廷和一干人,打出最具殺傷力的一顆子彈——《大禮或問》。
很多后人都認為,這是一封拍馬逢迎的奏疏,內容又臭又長,目的結果都十分卑劣。但僅看其內容,就知道有多強大——文章內容絲絲入扣,氣魄逐漸上揚,漂亮撐起大旗:皇上您決不能隨便換爹。以晚明學者錢謙益的說法,就似錢塘江潮,默默聚攏,忽然巨浪排空。
要說這篇文章,單純就為逢迎嘉靖帝,卻也不盡然。在舉進士第之前,張璁在家鄉溫州大羅山的東麓瑤溪創辦了羅峰書院,和心學創建人王守仁有一定交往,受王守仁思想影響較深,認為強行制止別人認父認母是在根本上有違人情、人性的。這樣,即使張璁只是一個連正式官職都沒有的“觀政進士”,他也無法保持沉默。
幫嘉靖帝爭爹,張璁是認真的,其認真態度,讓嘉靖帝讀完后的第一時間,就感動得近乎涕淚交流,少年心性未盡脫的他,當場就仰天大呼:吾父子終獲兩全也!
這場嘉靖年間一度相持不下的政爭,劇情驟然轉換:張璁為代表的“認爹派”與楊廷和為代表的“換爹派”猛掐,嘉靖帝得以輕松借力打力,贏得這場爭爹大戰的勝利。而張璁官位也一直扶搖直上,這個黃金機會,他真抓住了。
抓住機會,也拉足了仇恨。等到張璁獲得重用,眼看就要入閣時,各方面力量也賣力阻止,就不讓你入閣!
這時一個神交已久的親密戰友,挺身而出幫助了他:楊一清。
如果說正德年間的老臣們,誰能有楊廷和那樣重大的影響力,那當屬楊一清。在張璁初上《大禮或問》,開罪滿朝老臣時,第一個跳出來助拳的,正是遠在家鄉歸養的楊一清。他讀完這奏疏后拍案叫絕:張生此議,圣人復起,不能易也。
他的鮮明態度,也好似武俠小說中源源不斷的真氣,撐起了張璁為代表的“認爹派”的底氣,從而步步為營,趕走楊廷和。
楊一清為什么要幫張璁?從人品上說,楊一清公認是明代性情豁達的人物,做事更擅長調和:新君登基,穩定第一,拿著這風波脅迫皇帝,不是嫌大明朝亂得不夠么?類似的態度,他不但對喬宇等門生講過,也曾以私人身份,苦苦勸說過楊廷和。
當然這樣的好心里,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大半輩子啥官都做過,卻就沒入過閣,人生這巔峰一步,必須和張璁密切合作才雙贏。
在利益和相互激賞下,張璁與楊一清,這兩位人生資歷境況迥然不同的厲害人物,在嘉靖年間的黨爭中,結成了第一組戰略同盟,效果也出奇好:楊廷和走人,楊慎罷官,費宏辭職,正德年間的老班底,幾下一掃而空。而楊一清則如愿出任內閣首輔,接著投桃報李,把張璁運作進了內閣。大明王朝的政府最高權力機構,成了這好哥倆的二人轉。
對楊一清的幫助,張璁一生都感激,以他自己的話說: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亦不少矣!
兩位身懷大才的杰出人物,在共同的政治對手前走到一起。而兩人又都懷有振興社稷的遠大理想,而今內閣權柄在手,是不是該除舊布新大展宏圖了?
誰知更如火如荼的場面,緊接著就展開了——先前還密切合作的這二人,竟然在嘉靖帝面前生猛互掐起來,打得比當年幫嘉靖帝“認爹”時還熱鬧。
這就奇了怪了,友誼的小舟,為啥說翻就翻呢?
翻船之因
張璁一輩子挨罵事極多,其中就包括他就任內閣大學士后和楊一清的互撕。好些史家眼里,這就是個張璁恩將仇報的故事。但仔細看看張璁入閣后的表現,就知道并非如此。
早在張璁入閣前,也就是嘉靖六年署理都察院時,他先毫不留情整頓都察院風氣,刷掉了二十多個言官。還嚴抓考勤制度,上班下班加班都有時間規定,嚴打貪污腐敗,鼓勵言官糾察不法。這場嘉靖帝上任后第一輪劇烈反貪風暴,鬧得“一時苞苴路絕”,廉政風氣大好。
就連被張璁和楊一清聯合排擠辭職的老首輔費宏,對這事都服氣,說自己這幫老人一輩子整頓吏治,做夢都盼不到的好風氣,竟讓張璁做到了。
等到張璁入閣為相,大權在手,改革的步子也就越大,另一個更戳火藥桶的事,就是改革科舉制度。
明朝科舉制度發展到此時,問題有多嚴重?看看張璁考七次的倒霉人生路就知道。白白耗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在科考上,人生的黃金年華就在尋章摘句中不知不覺地流逝。
總結這經驗教訓,張璁決心做一件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素質教育:重新規定考試文體,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重在考察應試者素質,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
而另一個煞費苦心的地方,就是翰林院。按照明朝之前的規定,只有科舉考取前列成績者,才能入翰林院。而且日久天長,內閣大學士開始操控歷年的翰林院學生名單,安插自己親信,好好一個培養人才的地方,成了內閣大學士拉幫結派的自留地。
這個游戲規則張璁懂,以他的智商,如果照這個規則玩,只能玩得更好。但他態度堅決:廢!他直接用個最簡單方式——考試。不但選翰林要考,在職的也要考,不但考詩詞文章,更考國計民生的實在學問。甚至六部的各級小官,任期滿了都能來考。不管你科舉成績如何,只要你能造福社稷,入閣拜相的大門就敞開!
在張璁的苦心運作下,一時間,“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但這件事的阻力,想想就大,打的更是在朝在野一群老臣的臉,尤其是首輔楊一清。
嘉靖八年的科考上,楊一清精心定的翰林名單,夾了不少自己的私人親信,結果被張璁一狀告倒。
但早在這之前,倆人矛盾就由來已久,張璁的做法,從來對腐敗零容忍。但楊一清圓滑得多,凡事留一線,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一來二去,矛盾就不少。而且楊一清自己,也十分不干凈,好處也不少收,比起后來的嚴嵩徐階,算是個老實人,但在清廉得天下聞名的張璁眼里,實在太過分。
以《石頭錄》的說法,張璁和楊一清的友誼翻船,根子上是楊一清的兩個毛病:1、送乘間引厚入院。也就是誰給錢,就推薦誰入翰林院。2、多循舊弊,用私任,多受饋遺。也就是受賄用熟人,安插心腹。這倆事按照老臣們看,都不算是個事,但在一心整頓風氣的張璁眼里,卻是個大事!
于是以張璁自己文集里的感慨說:入閣之后,想除舊布新,卻發現恩人楊一清,成了最大阻力,于是只好下狠心了。
結果倆人的爭斗,越發白熱化,互相攻擊極多,直到楊一清自以為是放了大招:指使親信言官(紀檢監察官員)王準和陸桀,彈劾張璁受賄!
這下可是朝野嘩然,因為多年以來,張璁挨罵極多,但從沒人敢說他經濟有問題。他做事夠狠,為官卻極清,清廉到什么地步?說個事你就知道。
吏部侍郎徐縉因徇私舞弊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為了逃脫法律制裁,他在一個大酒壇子里裝滿了黃澄澄的金子,外書“黃精白蠟敬壽”六字送給張璁。張璁當然知道他內心的小九九,先不點破,而等賓客聚齊,這才當眾敲開酒壇,公開暴露徐縉的行賄行為,由法司審問,依照犯罪證據的事實,將其削職為民。這件事干得干凈漂亮,朝野頓時震肅。
但在楊一清看來,就不信有不吃腥的貓,結果氣得張璁辭職抗議。嘉靖帝也十分認真查了一番,結果根本就是造謠。一番精心攻擊,放了空拳。楊一清也十分尷尬,主動辭官而去。
但張璁的性子就是這樣——得理不饒人,接下來的反擊,卻是一招致命:張璁收錢是造謠,楊一清的舊賬卻翻出來:解釋解釋宦官張永過世時,你收人二百兩替人寫墓志銘是咋回事?
這件事才是個要人命的猛料:雖說收錢是長期潛規則,但身為內閣首輔,收提督團營的已故大太監的錢,這不是收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根本不該收的政治問題!
這個猛料砸來,楊一清頓時晴天霹靂:官職被削,待遇被剝奪,老先生連驚帶氣,終于郁郁而終,臨終留下憤怒遺言:拼搏一生,卻為小人所害。
由于楊一清曾有誅殺劉瑾大功,于是這場爭斗落幕后,張璁也坐實了“小人”名號。但另一個事卻也必須說:在嘉靖帝準備嚴懲貪賄的楊一清時,還是張璁三上密疏,請求寬宥,說了一些“保全一清,實所以促使臣等也”的話,才得以保全了楊一清的家人。否則以嘉靖帝針眼一樣小的心胸,這么個犯忌諱的事,沒這么容易了斷。
全身而退
與楊一清的友誼小船說翻就翻后,張璁人生扶搖直上,嘉靖十三年(1534年),張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仕途已是巔峰。
但楊一清這場風波,也令張璁的名聲,越發的招罵。他銳意改革,革除弊政,但都是孤單英雄一般的向前,唯獨依靠的就是嘉靖帝的支持。但嘉靖九年以后,這個根本依靠,卻開始改變了:政治新寵夏言扶搖直上,開始與張璁爭權。正由于張璁多年得意,朝中根基極淺,且夏言才能不遜張璁,更有張璁沒有的獨家絕技:寫青詞,也就是起草祭天的文辭。對正熱心修道的嘉靖帝來說,那真是急領導之所急,于是張璁的權勢,也越發搖搖欲墜。
長期連累帶氣的工作,也令張璁身體大不如前。嘉靖十四年(1535年),張璁體疾,屢疏致仕,嘉靖不批準,“為之親制藥餌。”最后出現了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不省人事的險情。
這樣,嘉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同意張璁致仕回家調養。這之后,嘉靖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并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復任,但都因張璁身體不好未能到京。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張璁病歿于溫州,卒年65歲。嘉靖傷悼不已,下詔祭葬有加,贈太師,謚文忠。
而這種“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的悲劇,也同樣應驗在政敵夏言身上。夏言聯合嚴嵩趕走了張璁,但黑槍打趴下夏言的嚴嵩,而后卻倒行逆施,開創了明朝政治極度黑暗的“嚴黨專權”時代。
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我們愛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