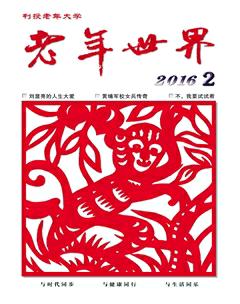盛開的民族雜技之花
漠中
雜技不是生活動態的簡單模擬,也不是表情的簡單外化。雜技是一種力的體現,一種極限的張揚。
我與雜技沒有直接關系,之所以涉筆雜技是心底纏綿著積久的縷縷絲線。因家庭環境,我自幼出入演出單位,除歌舞之外,包括雜技。耳濡目染雜技表演,漸漸熟悉了幾代雜技演員,也熟悉了他們所表演的節目,如:滾杯、滾燈、飛叉、蹬技、頂花壇、頂板凳、高車踢碗、單車踢碗、小跳板、大跳板、空中飛杠、空中飛人、硬氣功、輕氣功以及各種飛車。特別是踢碗、蹬弓、搏克、射箭,讓我感覺到內蒙古的雜技不同于其他地區,獨具蒙古民族特色。
早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前后,草原上雜技極少。當時有一家流動于城鎮和農村的家族式雜耍班子,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雜技。其實“雜耍”一詞,與雜技對比起來,有很大距離。舊詞典里解釋雜耍為:“北方人稱演幻術、踢毽子、說書、歌曲等各種技藝為雜耍”。《辭海》的解釋似乎靠近一些:“一部分游藝活動項目的舊稱。一般指某些活動性游戲,如投擲、套圈等。也專指雜技表演中手技和頂技節目,如扔球、打花棍、頂杯等”。
前些年我游覽和林格爾時,從漢墓壁畫中看見繪有樂舞百戲(雜技起始階段)的表演場面,說明內蒙古地區雜技藝術盡管極少,古代早已有之。
據說新中國成立前,在原歸綏、包頭、多倫諾爾、赤峰、海拉爾等地每逢夏秋廟會,有過馬戲班出現,他們用布簾圈住巴掌大一塊地方搭臺,敲鑼打鼓,表演絕活,賣藝掙錢。
1958年4月,中國雜技團一批教師和演員支邊來到內蒙古,從此,草原才掀開了雜技藝術有專業演出機構的歷史新一頁。
從1958年中國雜技團支邊內蒙古帶來傳統雜技,經幾代人努力打造,具有蒙古民族元素,色彩濃郁的民族雜技藝術走向中國雜壇。20世紀中葉主要節目有《花棍》《飛叉》《大武術》等20多項。值得一提的是《五人踢碗》不僅多次捧回大獎,還榮獲榮毅仁基金會雜技藝術一等獎,獎金110萬元。至此,內蒙古雜技演出節目上升至100多項,其中有28個節目獲國際國內金獎、銀獎、銅獎各種獎項近40枚。當時我在一家新聞單位以記者身份曾多次采寫成績突出的獲獎演員,進行宣傳。這也是我與雜技續接的情緣。
跨入21世紀之初,具有濃郁蒙古民族特色的《搏克勇士》《五人踢碗》《烏仁斯特牧其——柔術》等雜技節目和雜技劇《成吉思汗》《蒙古夢》《末代皇帝》《成吉思汗風》等形成舞臺藝術組合拳絕技。從1988年起始,內蒙古雜技團走遍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近30個國家、330多座城市。
內蒙古雜技團的品牌節目遐邇聞名。《四人踢碗》是以高車技與踢碗技巧結合,即從踢一個碗到踢五個碗,鏈式后踢、扇面型三對一傳踢,再于15秒內連踢15個碗,最后把奶茶壺、奶酪、壺蓋接連踢到對方演員頭頂,技巧性強,趣味性濃,博得觀眾陣陣掌聲。此節目于1990年在法國巴黎“明日”世界雜技大賽中奪得金獎。三名蒙古族和一名鄂溫克族女孩成為中國雜技史上第一次摘取國際金獎的演員。《五人踢碗》充分挖掘利用了多人高車踢碗優勢,重點突出5個人相互對踢的特點,技巧方面除完成各人踢4個碗、5個碗外,增加了丁字踢、交叉踢、鏈式后踢等集體技巧。結合蒙古族經典禮儀——銀碗、哈達,用盅碗舞表現形式精心打造。《蹬弓造型》以其高難度技巧動作,濃郁的蒙古民族特色,獲1992年首屆中國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黃鶴杯”銅獎。于1993年第十一屆朝鮮“四月之春”友誼藝術節上獲二等獎。《滾燈》是根據傳統節目《滾杯》發展而來的新節目,獲第二屆全國雜技的“銅獅獎”。《搏克勇士》以蒙古族搏克、雕塑藝術和雜技技巧為內容和特點。《射箭》成為雜技團創編的一個重點保留節目。《三人蹬技》于1993年12月意大利米蘭國際馬戲節上獲得銅獎。《烏仁斯特牧其——柔術》以小演員纖巧的身材和超軟度讓人聯想到草原上三月的小草,從熟眠狀態中經綿綿細雨沐浴,睜開睡眼,輕輕舒展手臂,緩緩破土而出,于陽光的愛撫下成長。
正如草原上三月的小草,內蒙古的蒙古民族雜技藝術受黨的陽光雨露,全方位創新打造,體現濃郁的蒙古族文化,似一枝不凋的鮮花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