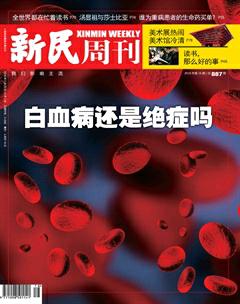“上海方案”,再進一步
黃祺
記者見到瑞金醫院血液科主任李軍民的時候,他正低頭忙著回復短信,對方,是陳竺院士。盡管這些年陳竺已經離開科研一線,從衛生部部長到現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崗位,但內心里,陳竺還是鐘愛著科研事業。陳竺曾在瑞金醫院工作近二十年,親身參與了“上海方案”從誕生到完善,直至被同行廣泛接受的過程。
要想理解“上海方案”在白血病領域的地位,首先要認識這種叫做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的疾病。李軍民主任告訴記者,1980年代中期他剛剛成為醫生的時候,APL的死亡率非常高,醫院收進的病人,可能搶救幾個小時就死亡了,特別是當不幸發生在孩子身上時,更加讓人惋惜。有了“上海方案”后,APL患者可以達到完全緩解率90%以上,完全顛覆了人們對這種白血病的認識。
但是,“上海方案”不能停滯不前,現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正在對“上海方案”進行優化,希望在更廣泛的患者身上,也能獲得同樣好的效果。李軍民教授告訴記者,短信中,陳竺院士正在詢問這一科研項目的進展。
瑞金醫院血液學學科,創建于上世紀70年代,盡管不是中國歷史最長的血液科,但談到白血病的治療,這里,是一面旗幟。在世界范圍內,瑞金醫院的“上海方案”,第一次讓外國同行聽到了來自中國的聲音,中國科研工作者為白血病治療開創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全國各地的患者慕名來到瑞金醫院,更高的水平意味著更重的擔當。
上海故事開篇
瑞金醫院2號樓,安靜地佇立在醫院一號大門的西北側,與周邊新建的醫院大樓相比,顯得樸素老舊。上到5樓,血液科住院部,仿佛時間穿梭,一些細節,透露出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氣息。狹窄的過道和護士站,飽經風霜的門窗、走廊盡頭醫生辦公室門外,堆放著柜子,醫生會議室里是扎實沉重的木椅、木桌,大概是因為太舊,木桌被雪白的床單覆蓋,醫生們就在蓋了床單的辦公桌上工作。
這里是瑞金醫院血液科最早的病房,白血病領域的“上海故事”就要從這里開始講起。
血液科奠基人王振義院士,今年92歲高齡。在瑞金醫院,王院士就像是“神一樣的存在”。這樣說,不僅是因為他開創了“上海方案”,還因為他迄今沒有離開科研工作。每周,王振義參加教學查房,讓年輕醫生“考自己”,醫生們把臨床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來,王振義回到辦公室,查文獻、找資料,過幾天,就把整理好的信息提供給大家。他用自己的方式,為白血病治療方式的改進出力。
談起白血病治療技術的進展,王院士有時候會感到著急,“按照我們現在的研究速度,要完全解決白血病問題,恐怕還要300年”。
王振義畢業于深受“西風”影響的震旦大學,熱愛古典音樂,一口流利法語、英語,畢業后進入瑞金醫院前身廣慈醫院工作。1952年,廣慈醫院細分出消化、心血管、內分泌和血液四個專業組,王振義開始在著名內科專家鄺安堃的指導下從事血液學研究。
“文革”動蕩中,王振義經常被調動,學過中醫,當過教師,直到1973年才重新回到瑞金醫院。59歲,別人“告老還鄉”“頤養天年”的年紀,王振義卻還泡在病房和實驗室中,嘗試別人從未嘗試過的設想。61歲,全反式維甲酸治療APL的第一個病例獲得成功,“上海故事”從此開篇。
作為靶向治療新方法,全反式維甲酸治療APL獲得成功,但現代醫學除了看到效果,還要求搞清機制。這個時候,陳竺、陳賽娟兩位年輕的學者,正在法國學習,王振義教授把弄清機制的任務,交給了他的這兩位得意門生。
“陋室”中的科研
王振義院士的辦公室里,只擺放了一張照片,就是他與陳竺、陳賽娟的合影。陳賽娟院士的辦公室,現在就在王振義院士的樓下,從師生到同事,三位院士在事業上合作三十年,為白血病研究領域留下一段佳話。
陳賽娟院士,從紡織女工“變成”的科學家,如果去掉科學家的身份,她就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人。兩年前記者采訪陳賽娟,她溫婉的態度、柔和的聲音和夾著上海口音的普通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堅韌與溫和是兩個共生的性格,陳賽娟恰好就是這樣的女性。
陳賽娟曾談及法國留學時的往事。與她一起攻讀博士的有一位美國同學,他們一起在實驗室工作。“我們中國人做事情很細致,但不太會講;這個美國同學很會講,說起來滔滔不絕。”陳賽娟在表達上吃了虧,美國同學接手了她做了一半的實驗。
為了完成實驗,陳賽娟到同在法國留學的陳竺的實驗室,繼續工作。“1年下來,我發了兩篇論文,這個美國同學一篇也沒有發。”
1989年,陳賽娟和陳竺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即選擇回國。但回到瑞金醫院,科研條件要比法國落后太多。記者看到的2號樓5樓走廊,曾經就是陳賽娟的“實驗室”。陳賽娟說起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細節。她把一個實驗設備放在走廊桌子上,調好溫度,等待培養結果。住院病人的家屬路過,看看好奇,手癢調了調溫度,“好了,這一天的實驗就白費了”。“陋室”中,瑞金醫院科研團隊取得碩果,1991年,瑞金醫院與其他三個中心共同發現了APL的核心發病原理和全反式維甲酸的藥物機制。
但到這個時候,“上海方案”還只是雛形。
一次參加國內會議,陳賽娟與哈爾濱的同行交流,這位同行告訴她,哈爾濱的張亭棟醫生,從1970年代開始用靜脈注射砷劑的方法治療急性白血病,獲得了很好的效果。砷劑,三氧化二砷,就是中國人熟知的砒霜,中醫有“以毒攻毒”的理論。
如果把全反式維甲酸與三氧化二砷結合起來,會不會帶來更好的治療效果呢?陳賽娟、陳竺夫婦帶領著團隊,開始驗證這個想法。
到2000年,兩藥聯合治療AP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PL成為第一個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上海方案”成型,并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可。

科研是沒有盡頭的,在實驗室里,探索還在日復一日地進行。陳賽娟說,針對APL高危病人的治療方法,已經啟動了多中心臨床研究,希望“上海方案”能夠在高危病人中間獲得更好的效果,希望能夠找到到治療其他類型白血病的方法。
更近一步,為了更多患者
已經取得的成績,是瑞金醫院血液科寶貴的財富,正是因為已經站上高峰,這里也被寄予更多期待,全國各地的病人慕名而來。
瑞金醫院血液科是全國最大的血液病診治中心之一,全年門診量達到10萬人次,年住院近6000人次。在有限的空間和人力條件下,血液科已經將工作效率提高到極限,但仍然不能滿足患者的需求。血液科主任李軍民告訴記者,再急的白血病病人,等待床位時間也要超過一兩周,慢性白血病等床位要按月計算,接近一半的病人沒法收治。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李軍民主任的主導下,瑞金醫院血液科聯合多家醫院,成立“瑞金血液病醫聯體”。“醫聯體”以瑞金醫院為基礎,聯合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新華醫院、中醫醫院、北站醫院、徐匯區中心醫院、楊浦區中心醫院,分別針對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征、移植后治療、免疫性疾病、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進行亞專科化特色分工。也就是說,患者在瑞金醫院診斷和首次治療后,可以根據既定治療和隨訪方案,到相應“醫聯體”成員單位繼續就診。
患者最關心的問題,是在“醫聯體”醫院是否能夠得到與瑞金醫院血液科同樣水平的治療。李軍民介紹,瑞金醫院血液科團隊將對病人實行全程管理,采取與瑞金醫院相同的治療方案,與成員單位開設聯合病房或聯合查房。
病人的信任就是醫生的責任,李軍民希望,無論技術還是硬件設施上,瑞金醫院血液科都能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療條件。2013年,血液科引進法國等離子清潔系統,開設“萬級清潔病房”,改善了危重病人感染的問題。
白血病患者接受大劑量化療后,機體免疫功能下降,極易并發各種感染,給患者治療帶來更大的風險。李軍民介紹說,萬級清潔病房的使用,可以提高危重病人的整體治療質量,顯著降低患者的感染發生率及由此帶來的死亡率,抗生素的使用也能降低30%以上。
在“醫聯體”成立儀式上,王振義院士對血液科的醫生們講了一段飽含深情的話:“我沒有多少時間在這個世界上,但我相信有這些年輕人攜手努力,血液病一定能夠更多突破。”無論在臨床治療還是科研中,年輕的一代血液科醫生,正在已有成績的基礎上,做更多的努力。
“上海方案”實現了部分急性白血病患者用靶向治療替代化療,但目前,低中危的病人、高危的病人,是不是也可以用靶向治療替代化療、或者實現部分替代?
李軍民主持的國家863項目“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優化治療”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軍民團隊對早幼粒的分層治療進一步優化,目前跟蹤的病例數已經達到800例,為了讓結論更有說服力,這項研究將積累病例1000例。李軍民告訴《新民周刊》,陳竺副委員長短信詢問的,就是這個項目的進展。
在跟蹤臨床效果的同時,團隊中的王侃侃研究員承擔的科研任務,從探究白血病驅動基因為基礎,揭示靶向藥物的機制,希望從基因層面給優化治療提供支持。
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占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的15%,其他更多類型的白血病,是不是也能找到新的方案實現治療方法的突破?李軍民帶領的團隊,也正在這一領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