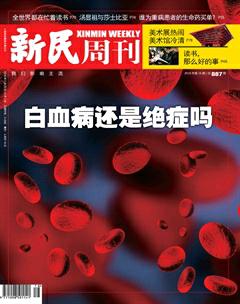施大畏談中華藝術宮
王悅陽
這是一串令文化人感到興奮的數(shù)字——開館三年半來,作為上海的“藝術博物館”,中華藝術宮已成功舉辦各類展覽100余個,展出作品逾18000件;接待觀眾近740萬人次。其中,節(jié)假日最高峰突破3.63萬人次。業(yè)內人士認為,前身為上海世博會標志性建筑中國館的中華藝術宮,如今已經(jīng)成為申城居民文化休閑的新地標。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華藝術宮的展示面積有6.4萬平方米,在規(guī)模上接近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法國奧賽博物館、英國泰特美術館等國際著名藝術博物館的水平。建設文化大都市,不再只是一個夢想,而有了值得依托的載體,值得奮斗的事業(yè)。
在做好傳統(tǒng)展覽的同時,中華藝術宮也已經(jīng)利用新媒體手段來豐富展覽形式,借助“數(shù)字博物館”項目推出了數(shù)字美術館網(wǎng)站,在線提供超過1.5萬幅作品的高清鑒賞和所有歷史展覽360度全景虛擬游覽。
以觀眾需求為首
在這三年多的時間中,中華藝術宮一直在展覽運行中努力。既滿足不同參觀人群的需求,又非常有學術追求。對此,中華藝術宮館長、上海文聯(lián)主席施大畏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從“海上生明月——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之源”、“東方之路——20世紀中國美術的探索”到“上海歷史文脈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成果展”“名家藝術陳列”……三年半來,中華藝術宮策劃推出了一批具備學術高度的長期展覽。這些展覽不僅一改以往國內美術館缺少常設展覽的空白,實現(xiàn)了美術館由“藝術畫廊”向“藝術博物館”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這些展覽是以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和世界美術史為學術定位的研究與展示,是堅持以“學術研究”傳遞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體現(xiàn)。
除了長期陳列展,中華藝術宮還策劃了不少特展來提升學術討論的氛圍。2014年,館方推出品牌系列展“同行——美術館聯(lián)合展”,圍繞“表現(xiàn)主義”與中國畫的寫意表現(xiàn)展開學術討論;2015年恰逢特列恰科夫誕辰100年,“同行展”聚焦俄羅斯最優(yōu)秀的油畫家,并通過“歷史的溫度:中央美術學院與中國具象油畫”等展覽探討中國油畫的發(fā)展脈絡,展示中國藝術與世界藝術之間的關系。據(jù)施大畏介紹,2016年的“同行展”正在積極策劃中,它將契合國家“一帶一路”戰(zhàn)略,集聚“一帶一路”國家藝術精品,打造專題展覽格局。
對于一個非營利性的綜合藝術美術館來說,平衡社會效益與經(jīng)濟效益始終是其運營工作中的艱巨挑戰(zhàn)。三年半的時間里,中華藝術宮在“把博物館帶回家”的運營理念下,以衍生品開發(fā)和配套商業(yè)服務獲取的經(jīng)濟效益,填補自身事業(yè)發(fā)展經(jīng)費上的不足。通過以館藏藝術品為基礎、自身文化定位為精神內涵的配套商業(yè)服務體系,自主新開發(fā)衍生品37類102款,取得了良好的經(jīng)濟效益。在此基礎上,又以社會效益為重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不遺余力地加強公共服務建設。通過自主創(chuàng)新具有文博特色的“中華藝術宮藝術服務企業(yè)標準”,為觀眾提供更加貼心舒適的觀展體驗,獲得了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的雙贏。
圍繞著“三年內建成亞洲一流美術館”的發(fā)展目標,在樹立“以人為本、以觀眾需求為首”現(xiàn)代理念,不斷創(chuàng)新現(xiàn)代文化服務內容的同時,現(xiàn)代化的體制機制與管理模式始終貫穿在中華藝術宮建設中。經(jīng)過三年半的砥礪,以“理事會決策、學術委員會審核、基金會支持”的三位一體的模式,已然在中華藝術宮的運行管理中踐行。通過由國內外著名藝術評論家、美術史專家、重要美術專業(yè)媒體代表和收藏家等組成的學術委員會,給予展覽、收藏和學術活動更為客觀和公正的標準。而由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為主管單位發(fā)起籌措的基金會,將具備前所未有的豐厚社會資本,為豐富館藏奠定堅實的基礎。
夢想的翅膀,逐漸高飛。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精彩的轉型
城市需要文化,文化大都市的建設是上海建設全球城市的必然選擇,是城市轉型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在黨的十八大對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新的部署下,2012年10月1日,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原址改建成中華藝術宮。自建成之日起,中華藝術宮始終秉持致力于對近現(xiàn)代經(jīng)典藝術的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和交流,以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zhàn)略思想為指導,以傳播民族和世界優(yōu)秀文化、文化育人為己任。
許多年來,施大畏一直有個夢想,那就是:有一天上海會擁有一座“奧賽宮”,即收藏展示近現(xiàn)代中國及上海美術的博物館。他和藝術界的很多同行,如中國美院院長許江等一起,曾為這一天的早日到來而不懈努力。總算,這個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這段極其重要的中華百年美術史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終于走出深深的庫房,展示在世人面前。
“上海美術館遷移至中華藝術宮之后,格局更大了,各項工作無論策展還是運營,都將圍繞‘中華兩字。雖為地方美術館,中華藝術宮卻是世博會中國館世界范圍影響力、集聚力的延續(xù)與傳承,是上海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起源地地位的體現(xiàn),也是該館展示中國近現(xiàn)代經(jīng)典藝術、開展國內外文化藝術交流等基礎功能的體現(xiàn)。”在施大畏看來,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建設,關鍵還是要解決文化民生。文化惠民是其中關鍵問題。把中國館變成中華藝術宮,核心在于通過這樣一個特大型的美術館建設,提升人的精神狀態(tài)和文化素養(yǎng)。從把最美的文化藝術交給普通公民這個角度來看,也許此舉能真正對上海的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起到一個“看不見的”支撐作用。
像中華藝術宮這樣規(guī)模如此巨大、由政府支撐的現(xiàn)代化藝術館,在中國也是第一個。對觀眾來說,這首先是享受,其次則是想象力。曾有“中國人缺少創(chuàng)造力”的說法,但是,如果建立起當代藝術的體系,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力自然會被激發(fā)出來。這不是臨摹,而是創(chuàng)造。 “我覺得,通過歷史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藝術,通過歷史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品位。”施大畏說,“王安憶的話讓我一直記著:很多很多歷史留下一點傳統(tǒng),很多很多傳統(tǒng)留下一點品位,很多很多品位留下一點藝術。因此,先有群眾進入美術館,后成國際文化大都市。硬件誰都有,但國人對尊重公共藝術空間的規(guī)矩似乎還不太懂。如果能拿出那么多好畫讓大家看看,來講品位、傳統(tǒng)和藝術,這樣對上海乃至全國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同時,這些藝術史上的代表性作品,還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藝術素養(yǎng)。更重要的是,百年歷史中,前輩藝術家勇于突破,勇于投身世界文明發(fā)展的大潮,極具智慧地將中國古代藝術的精神和精華,與時代潮流融合,創(chuàng)造出改變了中國藝術進程的偉大篇章——這些,如今都通過中華藝術宮呈現(xiàn)出來,必將給后人以啟發(fā)和力量。
多元的展覽
世界上哪座赫赫有名的藝術博物館,不是靠自身館藏吸引接踵而來的觀眾的?法國盧浮宮有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拉斐爾的《花園中的圣母》;美國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有梵高的《星月夜》、莫奈的《睡蓮》……上海的藝術博物館同樣不缺一流的館藏。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的發(fā)源地,這里匯聚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數(shù)百萬件各類藝術作品,僅上海市級美術單位收藏的中華藝術精品就多達3萬余件。然而,囿于過去有限的展覽面積,這些作品大多常年深藏庫房,只能借一些滾動的展覽,在少則10天多則一個月的展期里偶爾露個面,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如今,展示面積大幅提升的中華藝術宮,將使得上海豐富的藝術收藏資源形成長期陳列,作為展館的展示基礎。總計1000多件藝術作品,頭一次同時、并且長時間與觀眾見面。”在施大畏看來,常設的“海上生明月——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之源”,從清末以降的“海上畫派”到歷經(jīng)現(xiàn)代美術教育的文化啟蒙,從新興版畫的救亡圖存到商業(yè)美術的貼近生活,從新中國時期主題創(chuàng)作的宏大敘事到筆墨再造的時代新篇,展示的600余件近現(xiàn)代上海美術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凝聚著中國美術的精粹;而“錦繡中華——行進中的新世紀中國美術”則選取新世紀以來各個畫種的優(yōu)秀作品,真實而生動地展現(xiàn)中華民族的情感與智慧,中國當代社會的巨大發(fā)展與成就;“上海歷史文脈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成果展”更是難得一見的用美術作品留住上海城市的記憶;此外,藝術宮還為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上有著重要成就、為中國美術事業(yè)作出過突出貢獻、又將作品完整捐獻給國家機構的一批藝術大師,長期設立名家藝術陳列專館——賀天健、林風眠、關良、滑田友、謝稚柳、吳冠中、程十發(fā)成為第一批獲此殊榮的藝術大師。
文化是具有匯聚效應的。中華藝術宮將上海的藝術展示空間大幅擴容之后,全國、亞洲乃至世界許多著名美術館都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一批藝術珍品得以被請進來。開館伊始,來自大英博物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法國雨果博物館、美國惠特尼美術館等世界著名博物館和藝術機構的百件藝術珍品,就曾在33米層斗冠部分集中展示3個月,其中包括歐洲17世紀最偉大畫家之一的倫勃朗的肖像畫、羅馬時期埃及的大理石肖像雕塑等。之后,“米勒、庫爾貝與法國自然主義——法國奧賽博物館館藏珍品展”“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墨西哥當代藝術聯(lián)展”“法國三十年代美術館珍藏展”等多個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展覽,也展出優(yōu)秀經(jīng)典作品逾1.8萬件,逐步建立起中華藝術宮自身系統(tǒng)、科學的展覽體系。
這是一種眼光,更是一種胸懷。正如施大畏所說的那樣,“過去我們的美術館就是美術展覽館,現(xiàn)在我們要展示藏畫,學術部門需要有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的美術怎么梳理?怎樣才能從更為宏觀、更為深刻的角度,去發(fā)掘這段歷史過去還未被真正認識到的價值?目前,整個美術界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形而上的研究。而對當代藝術的發(fā)展,我們應該建立怎樣具有活力、能敏感地吸納社會創(chuàng)新力量和不斷自我更新的機制?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和社會各界熱愛藝術的人們共同思考和推動的。”
講好中國故事
上海,是一片東西方文化碰撞與交融的熱土,是一座國際展示與互動的舞臺。中華藝術宮濃縮與記載著上海這座城市在時空維度上的凝固之美,又見證與實踐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創(chuàng)造之美,風雨砥礪仿佛跳躍的音符,預示著輝煌必將來臨。中華藝術宮所呈現(xiàn)的是歷史與當下文化存在的精華,是一條反映中華文化與時代同行并不斷積累和延伸的現(xiàn)代強國之夢,這一絢爛夢想的早日實現(xiàn),將繼續(xù)激勵我們在追求文化藝術發(fā)展的道路上勇敢前進。
作為上海體量最大的公益性藝術博物館館長,施大畏說,他最看重的是,展覽怎樣在國際語境中講好中國的故事。
中華藝術宮這兩年有不少主題性對比展覽——比如“大師與大師——徐悲鴻與法國學院大家作品聯(lián)展”等。通過比較畢加索的作品與中國山水畫,可以獲得比單個展覽更多的訊息。對此,施大畏解釋道,中國的山水畫是散點透視,是意象型的,藝術家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求,將心中的山頭、溪流搬來搬去,搬到喜歡的狀態(tài)。如果你理解了這些,那么為什么不能理解畢加索把人的眼睛、鼻子搬來搬去,根據(jù)自己的需求自由組合呢?畢加索不就是把我們老祖宗原來三維的觀察方式變成二維的嗎?這就是一種觀察方式而已。兩相對比,我們不僅能理解畢加索,也能在世界范圍內理解自己特定的文化藝術現(xiàn)象。
“在這些對比的主題美術展覽中,相互交融的文化在今后成長的過程中會變成美術史,一部美術史也是一部社會發(fā)展史。”施大畏說,“中國文化面對整個開放的世界,處于同一個平面上,可以平行對話。不單繪畫如此,所有文化藝術樣式都能受到啟發(fā)。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神秘性變?yōu)榭茖W性,在世界的坐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有自己的文化理論體系,也會真正有文化自信。”
施大畏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jīng)歷了從窮到富的過程,中國現(xiàn)正在爭取成為世界強國。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我們到底需要什么?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除了科技發(fā)展,除了經(jīng)濟建設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歸根到底是一個人肯定生命和世界的態(tài)度,是一種價值觀。”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文化的多元,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能簡單地、指令式地傳達給大眾,而是要通過優(yōu)秀的文化創(chuàng)作和藝術實踐來實現(xiàn)。這里面就存在一個文化判斷的問題。”施大畏舉了一個例子——中華藝術宮開館時搞了一個展覽,是針對動漫,尤其是外國動漫在全國的盛行,策劃了一個上海電影制片廠美術電影的回顧展。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同志當時觀看了這個回顧展,很感興趣,但他看完后提出的問題讓施大畏陷入沉思:“現(xiàn)在的孩子們能看懂嗎?”施大畏明白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文化判斷是什么?”
“中華藝術宮開館三年多迎來了740萬的觀眾,但你給所有的觀眾提供什么,這始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構建公共文化體系,首先就是必須對公眾負責,這就是傳播和引領的責任。我認為,必須落在小處,落在實處。就是要把我們知道的故事,用最簡單、最樸素的方式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