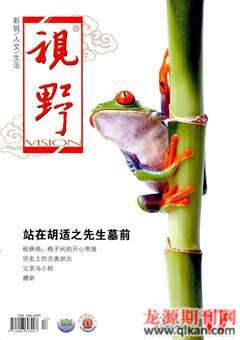最后一次愛你
舒 庸
他原本是一家油漆店的小老板,與妻子結婚三年了,有可愛的女兒,日子過得很幸福。
沒想到,在一次意外中,他的油漆店著火了,頃刻之間,店內價值十萬元的油漆和近萬元的現金化為灰燼。當他和妻子掙扎著從火海中跑出來后,均已被嚴重燒傷。幸運的是,他們一歲多的女兒在店著火前被鄰居抱去玩了,無意中躲過了一劫。他全身燒傷面積達90%,只有兩只腳上的皮膚是完好的,妻子渾身的燒傷面積也達60%。
躺在醫院燒傷科的病房里,他心如刀絞。住院才五天,就花去了六萬元。而這些錢,都是家人向親戚朋友借遍了,才籌到的。盡管社會上一些知情的好心人也多多少少地捐了一些錢,可這與夫婦倆治療燒傷所需的幾萬元相比,無異于杯水車薪。
他的家在農村,家里最值錢的那個小店也被大火吞沒了。而他療傷的金額實在太大了,是任何一個農村家庭都無法承受的。
他意識到,是該自己作出抉擇的時候了,與其兩個人一起死,不如集中錢救一個。他想,女兒還小,不能沒有媽……
于是,他開始請求醫生,停止對他用藥,讓他回家,而且事情的真相不能讓他的妻子知道。家人在一次次的努力籌錢失敗后,不得不含淚答應了,醫生也流下了無奈的眼淚。
就這樣,年輕的他突然要面對死亡,要永遠離開他深愛的妻子和女兒,他感到于心不忍,但又毫無辦法!他覺得自己被燒傷的不是肌膚而是心臟,但他又為用這樣的方式換回妻子的生命而感到欣慰,畢竟這是自己惟一能為她做的事情。
臨走之前,他向家人和醫院提了最后一個要求:再見自己心愛的妻子一面,再觸摸她一下,就一下。
重度燒傷的他躺在擔架上,顫抖著伸出手——那只燒傷的手,仿佛穿越了幾個世紀,終于放到妻子同樣傷痛的手上。咫尺天涯,這感人而揪心的一幕讓在場的人不忍看下去。
在他事先的安排下,妻子以為他只是需要轉院治療,而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分別。盡管如此,他還是止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在場的人全都掩面而泣。接著他異常平靜地安慰妻子:“不要哭,我會好的,再去開店,過日子……”
他的哭泣是他離開醫院的那一刻開始的,一路上,淚水就著血水,淋濕了整個枕頭。
四天后,他匆匆而去,年僅28歲。
他的妻子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她現在仍然不知道丈夫已經去世,而以為他“正在好轉之中”,她仍然期待著與他重新開始新生活的那一天。
(秦等星摘自《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