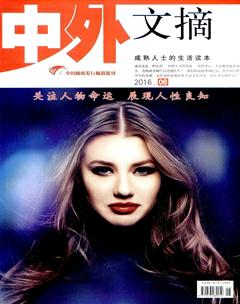我寫張志新
陳禹山 周華
1979年6月5日,經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審稿批準,光明日報發表長篇通訊《一份血寫的報告——記黨的好女兒張志新》,震動全國,波及海外。連續性報道近百天,編輯部收到讀者來信來稿達兩大麻袋。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盧云說,一個典型報道影響如此之大,在我國新聞史上前所未有。
編輯部收到來稿《為真理而斗爭》
十年“文革”,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干事張志新冤案是其中之一。1979年春,中共遼寧省委為張志新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
此時,我在光明日報記者部任記者。記者部收到遼寧《共產黨員》雜志的一篇題為《為真理而斗爭》的來稿,講的是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的事跡。記者部主任盧云把來稿交給我。我把稿子編了,交他審定。他看后,問:此稿如何?我說,題材重大,不足的是寫法上情輕理重,議論多了些,給人講大道理多了些。他說:“你去沈陽跑一趟,如何?”
這是撥亂反正、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重磅炸彈,事不宜遲。我接受了任務,第二天就上路了。
赴沈陽采訪
我到沈陽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共產黨員》雜志提供的《為真理而斗爭》的稿件。我們該如何辦呢?我打電話向盧云請示。他說,我們的計劃不變,另寫。
人民日報已見報,我們不能太遲。我改變采訪計劃,向遼寧省委提出要看有關張志新的檔案材料。在報社駐遼寧記者站的協助下,我當天就得到了張志新同事舉報她的信件、批斗審訊她的記錄、她寫的大量申明自己的觀點并為自己辯護的材料、中共遼寧省委對其案件的會議審批記錄、法院的判決書、行刑記錄,等等。所有這些材料都是原件。
閱讀案卷材料,我心靈極度震撼,了解了案件的真相和發展的全過程。接著,我去采訪張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兒曾林林,主要是要了解細節。細節,特別是動人的細節,對寫好一篇通訊,至關重要。
對曾林林的采訪,我事先擬定了要問的問題,如“媽媽在家時怎么生活,媽媽不在了又怎樣”;“媽媽是怎樣教育你的,對你的希望是什么”;“你最后一次見到媽媽是什么時候,是在哪里見的,媽媽對你說了些什么?”等。
此外,我還采訪了遼寧省委宣傳部張志新的同事和她的鄰居,我用了約三天時間,就基本上完成了通訊的采訪任務。
那一夜,我不知流了多少淚
在我寫《一份血寫的報告》時,從中央高層到地方基層仍有一股力量在肯定“文革”。報道該如何寫,是個問題。我遇到最大的難題是張志新被殺,是因為她指出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1958年以來推行“左”傾政治路線。我寫這篇報道時,毛主席雖已逝世,但當時關于毛主席的過錯是不能寫、不能說的。這是“高壓線”。當年張志新觸及的就是這條“高壓線”。
當時,全國正在批判林彪、“四人幫”。寫關于張志新的報道只能把矛頭指向林彪、“四人幫”。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是事實,但說張志新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被殺,不完全是這么回事。記者報道說假話是天理不容的。我冥思苦想,最后決定在通訊中寫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后面加上一個“此外”:“此外,她(張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的同時,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對自己的領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表達了她對自己的領袖的熱愛和深厚的階級感情。”
寫上這段文字,關于張志新死因的報道也就“全面”了,但還是不那么真實、客觀、公正的。因為事實主次倒置、本末倒置了。
寫這篇通訊,加上乘火車往返于北京沈陽,共用了五天時間。在這五天時間里,我腦子里就只有這一件事。我白天黑夜都在看案卷材料。我悲憤,我痛苦,也感到內疚,感到張志新之死也與我們新聞界有關。我寫了一夜,天亮后即把稿子送遼寧省委審查。那一夜,我不知流了多少淚,椅背上搭著擦淚的毛巾,天亮時是濕的。
寫稿前,我已準備了“預制構件”。每次采訪后,我及時把那些感人的情節或細節寫出來,像建造房子那樣,制成“預制構件”。寫稿時,我把“預制構件”整塊搬到合適的段落上去。這樣不但進度快,且效果好,因為“預制構件”的文字是在感情熱辣辣的時候寫出來的,是感動了我的,自然也就會打動讀者。例如,我訪問完曾林林后就寫下:“一天,女兒放學回來,鄰居王阿姨一把把她拉到自己家里,說:‘街道搞衛生在噴藥,你不能回家!正在這時候,有幾個人在張志新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已被逮捕的張志新也被押回家來。她向押送人員提出,希望讓她見見兩個孩子,但遭到拒絕。王阿姨止不住地掉淚,到門外張望了一會兒,對張志新的女兒說‘林林,你快到你家門前那幾棵樹下去!林林向自己的家走去。這時,她看見了媽媽戴著手銬,被幾個人押著從家里走了出來,推上了停在門前的吉普車。吉普車開動了,林林跟在后面追。車開遠了,消失了,林林坐在地上號啕大哭,呼喊著:‘媽媽!”
《一份血寫的報告》這個標題,得到了新聞界的普遍認可,這是記者部汪波清同志提議的。標題猶如文章的眼睛,有個好標題,至關重要。
一直在連續報道
在以后的近百天連續報道中,我又采寫了長篇通訊《走向永生的足跡——張志新的成長歷程》,介紹張志新成長的社會環境、進步家庭的影響、童年艱苦生活的磨煉、新社會對她的熏陶,特別是黨對她的培養教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她的哺育,加上她自覺地改造自己,使她逐漸成為一個有崇高理想、善于思考、善于明辨是非、勇于捍衛真理的共產黨員。
1979年8月間,我還采寫了《張志新沉冤昭雪經過》的調查報告。由于報上刊發了有的學者提出“要改造那追求真理要以流血犧牲為代價的環境”的文章,觸及了當時的底線,調查報告因而未能發表。
2000年我退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寫《世紀奇冤——張志新冤案全記錄》,這也是當年關于張志新報道的繼續。我寫這本書,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后來進入官場(作者1990年任深圳南山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的感受,我感到我們社會產生張志新冤案的那種環境和條件仍然存在,那就是我們民主與法制方面的缺失。
完稿后,我請袁庚同志為第一讀者。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仔細讀完全稿,在書稿一些段落的空白處,寫上:“妙”、“妙極”、“精彩”、“精彩至極”等批語。他說,這是“世紀之作”。
另一位讀者是中宣部離休干部田丹。他是我當年在北京新華社工作時的頂頭上司,離休后仍在中央有關部門參與審查稿件工作。他說:“《一份血寫的報告》,血跡斑斑。《世紀奇冤》鮮血淋淋。讀了令人悲憤,催人淚下,發人深思,深深感到加強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此書寫的是歷史,沒有錯。但現在出版有困難,我想,也許再過些年,這本書是有可能出版的。”
香港多家出版機構曾找我,有的還開出高價,我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我不想搞“出口轉內銷”,我把書稿作為遺產交由兒子保存了。
我可以無愧地告訴讀者:我已竭盡所能,把關于張志新冤案的真相,真實、客觀地告訴世人。待《世紀奇冤——張志新冤案全記錄》面世之日,才是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時。我深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摘自《中外書摘》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