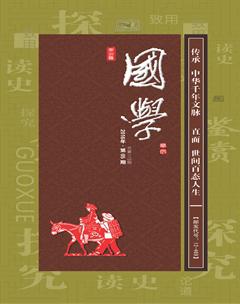蘇格拉底與孔子
許錫良
西方的教育傳統與中國的教育傳統的差別,其實早在柏拉圖對話錄里的蘇格拉底與《論語》里的孔子那里早就奠定了基調。蘇格拉底的對話與孔子的語錄就是最好的標志。而且,這個差異至今仍然無法溝通。
中國的教育注重記憶與背誦,總感覺如果學生沒有記住與背誦出一些什么東西,那么教育就是空白的。因此,我們總是容易見到有形的東西。一些大學畢業生拿著自己的聽課筆記去找工作,以為這些東西就是所謂的大學教育了,結果發現在大學里老師講授的筆記,遠不如一些網絡資料說得全面周密詳盡,因此深感讀大學幾乎等于是零。這就是一種記憶與背誦的教育觀念在起作用,他們不知道真正的教育是一個過程,你的生命在這個過程中的體驗、感悟與升華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一個人也很容易發現,一個人吃了一輩子的飯,結果只要一餐不吃,肚子里仍然是空空如也,你能說這一輩子的飯白吃了嗎?所吃的飯要化成你自己的身體的營養才有價值,同樣經典與知識只有在有利于促進你去發現問題,促進你的思考的時候,這些經典與知識對你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讀書似乎純粹只是為了考試,為了表演,為了在人前展示,為了能夠呈現的及時效應,這就是我們應試教育的悲哀。
-1-
中國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夠及時地呈現出一些可以讓人看見,可以演示的東西,那么要說服中國人說這個教育是優秀的教育將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的一切教育改革都強調可操作性,要見到實效。那所謂實效又是什么東西呢?就是背誦與記憶的東西的數量,也就是海量的背誦與記憶。中國古代的私塾幾乎只有一種教育方式,那就是把《四書》《五經》拿出讓學生不加理解地反復背誦,甚至要求倒背如流。這樣,家長才放心,政府官員才放心,教育才算是有了成效。但是,如果按照蘇格拉底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對話,探討,沒有什么格言警句需要背誦,而且弄了半天連個標準答案都沒有。這如果放到中國,是沒有人會答應的。人們將會責問你,你究竟是在讓孩子干嗎?這不是誤人子弟嗎?可是,西方人非常清楚,這個過程才是最好的教育過程,因為這個過程讓孩子學會了探究,培養了探究意識與對未知領域的濃厚興趣,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樣的教育即使強調閱讀經典,也只是為提出或者解決問題而來的,而不是像農民的倉庫里的糧食那樣僅僅用來儲備的。其實,中國教育的背誦與記憶雖然容易檢驗出“成果”,但是卻很容易傷害學生的其他的興趣與愛好,容易將他們最重要的思考能力與想象力破壞。
而蘇格拉底法,則最容易培養學生思維的樂趣,探究的樂趣,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學會思考,掌握探究的方法。這樣的方法與方式很容易被應用到生活與生產中去發現問題與探究問題。一種不會培養學生問題意識與探究意識的教育,是不可能會有什么創造力的。
-2-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中國人常常以背誦與記憶的數量作為教育的成果,可是,他們既不會思考,不會提出問題,也極其缺乏想像力與創造力。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有“四大發明”,而且這“四大發明”幾乎與我們的正統教育都無關。但是,蘇格拉底還在世的時候,他的學生柏拉圖已經表現了非凡的創造力,并且成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蘇格拉底奠定的教育基礎是一代勝過一代。孔子奠定的教育基調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敢于面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中國人,應該不難看到這個最普通的事實。
我們總是害怕不能夠抓住一些實在的東西,就像一個農民一定要看見稻谷長出才會放心一樣。按照這種理解方式,如果一個人把飯吃下去,不是變成滋養身體的營養與排泄物排出,而是必須仍然存留在肚子里,讓人摸得到,而且必須始終在肚子里有一副鼓鼓的樣子,這才讓人放心,才覺得踏實,那么我們必然將要鬧出毛病來。知識在人的頭腦里如果沒有被及時理解與消化,也是要妨礙人的正常思考的。但是,我們現在仍然是誦經、國學,背誦、記憶這一套。我們的教育似乎抱定了這樣的宗旨:盡快將孩子的大腦填滿,決不給孩子的生命有片刻喘息的機會。
可憐我們的學生生來是為文本而活的,我們的教育就是要把學生引導到文本那里去,其實,真正的教育是把文本引導到學生的生命里去。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前者,學生是為本本而活,后者的本本是為學生而存在。學生記住一些東西的目的不是為了考試時順便完成文字搬運工的作用,而是因為學生想過了,做過了,體驗了,最后無意中他們記住了,“記住了”恰恰是在想過了,做過了,體驗了之后的副產品,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副產品,這些東西有時不如忘記了的好。
如果我無意中記住了一個路牌,那不是因為我要特意記住一個路牌,而是因為我要找到自己的路。如果我記住了一個知識,那不是因為這個知識是值得記住的,而是因為這個知識是我提出問題的依據,或者是我解決問題不可缺乏的材料。經典、知識的意義正如這個路牌的作用,路牌不是人們用來背誦的,只是用來給人指路的,一旦路找到了,這個路牌被忘記也沒有什么關系。真正的思想智慧常常不是有形的結果,而是無形的過程,不是現成的結論,而是一個問題的意識,不是文字上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蘊含在文字之間,蘊藏在字里行間的那些靈動的思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愛因斯坦的警告:只有將課堂上所學的東西完全忘記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這個話是蘇格拉底對話過程的絕妙概括。
-3-
我想教育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思考比記憶重要,想象比背誦重要,問題意識和發現意識比背誦與記憶知識重要,批判能力比模仿能力重要(模仿在兒童階段也是一個不缺乏的學習方式,特別是在行為規范方面。),而創造能力才是最終目的。記憶太多,總是想到別人的陳規陋習,而恰恰是忘記了自己的生命,忘記了思維與獨創才是生命的本性。兒童的見解總是不同于成年人,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還沒有被知識垃圾填充過多,外行轉行,常常比較容易發現新問題。這些都說明思維能力、思考方法,想象力與創造力是在記憶不是太多的地方才能夠閃現。讀書是為了促進思考,而不是為了記住。
我沒有聽說蘇格拉底讀過什么經典名著,我只知道他的學生一旦沾上了他,并且在他的產婆術的追問下,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追問問題所在,而且沒有盡頭,這足以促使后人對前人留下的問題躍躍欲試,代代相傳,這是蘇氏教育下,一代勝過一代的重要原因。但是,孔子在有生之年口口聲聲“五十學《易》”,《詩三百》,“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周公是他的人生榜樣,周禮是他的社會理想。孔子沒有給后人留下思考的余地,更沒有留給后人可以繼續探索的問題,只是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復背誦的格言警句,與一個高不可攀的圣人形象,還有一個遠在孔子之前五百年的周禮制度,與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知識態度。
中國傳統教育的悲哀莫過于此,我們的教育始終不能夠突出重圍,其根源也在這里,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社會也無法走出權威主義與專制獨裁,也是在這樣的教育奠定的心理基礎上得以幽靈不死,死灰復燃。現在看來,我們仍然沒有突破這樣的教育方式。
我們中小學教師從崇拜孔孟,背誦經句,復興國學,再到崇拜現實中的各種各色的所謂的“教育名人”,把學習當成背誦與記憶,把探索當成簡單模仿,把反思與批判看成是“罵人”與“吵架”的不和諧之音,把想象看成是胡思亂想,浪費時間,把創造看成是調皮搗蛋。天才人物的被扼殺,雖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尤其以今天感覺令人痛心疾首。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我們的差距,看到了后果的嚴重性,但是,我們仍然無法有所突破。
-4-
選擇蘇格拉底還是選擇孔子,這其實是選擇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但是,孔子影響下的中國人與中國教育,無疑決定了中國人與中國教育的選擇。我們總是被自己的投影所形成的恐龍式的巨影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