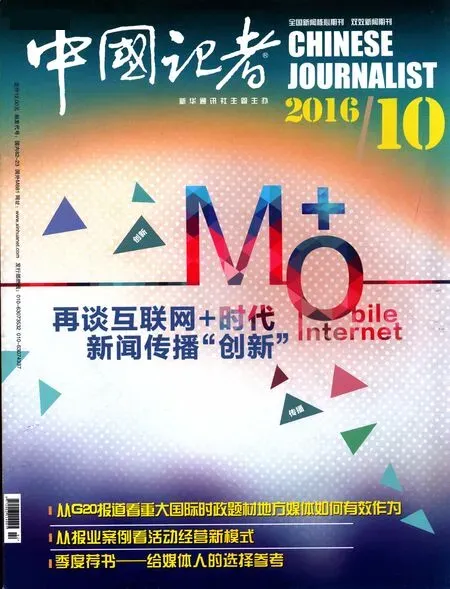地方媒體記者有可能“跨國采訪”常態化嗎?
□ 文/劉功虎
地方媒體記者有可能“跨國采訪”常態化嗎?
□ 文/劉功虎
在種種局限條件下,“跨國采訪”很難做到采訪人每次都跨出國門進行采訪。本文結合作者自身的實踐,重點介紹作為地方傳統媒體的記者,如何在不出國門的情況下,實現跨國采訪的常態化,分享經驗,歸納得失。
長江日報 深度報道 跨國采訪 人物訪談
在全球化和全媒體時代,跨地區、跨國家采訪是媒體有追求的表現和保證“獨家”之道。但限于國籍和語言障礙,更局限于采訪成本和時間效率的制約,媒體記者不可能動輒走出國門,報道需求和現實困難常常構成一對緊張的矛盾。如何打破國界和語言障礙,在無法面對面的情況下,準確快速找到“地球任何角落”的采訪對象,實現采訪目的,需要切實研究方法和技巧。
《長江日報》在2012年初推出《讀+周刊》深度報道系列,每周一期,至今已有五個多年頭。該刊以富含思想含量的新書為抓手,話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外交、地理、軍事、藝術等等,內容幾乎無所不包,而采訪對象每每為國際、國內一流的、前沿的名人名家,或者學術泰斗。按照報社要求,每次報道需要采訪到這些名人名家或熱點話題人物本身,一線記者要與之進行高質量的對談。我有幸參與了這個周刊的創刊,并一直擔任主力記者至今,數年下來采訪到王蒙、張維迎、林毅夫、秦暉、彼得·海斯勒、理查德·道金斯、陶涵、拉納·米特等近百位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此外,涉及到某些重要的日常文化新聞生產,我也會遇到需要跨國采訪的情況。
如此頻繁的跨國采訪,我沒有一次是親身跨出了國門進行采訪的,每次都要面臨種種“局限條件”。所謂“局限條件”,就是指身在國內,無法與國外受訪對象見面的情形下,記者尋找、接觸進而實現采訪所能利用的現成一切通訊工具或渠道,包括熟人網絡、中介和通訊工具等。我在《讀+周刊》的采訪實踐中,跨國采訪工作量約占到全部采訪量的1/5,均是在中國國內完成。《讀+周刊》的基本運作方式是以新書為載體,圍繞一個核心話題專訪新書作者,因此出版社往往是最重要的中介,也省卻很多尋訪作者的麻煩。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某作者由于名氣太大,或者事情太多,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辦法幫忙“搞定”,這時候就需要記者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手段。還有的情況是,新書過氣,出版社沒有興趣圍繞某書營銷,而我們卻因為話題需要想尋訪到這位作者,也往往需要開動腦筋,自己想辦法找人。再就是《讀+周刊》的話題設置,常常并不以新書為依托,而完全是新聞熱點導向,這樣要找到某位名人名家也需要靠記者自身的智慧和努力。
下面我結合不同情況,介紹一下相應的應對辦法,并嘗試做一點理論總結,分享自己的經驗得失。
一、找人工具不在新而在有效
采訪案例1: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偉”,當時身在埃及的美國記者)
見報時間:2012年3月6日
報道標題 :《我在正確的時間去了正確的地方》
采訪案例2:宇文所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漢學家)
見報時間:2014年7月8日
報道標題:《美國人距離唐朝不比中國人遠》
跨國采訪,首先的難點是尋找到受訪對象,而不是語言障礙、通話成本、時差等等。我們在國內構筑的“熟人網絡”作用十分有限,如果出版社這個中介無從依賴,一切就都得自己“摸著石頭過河”。好在互聯網時代,可用的現代通訊工具很多。我這里先介紹一個案例,就是5年前采訪彼得·海斯勒所用到“組合式辦法”。
彼得·海斯勒是一位美國年輕人,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后來到位于中國涪陵的長江師范學院當教師,并寫出《尋路中國》《江城》等觀察中國現實狀況的書籍,隨即從中國消失。他是那種居無定所、四海為家的典型美國人,離開中國后其書在中國大火,十分暢銷,釀成新聞熱點。很多國內媒體記者試圖采訪到他本人,但是因為難于“打撈”而放棄。
正是在這種新聞背景下,《讀+周刊》希望找到這個美國人,好好聊聊他推出三部曲的動機、艱難過程以及怎么看待自己的“走紅”。時間很緊迫,而人在何方都是個問題,任務到了我頭上,卻感到茫無頭緒。苦思無果之后,我通過重慶的114查號臺,撥通了長江師范學院的總機,那邊是一位女士接的電話,她告訴了一個彼得·海斯勒教書時的同事、《江城》譯者李雪順的手機號。我如獲至寶,立即打電話給李雪順。當時李雪順與彼得·海斯勒也失去了聯系,只知道后者去了埃及,具體去向不明,所幸他依稀記得海斯勒的一個電子郵箱名,于是給了我。我向這個郵箱發去信息,連續一周未獲回復,我用簡單的英語催問了幾次,對方才回復說弄錯了,他不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掉頭又與李雪順聯系,他才發現自己記錯了郵箱名,又給了一個郵箱。最終我與彼得·海斯勒成功建立起直接聯系。
采訪到彼得·海斯勒,推出一篇有影響力的報道,是我加入《讀+周刊》的首次出擊。該報道是該周刊創刊的重磅作品。那年還沒有微信,微博也剛興起不久。我最開始想起利用的“打114”,也許現在很多人看來很蹩腳,絲毫沒有技術含量,“怎么好意思拿出來說”。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個看似通訊發達、新興媒介遍地的時代,千萬別忘了這門“古老的”工具。
采用類似手法,我還采訪到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是資深的美國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化有很深的研究造詣,著有《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詩》等7部重要專著。2014年夏天我聯系采訪他的時候,他的新書已經過了營銷期,出版社也無法幫忙牽線。我通過網絡“人肉搜索”,搜到他在中國有一位好友、武漢大學教師榮啟光,然后撥打武大總機電話,輾轉找到榮啟光的聯系方式。通過榮啟光,我與宇文所安的夫人、他的哈佛同事、中國人田曉菲建立起直接的電郵聯系,最終寫成長篇報道《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美國人距離唐朝不比中國人遠》。
二、合法窮盡“人肉搜索”
采訪案例3:旅法作家沈大力、華僑書商潘立輝和法國漢學家班岜諾
見報時間:2015年8月11日
報道標題:《“太史公曰”變身法文歷經百年》
“人肉搜索”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下,幾乎就是一個貶義詞。原因當然很多,主要還是隨著網絡的興起,每個人都介入網絡生活,難免泥沙俱下,引發一些過度搜索、從而過多窺私并非法暴露他人隱私的現象。但是客觀來說,“搜索引擎”、網絡工具永遠是中性的,它只是人類的工具,就看怎么利用和掌握。這里借用這個詞是想表達:一個優秀的記者,為了完成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定要善于充分利用互聯網工具,前提是采訪目的正當,使用手段合法。在這樣的前提設定下,記者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使出渾身解數,盡可能窮盡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所能抵達的角落。

我在2015年中做了一期《讀+周刊》訪談專題,一口氣采訪了三個身在法國巴黎的人。事情原委大致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譯注五卷本《史記》百年后,當代法國漢學家班岜諾教授補譯完“列傳”部分,《史記》在法國全部出齊。我從澎湃新聞一則轉載的簡短消息上得知了訊息,覺得其意義非凡,值得深入報道。但是我以前從未做過有關法國的報道,人脈全無,語言更是不通,接到采訪任務后感覺完全無從下手。
最開始我習慣性地在網上隨意瀏覽搜索,毫無收獲。然后我決定把視線收回,回到澎湃所轉載消息的源頭上去,那是一家當地華僑開辦的報紙——《歐洲時報》所報道的,作者署名沈大力。我用谷歌搜索沈大力的訊息,得知他是生活在巴黎的作家,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法文教授。
搜索到這一步,還是無法與當事人直接聯系。接著我又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歐洲時報》,竟然有這家報紙的中文ID!而且,澎湃的消息正是從這個ID轉發,沈大力文章的最初鏈接是由這個ID提供的。然而,如果只是到這一步,我仍然無法與當事人取得直接聯系。我需要一個電話號碼。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給《歐洲時報》的新浪微博發了一封私信,詳細介紹自己的采訪意圖和要求,并附上自己的郵箱和手機號碼。
大約在當天傍晚時分,我的電子郵箱就收到了一封郵件,是《歐洲時報》主編董純女士發來的,原來她是沈大力先生的夫人。她向我提供了法文《史記》的出版人、柬埔寨華人后裔潘立輝先生和漢學家班岜諾的聯系方式。
也許在一些“人肉搜索”專家那里,我的搜索能力還只能算是“菜鳥”級別,甚至未入門,但是我要說,只要達到了采訪目的,我就是一個“成功者”,無需妄自菲薄。我所使用的“人肉搜索”盡管還不夠曲折,戲劇性不強,但卻已經是我使用通訊工具最繁復、利用最充分的一次:搜索引擎、微博、電郵和電話,各種手段齊上,最后完成了報道任務。有評價認為,在這個題材上我比國內所有同行都走得更遠、談得更深。
三、調動全部的想象力
采訪案例4:沈睿(旅美學者、詩人)
見報時間:2015年1月30日
報道標題:《余秀華爆紅過程還原》
采訪案例5:理查德·道金斯(英國牛津大學教授)
見報時間:2013年6月18日
報道標題:《人不是從猴子進化來的》
新聞采寫的全程均需要調動人的想象力,尋人找人也不例外。它不是一項純粹的技術活或者說體力活,指引我們尋人的是想象力。
2015年初,詩歌《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睡你》爆紅,其作者余秀華迅速成名,上百家媒體涌向湖北荊門余家。她的走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炒作?《長江日報》以此為選題方向,分派我展開調查報道。我趕往荊門余家兩趟,一有空就在網上爬梳細節。由于絕大多數媒體均被余秀華特殊的身世和才華所打動,接下來都致力于報道余秀華“積極向前”的一面,報道她的“現在”“現場”為主,而介紹她成名“前傳”的文字多為網上抄襲,往往寥寥數語帶過。其中把她推向封口浪尖的幾個人則甚少關注,其中一個詩評家沈睿,因為遠在美國亞特蘭大,更無一個記者采訪她作為“推手”的動機。
我發現這一被廣泛忽略的線索之后,通過一個在蘇州打工的“業余詩人”王小歡,加上了沈睿的微信。不采訪不知道,一采訪我豁然開朗,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沈睿根本不認識余秀華,也不認識《詩刊》的編輯劉年,她只在幾天前才在天涯的一個論壇上讀到余秀華的詩歌,并為這個女人的詩所深深感動。沈睿說:“怎么會有炒作?誰在炒作?我跟他們任何人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當跟沈睿在微信和電郵你一言我一語交流的時候,我深深慶幸自己多留了一份心眼,多開動了一下腦筋,多動了一下手腳,而不是停留在浮躁的以訛傳訛中。這個世界除了有很多現實的人,也還有一些真正的詩人。我在調查的時候,對人事關系的想象力幫助我走進了原初的風暴眼,抵達了事件的真相。
在采訪英國生物學家、科學哲學家道金斯受阻時,我也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道金斯由于是“學術明星”,時間十分稀缺,即使他的著作出版中文版,他也不肯配合中國的出版社做宣傳,因此媒體要想約訪他十分困難。我在漫長的等待后想到一個辦法,就是聯絡一個叫“張宏斌”的中國民間學者、音樂愛好者,他曾留學英國,是道金斯的門生。我們經常同時出沒于一個論壇,他偶爾會推介道金斯的學說,但不屬于那種活躍的網絡人士。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給張宏斌的新浪微博發了私信。沒想到他這個人很熱情,信用很好,在他的幫助下我最終采訪到道金斯,屬于國內獨家。
坦率說,我是在無意和無奈中“想”到這位中介人的。在我接觸的海量資訊中,在我所掌握的蛛網般的人際關系里,張宏斌是一個很弱的信號。如果我從未曾“想”過他且及時抓住頭腦中這個意向,我可能至今仍與道金斯無緣相識。
四、“6個人原理”揭示的是希望而不是難度
下面脫離具體案例,談談跨國采訪的一個關鍵疑問: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一個人,是不是一定都能找到?
這無疑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大眾話題。有意思的是,我相信目前可能還沒有誰能夠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因為很容易找到反例來否定特定的論斷。在我看來,它更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是一個抽象的疑惑。“記者”這個職業為我提供一種便利,可以來反復驗證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
現在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或聽說過“6個人”原理。這是一個通俗提法,理論化的表達是“六度分隔理論”,1967年由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提出。這個理論用通俗語言描述就是:“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
讓我們來假設:如果某人認識100個人,而這100人中的每一人都認識另外100個不重復的人,那么一個人經過一層間隔就可以和100x100=10000個人認識。如果存在六層關系,并且每一層都不重復,那么最終會覆蓋1萬億人口。這就是六度分隔理論所展現的巨大能量。
但在社會實踐中,每個人都很難發現這種巨大能量的存在。“六度分隔理論”說明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弱紐帶”關系,但要深究,它就可能發揮很強大的作用。通過弱紐帶,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相近”。要指出的是,六度分隔不是一個定理,也不是一個猜想,而是一次實驗的結果。一般而言,它不針對整個地球上的社會網絡,也不針對中國社會網絡,并不能指導我們找到“任何一個人”。此外,“6”也不是最大數目,而是平均數目。
這個理論在很多情況下,對很多職業、很多個人來說,作用不大。但是,很幸運的是,“記者”這個行當,一定要充分認識這個理論的威力。“6個人”原理當然不是說找人很容易,而是作為一個記者,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找人難度的極限何在。這個原理揭示的不是難度,而是希望。一個記者的信心和毅力無疑十分重要。
理論盡可簡潔,現實足夠復雜。我在采訪中最深的體會是,不少約訪尋人,所經歷的中間環節遠不止6人,但是最終總能找到這個人。迄今我還沒有敗績。每次成功聯系到受訪人之后,我就會產生世界很小的感覺;但在那之前的漫長摸索的過程中,又感覺有太多的墻和坑。因此,對于找人的結果,我們盡可以保持樂觀,但在尋找的過程中,一定要有耐心、細心和專心,要有一顆強大的心臟,同時方法要盡可能合理、實用、高效。
(作者是《長江日報》文化新聞部讀書周刊業務主編、記者)
編 輯 梁益暢 46266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