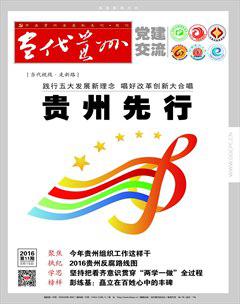黨性修養的途徑與態度
一個人在職場與社會中要想獲得成功,需要能力、知識、智慧的積淀,但最終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修養。個人成事創業需要職業修養、綜合素養,作為黨員干部還需要有黨性修養,唯有黨性修養,才能實現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言,不同的階級和政黨皆有黨性。但是,世界上很少有政黨像馬克思主義政黨那樣強調黨性,在眾多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又很少有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強調黨性。中國共產黨是從革命勝利中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始終強調堅持黨性和黨性修養,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決定的,也是中國共產黨承載的歷史使命決定的,更是迎接“四個挑戰”、克服“四大危險”的現實要求決定的。
共產黨員的黨性鍛煉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是實現黨性的根本途徑,包括理論修養、政治修養、道德修養、紀律修養、作風修養。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修身養性的必修課,是共產黨人的心學。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主要有三個基本途徑:
第一,黨性修養繼承了古代中國的“心律”文化的精華,產生了自我批評的個人修煉途徑。在“心律”(自我約束力)與“法律”(外部約束力)的關系中,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強調“心律”的優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先失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論語·衛靈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把“老莊申韓”單列為“老莊申韓列傳”。據他的研究,申不害、韓非等法家的思想乃是來自老子、莊子等道家的思想,所以司馬遷應該是中國學術史上率先提出“法律”來源于“心律”、“心律”大于“法律”的學者。毛澤東曾經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表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可以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中來,而傳統修身文化的精華也可以納入到黨性修養中來。中國共產黨從我國古代的“心律”文化中吸收了許多有益的智慧,變成了黨性修養的思想源泉,如黨的領導人經常引用古人講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等無數箴言。
第二,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矛盾論基礎上通過黨內正確、原則的思想斗爭,在政治生活中實現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即在個人“修煉”的基礎上增加了組織的“修煉”的內容。這種修煉超越了儒家、佛學的唯心主義式的個人修煉,把個人修煉和集體修煉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實現了黨性修養的集體途徑,而個人修煉與集體修煉相結合的武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三,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基礎上形成了在客觀世界改造中改造主觀世界的途徑,在黨內培養了一大批黨性修養極強的黨員干部。延安時期,有一位“紅色技術專家”張協和,一身正氣,始終堅持黨性修養,到了晚年他總結出自己的座右銘:“做人,對有的事情要感興趣,對有的事情要不感興趣。比如追求權位、物質享受是無止境的,你的興趣若在這方面,就苦惱一輩子。如果你對求學問、對為人民服務很感興趣,你將會永遠樂觀。只有不計權位、享受的人,才是真正做學問的人,才能學有成就。”因此,堅持實踐哲學,就是堅持密切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克服本本主義與經驗主義;就是堅持知行合一、克服人格分裂。
這三個途徑必須始終統一在唯物主義的態度之中,即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列寧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的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指出了黨性修養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的重要性。周恩來同志1943年在重慶紅巖為自己制定的“七項修養要則”中明確指出“健全自己的身體,保持合理的規律生活,這是自我修養的物質基礎”,指出了健全的身體是黨性修養的前提,強調了辯證唯物主義態度的重要性。(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