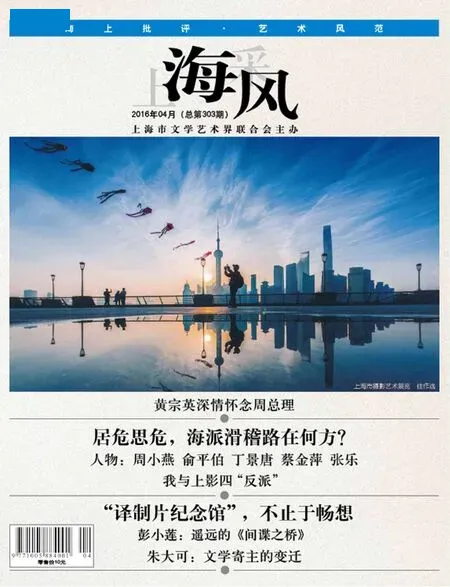鄭孝同:我有一個偉大的父親
文/岐 山
?
鄭孝同:我有一個偉大的父親
文/岐山

鄭午昌(左)鄭孝同(右)
2016年初,一場題為“世界和平感化力——鄭午昌、鄭孝同、鄭人剛精品書畫聯合國特展”的畫展在位于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外交官展廳舉行,聯合國副秘書長南威哲在他的賀信中說,“三代美術家展現的是跨越整整一個世紀的杰作”,稱“鄭午昌是一位與齊白石、徐悲鴻一個級別的偉大藝術家”,認為鄭午昌對中國美術史的書寫所作出的貢獻不可估量。誰都無法否認這份評價的分量。
展覽結束后不久,在一次沙龍活動上,我見到了剛從紐約歸來的鄭孝同,穿著一件黑色的對襟中裝,灰白的頭發自然地向后梳起,行止間流露出的儒雅清逸的況味,讓人很容易就想到了他那些清淡雅逸的山水畫作和那句“吾乃吾自畫,自得其樂,修身養性罷了”的夫子自道。活動開始前的一個小時,我們坐在休息室里這樣那樣地聊了很多,關于父親鄭午昌,關于傳統中國繪畫,也關于作為后輩的他自己。毫不意外地,鄭孝同特別向我提到了南威哲對父親鄭午昌“與齊白石、徐悲鴻一個級別的偉大藝術家”的評語。那種自豪發自肺腑,甚至在他看來,相較齊、徐二位,父親對中國美術史研究所作的貢獻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我有一個偉大的父親”,整個采訪中,這句話被鄭孝同重復了好幾遍。“他是學者型的畫家,是美術理論家,也是美術教育家,他是當年海上畫壇的風云人物。對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我就越來越佩服他。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跟他身上那種強烈的使命感都是分不開的。”
父親的三個“第一”
在百度百科“鄭午昌”詞條之下,可以看到這樣的關鍵句:他和徐志摩、郁達夫一道,都是杭州府學堂“錢塘才子”張相的弟子;擅畫山水,兼畫花卉人物,能融詩、書、畫于一爐,更因其所繪之楊柳與白菜別致有趣,而被畫界好友戲稱為“鄭楊柳”“鄭白菜”;他做過民國時期中華書局美術部的主任,上海美專、杭州國立藝專、新華藝專、蘇州美專等校國畫系教授,劉海粟、吳湖帆、張大千、黃賓虹都是他的畫友,潘君諾、蔣孝游、婁詠芬、丁慶齡、王扆昌、王康樂、尤無曲、陳佩秋都是他的學生;后來他又在上海開辦漢文正楷印局,是漢文正楷活字字模的首創者,被蔡元培譽為“中國文化事業之大貢獻”。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抗戰時期,曾與劉海粟、吳湖帆、俞劍華、李健等書畫家、收藏家一起舉辦了中國歷史書畫展覽會,門券所得,悉數交與上海醫師公會,作為戰時醫藥救濟之用。此后又與梅蘭芳、周信芳、吳湖帆、汪亞塵、范煙橋、楊清磬、丁健行、張旭人、張君謀、汪士沂、陸書臣等20人,結成“甲午同庚千齡會”,相約誓不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解放戰爭時期,他又秘密為解放區印刷廠提供鉛字,掩護被國民黨反動派追捕的革命學生,資助地下黨營救獄中的革命志士。畫內畫外,樁樁件件都頗值一書。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最廣為人知的,無疑還是作為畫家的鄭午昌。
“父親偉大在哪里呢?這樣說吧,我的父親是浙江嵊縣人,1922年來到上海,至1952年去世,整整30年時間里,他做了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對中國美術史做了很大的貢獻,他創造了三個‘第一’。”
鄭孝同口中的第一個“第一”就是鄭午昌于1929年編著出版的《中國畫學全史》,這部作品開了我國畫學通史寫作之先河,被蔡元培先生贊為“中國有畫史以來集大成之巨著”。
據說這部35萬字的煌煌大作是鄭午昌與當時著名書畫家黃賓虹、黃藹農、許征白等往來切磋,探討有得,耗5年精力剛才寫成的,但鄭孝同說“其實不止五年,在很早之前,他還沒有來上海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想法了”。來上海之前,鄭午昌曾經在杭州高義泰綢莊做過一段時間的家庭教師。說是家庭教師,工作的內容其實相當于半個文書。高家是杭城首富之一,家中收藏頗豐,“高家的第三個兒子當時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美術部主任,后來父親到中華書局任職,我猜想就是他引薦的”。那會兒在高家,教書之外,鄭午昌也會相幫著對所藏的字畫進行一些必要的整理。鄭午昌畢業于北大歷史系,歷史和繪畫本來就是他的興趣所在,有事沒事也喜歡去博物館逛逛,在鄭孝同看來,正是青年時代的那么許多的積累,為父親后來畫學全史的寫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1943年中秋,鄭午昌和甲午同庚會同仁的合影
“在《畫學全史》的序言里他說,自己的這本書僅僅是拋磚引玉。他還說,中國的美術史為什么要由外國人來寫呢?中國的美術史理所應當要由中國人來寫。這表現了他的一種社會責任感。”鄭孝同說。南京藝術學院的博士生褚慶立曾在自己以鄭午昌和《中國畫學全史》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中作過比對,雖然在鄭午昌之前,已經有過中國美術史相關的作品問世,但大多只是對日常授課講義的簡單整理,很多都是參考乃至照搬了日本學者的論述,并沒有太多的個人創見。而鄭午昌的這一本“無論從觀點還是體例都是自己的東西”(鄭孝同語)。直到現在,《中國畫學全史》依然是美術專業的經典教材和中國美術史研究的重要工具書,并不斷再版。“1999年出版社推出領導干部的必讀叢書,16本書里就有2本是我父親的,一本是《中國畫學全史》,一本是《中國美術史》。”2009年,東方出版社推出“民國經典學術·中國史系列”叢書,全套11本,《中國畫學全史》也赫然在列。
與此同時,鄭午昌還是海上畫壇卓越的組織者。1929年他與王師子、謝公展、賀天健、陸丹林、孫雪泥等一起創辦“蜜蜂畫社”,編印《蜜蜂畫集》《蜜蜂畫報》及《當代名家畫海》,舉行講座、畫展,畫社先后參加者達百余人,聞名海內外。1931年他又與張聿光、賀天健、孫雪泥、陸丹林、錢瘦鐵、馬公愚、張大千、丁先念、王師子、陳定山、李祖韓、謝公展、汪亞塵、王一亭、黃賓虹、吳湖帆、姜丹書、徐悲鴻等一道組織“中國畫會”,編印《國畫月刊》《現代中國畫集》,畫會會員有三百余人。此外,鄭午昌還參與了“寒之友社”等藝術團體,探討國畫藝術,并與畫友湯定之、符鐵年、謝公展、王師子、謝玉岑(謝逝后由王啟之補)、張大千、陸丹林等9人結為“九社”。
鄭孝同所說的第二個“第一”,正是方才提到的“蜜蜂畫社”。“中國畫壇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蜜蜂畫社的成員。畫社成立時定有章程,里面規定了社員的義務、責任,每年都有任務。我看過一篇由中國畫院的一個朋友寫的文章,說蜜蜂畫社是‘史無前例地’有了章程。在此之前,畫社的主要活動就是聚會喝茶聊天,最多就是搞一些慈善活動。從我父親開始,畫社在學術上有了專門的條款”。就此,創作與研究從美術家的個人活動發展成為有組織的團體活動,某種意義上,這或也可以視作是“中國文人畫向現代美術過渡的一個轉折點”。
而這第三個“第一”,則是1939年,鄭午昌憑借自己的山水畫作品,在當年的紐約藝術博覽會上從來自72個國家的畫家作品中脫穎而出,一舉獲得金獎,為中國畫在國際畫壇贏得了殊榮。
“憑借這三個‘第一’,對中國美術史的發展,父親確實是有功勞的。陳佩秋說他是繼吳昌碩、任伯年之后的海派繪畫的領軍人物,這個說法應該講也是相當精確的。”鄭孝同非常肯定地說,“父親這個人責任心太強了。編書、成立蜜蜂畫社,后來他還組織中西畫家一起討論中國話的未來應該怎么走,他說‘要做一只蜜蜂,飛向中西繪畫的藩籬,采摘其花粉,釀成新時代的佳蜜’。但是他反對美術教育過度西化,對當時學校取消傳統中國畫授課,他是非常反對的。他認為‘國畫寄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極應發揚光大’。還有一句,‘國畫實具締造世界和平的感化力,極易傳播’——這也是我們這次畫展的題目——父親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兄弟七人,只有我將繪畫進行到底
鄭午昌有個齋名叫“鹿胎仙館”,他的太太朱顏則有一個號叫“鹿胎仙侍”,從中足以窺見夫婦二人的感情。鄭孝同藏有父親所書的一副對聯,上聯“煎茶、煮飯、掃地、洗衣,自家有力自家做”,下聯“學佛、讀書、養花、作畫,終日如癡終日忙”。“這副對聯是我母親給我父親出的一道題目,讓他把平日生活中的事寫成一副對聯。父親于是就寫了這一副。上聯是我母親平日做的事情;下聯是我父親平日里做的事情。”
鄭孝同是這對恩愛夫妻的第五個孩子。“我們家有七個男孩子,喜歡畫畫的有三個,我二哥,我,還有我七弟。后來二哥去學外語,七弟去搞建筑了,從事繪畫相關工作的只有我一個。”事實上,他的二哥和七弟也都不是泛泛之輩。二哥鄭孝通是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在英語界頗負盛名,曾經風靡全國的、被英語學習者們奉為經典的《新概念英語閱讀手冊》《英語學習三點法》就是由他編寫出版的;七弟鄭孝正則是同濟大學建筑系的教授,矗立于上海外灘的人民英雄紀念塔便是由他設計的——從父親到兒子,這是一個典型的學者之家。
鄭孝同打小就對繪畫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我是不記得了,我母親跟我說,那時候我還很小,一看到父親拿毛筆寫字,就撲上去搶。于是父親干脆在地板上鋪了一條草席,攤上一大張宣紙,讓我一個人拿著毛筆涂,涂得身上臉上全是。他對母親說,就讓他過把癮吧,讓他玩。他還說,這一個將來可能要畫畫的。”就是從這一刻起,鄭午昌動了要教兒子畫畫的念頭也未可知。鄭孝同稍微長大一點,就開始立在畫案邊,為父親研磨,看父親作畫了。
許多年之后的有一天,鄭孝同的一個收藏家朋友找到他,說自己看到一幅署名為鄭午昌的畫,畫的是一只公雞,他不確定是不是真跡,想聽聽鄭孝同的意見。鄭孝同問他,這幅畫是不是叫《東方紅》。朋友說是。鄭孝同一拍大腿:這就對了!
那是1950年,鄭午昌全家剛從延安東路搬家到南京東路。“喬遷新居,母親對父親說,你畫幅畫吧。父親略加思索便畫了起來,邊畫邊向我解釋,這是雞冠,這是雞脖子上的錦毛,尾巴毛要畫得長,要畫得有飄動的感覺……而且父親畫的這只雞是正面的。我還記得父親跟我說,畫雞要從側面開始畫,正面的雞是很難畫的。因為父親的這句話,我后來一直在找有沒有人是正面畫雞的。尋來尋去,確實很少看見。可以說幾乎沒有。”
一直有心致力于弘揚國畫藝術的鄭午昌此時正在積極參與創建“新國畫研究會”。遵照“新國畫”的精神,鄭午昌在題詩時有意效仿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寫法,文辭相當淺白通俗:“公雞公雞聲何洪,喔喔幾聲動晚風。聲隨風,吹大地,起來起來莫再睡,快來工作振精神,一日之計在于晨,及時不作應自悔,社會豈容偷懶人,偷懶人比如行尸和走肉,自思何以對民族。聞雞聲倘能即起,向前事工農,懶人便可變英雄。”他一邊寫一邊問一旁的鄭孝同認不認得,讀不讀得出,說你能讀出,那工農兵們也一定能夠理解。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唱《東方紅》的歌,我就說,那名字就叫‘東方紅’好了。父親說對對,就叫‘東方紅’。于是他就又在這首詩的下面,用隸書寫了‘東方紅’三個字。所以我對這幅畫,印象深刻得不得了。”
另一幅讓鄭孝同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大西南進軍圖》,是父親和他的好友王個簃、戈湘嵐一道合作完成的。創作地點也是在南京西路的家中。因為尺幅很大,畫紙只得鋪在地板上。這幅作品參加了全國的美展,并以拉出折頁的方式,刊登在當年的《人民畫報》上。據說作品被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鄭孝同后來還專門去上海圖書館借了那期《人民畫報》出來臨摹。
還有《志愿軍雪夜進軍圖》。畫面上的志愿軍戰士手握機關槍站在墜毀的敵軍飛機機翼上。“小朋友對飛機大炮都是很感興趣的。我父親就指著畫上的深深淺淺的黑點說,顏色淺的點是灰塵。然后他說我再點幾點深的給你看,這是彈孔。還有作為畫面背景的農民的房屋,那些籬笆的畫法,父親都一邊畫一邊講給我聽。這些細節我一直記得很清楚。”
不是姐姐的姐姐,不是老師的老師
1952年,鄭午昌因為突發腦溢血不幸辭世,那一年,鄭孝同10歲。除卻上文提到的零星記憶,他對父親的了解,更多還是來源于母親的追憶和旁人的講述,以及長大之后對父親畫作的臨摹和史料的閱讀。其中,鄭午昌當年在杭州國立藝專的學生,年長鄭孝同二十余歲的陳佩秋,成了溝通鄭孝同與父親鄭午昌的最重要的一座橋梁。

鄭午昌在畫室作畫
“有些事情我自己其實已經不記得了,是陳佩秋告訴我的,我叫她姐姐,她是我不是老師的老師,不是親戚的親戚。她說你父親最喜歡你,上課的時候還把你帶過來,我們下課之后也都會跟你玩。那時候我大概四五歲吧。后來我父親過世,陳佩秋把母親接到自己家里贍養,我因為要讀書,還是留在嘉定錢門塘。但是每到寒暑假,我都會去陳佩秋家里住上幾天。他們的畫都攤在桌子上,隨時都可以站在邊上看。也說過要拜她做老師,但她說你不要拜師了,畫拿來我給你看就是了。”后來,鄭孝同到陸儼少藝術院當院長,“接觸一些陸儼少的東西,我的畫上也表現了一些出來”,陳佩秋看了之后對他說還是要學宋元,說陸儼少也畫得很好,但是不適合你去學,你直接學宋元的,學你父親的。鄭孝同將陳佩秋視作父親之后第二個最崇拜的人,因為她,“我這根斷掉的風箏線又接了上去”。

鄭午昌作品 古岸垂柳(二件)立軸 (1947年)
在鄭孝同收藏的父親遺作中,有一幅題為《疊嶂清秋圖》的作品特別有意思,那是鄭午昌與陳佩秋師生“合作”的作品。1982年,因為鄭午昌遺作展的需要,鄭孝同拿出了這幅父親生前的未竟之作請陳佩秋補筆。陳佩秋在畫作上題的款識,對此事來龍去脈有過清晰的記述:“此為鄭午昌先生晚歲所作,始寫右側半幅后即不幸逝世,今秋同門丁慶麟、婁詠芬、張宇澄諸學長多方斡旋籌得重金,在上海美術館為先生舉辦書畫遺作展。……此圖為孝同所藏,因以出示,盼余補成。囊昔先生在西湖國立藝校執教,余多次臨撫先生范本,皆未得其神理,忽已三十五年有余,展圖猶聆師教,不覺信手撫之,勉成左半幅,而右半幅山徑、雜樹、人物先生及敷色者亦代潤飾,想先生豁達大度,必不至有所怪罪也。壬戌九月佩秋記。” 一幅作品,前后隔了三十余年,終由師生二人合作完成,這無疑是一段畫壇的佳話。
“我父親主張畫畫要‘清厚’,他說清厚比渾厚更難。”和父親一樣,在筆墨趣味上,鄭孝同始終是偏傳統一路的。在他看來,古典的技法,民族的精神,這是中國畫最重要的核心。有評論家用“清、淡、雅、逸”來形容鄭孝同的作品。而這種對“清、淡、雅、逸”的追求,在鄭孝同看來,歸根到底其實就是一個“靜”字——清是清靜,淡是淡靜,雅是雅靜,逸是逸靜。“石濤就有一幅畫,畫到至處,不敢題句。為什么不敢題句?因為畫得太靜了,字寫上去要驚醒它的。太靜了會不會就沒有畫畫的激情了呢?我覺得不是的,這種靜恰恰就是一種創作的推動力,是那種內在的張力與爆發力,是澎湃的激情的最高點——而這個靜,恰恰就是我們在當下的創作里最最缺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