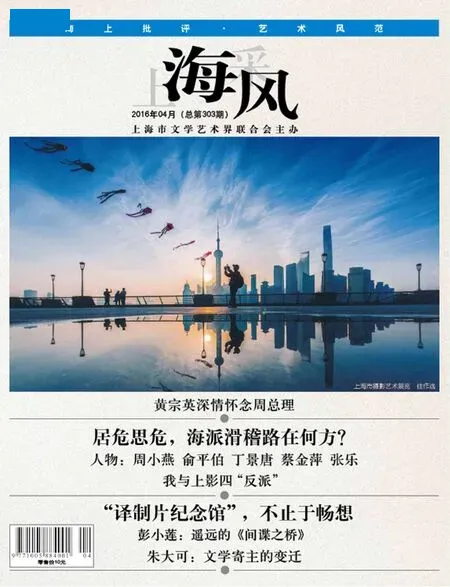互為鏡像的普拉東諾夫與卡夫卡
文/張 閎
?
互為鏡像的普拉東諾夫與卡夫卡
文/張閎

張閎
同濟(jì)大學(xué)文化批評(píng)研究所教授,批評(píng)家
安德烈·普拉東諾夫是弗蘭茨·卡夫卡在蘇俄的鏡像。這兩個(gè)人的世界有著整體上的相似性——1910年代的奧匈帝國(guó)與1920年代的蘇維埃俄國(guó);一個(gè)陰霾密布,一個(gè)赤日炎炎。因此,當(dāng)我們閱讀其中一位的時(shí)候,可以把另一位看作一個(gè)反面的鏡像。
當(dāng)K(卡夫卡小說(shuō)《城堡》中的主人公)以土地測(cè)量員的身份來(lái)到城堡時(shí),已近午夜時(shí)分。K以其自身的昏聵和不確定性,來(lái)丈量午夜的大地,這本身就是一樁荒誕的事情。而無(wú)產(chǎn)者沃謝夫(普拉東諾夫小說(shuō)《基坑》中的主人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沃謝夫從來(lái)不曾有過(guò)任何昏昧的時(shí)刻,相反,他幾乎一直是一個(gè)清醒的人。由于他過(guò)分執(zhí)著于思考,以致耽擱了行動(dòng),并因工作懈怠的理由而被解除了工作的權(quán)利。他對(duì)自己說(shuō):“人沒(méi)有思想,行動(dòng)也就失去了意義!”在沃謝夫看來(lái),人一旦失去了對(duì)真理性的追求,生命也就失去了意義。但工會(huì)的工作人員卻不這么想。他們認(rèn)為,幸福產(chǎn)生于唯物主義,而不是胡思亂想。蘇維埃需要是行動(dòng)。工人階級(jí)只需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一下頭腦,然后去行動(dòng)。“要是我們大家一下子都去思考問(wèn)題,那誰(shuí)去行動(dòng)?”如此一來(lái),共產(chǎn)主義就無(wú)法實(shí)現(xiàn)了。
沃謝夫是蘇維埃的哈姆萊特,生存的意義問(wèn)題一直困擾著他。“一切都馴服于生存的規(guī)律,唯獨(dú)沃謝夫與眾不同,緘默不語(yǔ)。”他不是一個(gè)“僅靠面包而活著”的人。可是,蘇維埃的正午,烈日灼人,饑餓和炎熱讓沃謝夫陷入肉體的萎頓,也讓他的理性躑躅在迷惘的邊緣。甚至列寧也發(fā)現(xiàn)了這里所存在的悖論。他在《偉大的創(chuàng)舉》中寫(xiě)道:“饑餓,這就是原因所在。為了消滅饑餓現(xiàn)象,必須提高農(nóng)業(yè)、運(yùn)輸業(yè)和工業(yè)的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結(jié)果就成了這樣一個(gè)循環(huán):要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就得消除饑餓;而要消除饑餓,又得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列寧:《列寧論勞動(dòng)》,第413頁(yè),工人出版社,1956年。)列寧在另一處引用《真理報(bào)》關(guān)于“共產(chǎn)主義星期六義務(wù)勞動(dòng)”的報(bào)道稱(chēng):“共產(chǎn)黨員為保衛(wèi)革命果實(shí),不應(yīng)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應(yīng)該是無(wú)報(bào)酬的。”(《列寧論勞動(dòng)》,第401頁(yè)。)
事實(shí)上,沃謝夫已經(jīng)進(jìn)入了K想進(jìn)入而不得的那個(gè)城堡。但那里就好像愛(ài)麗絲所進(jìn)入的鏡中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有著反向的規(guī)則。普拉東諾夫的世界是對(duì)卡夫卡的世界的具體實(shí)現(xiàn),它是K想要進(jìn)入城堡的真相。如果說(shuō),卡夫卡描述了一個(gè)向上矗立的城堡,而普拉東諾夫則描述了一個(gè)向下延伸的基坑。任何一個(gè)高聳在地面上的建筑,都需要一個(gè)基坑,而且,建筑物越高,基坑就越深。與通天的巴別塔相對(duì)應(yīng)的是深淵般的地獄。但丁曾經(jīng)描述過(guò)這兩個(gè)方面。普拉東諾夫所處的蘇維埃烏托邦世界,它的基坑卻像是一座墓穴。就在人們要建立高聳入云的蘇維埃宮時(shí),普拉東諾夫?qū)⒛抗庾⒁獾剿幕印R驗(yàn)轲囸I和勞累,工人們一個(gè)個(gè)倒斃坑中。這是一個(gè)卡夫卡式的悖論。卡夫卡曾在寓言故事《夢(mèng)》和《在流放地》中,揭示過(guò)這一悖論。
普拉東諾夫的語(yǔ)言完全不同于其同時(shí)代的蘇俄作家。在他筆下的人物說(shuō)著一種奇怪的語(yǔ)言,既不像日常生活語(yǔ)言,又不像官方媒體語(yǔ)言,而是各種各樣日常的、流行的和觀(guān)念化的,以及官方政治文獻(xiàn)上的那種公文式的語(yǔ)言的混合體。那些剛剛獲得了無(wú)產(chǎn)階級(jí)之“階級(jí)意識(shí)”的勞動(dòng)者,苦于找不到自己的語(yǔ)言。意識(shí)萌生的前期階段,理性的燭光搖曳不定,仿佛隨時(shí)會(huì)被激情的狂風(fēng)吹滅。觀(guān)念性的概念和話(huà)語(yǔ)與肉身感受相分離。人物的言說(shuō)如同翻譯機(jī)器,翻譯著意識(shí)形態(tài)機(jī)器生產(chǎn)出來(lái)的話(huà)語(yǔ)。他們結(jié)結(jié)巴巴地使用一種抽象的意識(shí)形態(tài)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自己幼小的階級(jí)觀(guān)念。而他們的身體卻依舊被捆綁在舊的生產(chǎn)工具之上,被沉重的體力勞動(dòng)所桎梏。在缺乏物質(zhì)生產(chǎn)機(jī)器的情況下,工人階級(jí)只能成為觀(guān)念生產(chǎn)機(jī)器的附屬物。
這種與肉身經(jīng)驗(yàn)相分離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元語(yǔ)言”,構(gòu)成了對(duì)言說(shuō)主體自身的否定。話(huà)語(yǔ)從一架意識(shí)形態(tài)語(yǔ)言機(jī)器里生產(chǎn)出來(lái),而這架機(jī)器已然預(yù)先植入到言說(shuō)者(同時(shí)也是勞動(dòng)者)的頭腦當(dāng)中。話(huà)語(yǔ)(符號(hào))是言說(shuō)行為的本質(zhì),同時(shí)也是言說(shuō)者的自我意識(shí)。言說(shuō)者的主體地位喪失,符號(hào)本身既是主體,又是價(jià)值。無(wú)產(chǎn)階級(jí)成為一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代碼,一個(gè)符號(hào)性的存在。它的價(jià)值只在話(huà)語(yǔ)的層面上方得以呈現(xiàn),而具體的勞動(dòng)者反而幽靈化了。
具體的工人自身有明確的肉身感受,但在話(huà)語(yǔ)層面上或者無(wú)法呈現(xiàn),或者以否定的形式呈現(xiàn)。仿佛肌肉與意識(shí)之間、意識(shí)與口唇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巨大鴻溝。在尚未能跨越這道鴻溝之前,勞動(dòng)者的肉身早已筋疲力盡了。于是,死亡——肉身的消亡——接踵而至。即便是死亡,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肉體消亡和意識(shí)死滅,而是話(huà)語(yǔ)的中斷,話(huà)語(yǔ)載體的個(gè)體性的故障。符號(hào)自身的價(jià)值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只是暫時(shí)性的蟄伏,它再尋找新的宿主。
普拉東諾夫才真正稱(chēng)得上是偉大的蘇維埃作家,他使用的是真正的蘇維埃語(yǔ)言,并且,真正呈現(xiàn)出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