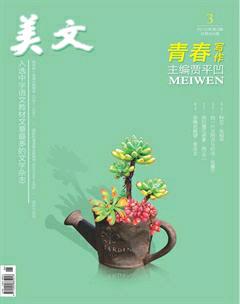文學(xué)應(yīng)守德而為
安黎
有人曾不無擔(dān)憂地問我:伴隨新媒體的興起,文學(xué)會(huì)消亡嗎?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huì)。
貌似不假思索,其實(shí)是思索過的,因此才會(huì)那樣地胸有成竹,脫口而出。我的觀點(diǎn)是,新媒體只是傳播手段的更新,可能涉及文學(xué)載體的變化,但并不觸及文學(xué)的根本。打個(gè)比方說,過去的人坐轎子、騎毛驢,現(xiàn)在的人卻坐飛機(jī)、坐豪華游輪,甚至自己駕車。交通工具的更新?lián)Q代,并不意味著人的變異和消失。人還是人,不是牛,不是羊,不是磚石,亦不是木頭。明代的人和現(xiàn)代的人,也許眼界和思維有所不同,但從生理的意義上,并無太大的區(qū)別。只要人類永恒存在,作為人學(xué)的文學(xué)也會(huì)亦步亦趨地永恒存在。
文學(xué)之于人,共生共存,文學(xué)既是人類精神的衍生物,又是人用以滋養(yǎng)生命慰藉靈魂的營養(yǎng)劑。只要人有表達(dá)之需,有傾訴之欲,有交流之求,文學(xué)就不會(huì)黯然退場;只要人間需要溫暖,需要關(guān)愛,需要正義,文學(xué)就不會(huì)遭遇冷落。
在相當(dāng)程度上,文學(xué)是一種德。它傳播德,勸諭德,培植德,并以其自身的道德,“潤物細(xì)無聲”地引領(lǐng)社會(huì)風(fēng)尚趨于道德。中國的歷史,就像一塊雜色布,有黑有紅,有黃有藍(lán)。其中有數(shù)個(gè)歷史階段,草綠花艷,雁翔鳥飛,令后世的人念念不忘地懷戀與追憶。這些階段的共同特征,就是社會(huì)治理方式頗為人性化,慈眉而善目,心慈而手軟,不濫用刀刃,不殺氣騰騰。一種仁德,猶如和煦之風(fēng),蕩漾于大地,撫慰于人心。德政的實(shí)施,不能說與文學(xué)毫無關(guān)系。因?yàn)椋源呵飼r(shí)期的《戰(zhàn)國策》開始,文學(xué)雖身居草莽,但目光卻總在廟堂的高墻縈繞,幻想著以謀士之角色,行指點(diǎn)與勸諭之功能。這一傳統(tǒng),生生不息,從未斷流。苦口婆心,諄諄而又切切,很有那么一點(diǎn)“誨君不倦”的執(zhí)拗。當(dāng)然,“誨”是萬萬不可以的,準(zhǔn)確地說應(yīng)是“奏”或“勸”,至多是“諫”。“諫”過于直言不諱,充滿了風(fēng)險(xiǎn)。相比之下,“勸”則委婉含蓄許多,旁敲側(cè)擊,拐彎抹角。“勸”什么?自然是勸君要以己之德,施之天下以德治,從而善待天下蕓蕓子民。開明的執(zhí)政者,并不完全拒絕文學(xué)中的合理化建議,以“兼容并蓄”的胸懷,不但采擷采納,而且將其轉(zhuǎn)化為治國之策,從而使一個(gè)時(shí)代,映現(xiàn)出霞光萬道之盛景。
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中,從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從杜甫、白居易到陸游、辛棄疾等等,有相當(dāng)篇幅的文字,從本義上,并不是寫給大眾的。或許,表面上是講給大眾聽,但卻心有旁騖,堅(jiān)信隔墻有耳。尤其是那些政論性的隨筆或小品文,滿篇皆為“形而上”,絲毫不涉及油鹽醬醋之類的“形而下”。
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不論讀者是誰,作家的出發(fā)點(diǎn)不無良善——其意在于修繕房屋而不在于挖房屋的墻角——文學(xué)也許力量有限,但哪怕是一縷微風(fēng),也要吹散霧霾;哪怕是一只蜜蜂,也要釀造甘甜;哪怕是一片樹葉,也要綠化大地……做有德之人,寫有德之文,如此這般,文學(xué)的園林才能萬紫千紅,社會(huì)的河流才能碧波蕩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