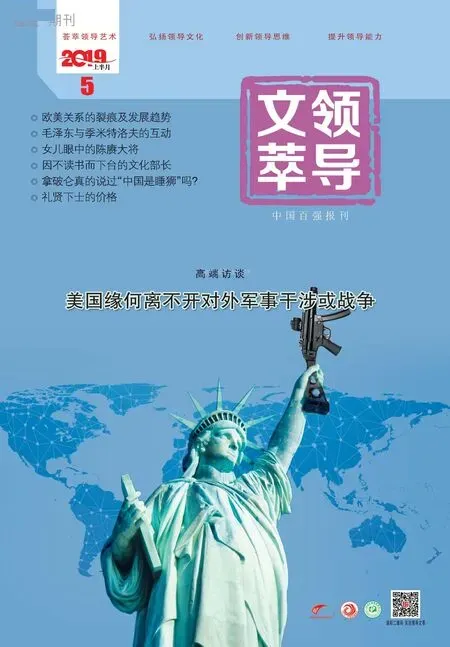1967年,彭德懷怒斥姚文元
沈國凡
一
1967年元旦,鐵窗里的彭德懷如同一只猛虎,被關進了籠子里,沒有了行動自由,更沒有了用武之地。他感到焦慮和不安。
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對手,更談不上拼刺刀,這位戰功赫赫的名將,感到了無力和失望。
他實在感到苦悶和不解,毛主席讓自己出來到大三線去工作,現在怎么又被一些學生莫名其妙地押回北京?這些學生哪來那么大的膽子?毛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現在的情況?
無數的問號在他的腦子里翻騰。他懷疑黨內出了內奸,有壞人在迫害自己。
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狀況,就將發給自己寫檢查的紙筆鋪開,準備直接寫信給毛主席。
彭德懷在信中寫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于27日押解北京。現在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禮!祝你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這封信經層層轉送,最后終于到了周恩來手中,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上宣讀了這封信。
這是彭德懷寫給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報告了自己的處境,充滿了悲憤、痛苦與無奈。彭德懷已預感到自己在這場劫難中很難生還,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禮”這樣的語句。
二
就在彭德懷給毛澤東寫完這封信之后的第三天,一群紅衛兵沖進來,拿出一張《人民日報》讓彭德懷學習,并對他說:“讀后要寫心得!”
紅衛兵走后,彭德懷躺在床上,翻開那張報紙,大標題《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赫然在目。對于周揚這個名字,彭德懷是熟悉的,這個既不管槍,又不管糧,更不管權的人,怎么會一下子變成“兩面派”了呢?他覺得奇怪,便認真地讀起來。讀著讀著他氣憤了,文章中那些殺氣騰騰的話,根本就是以勢壓人,不讓別人說話嘛。這哪還有一點真理可言?
他翻過來看了一下作者的名字,這一看不打緊,他氣得兩眼圓睜,將報紙扔在桌子上,罵道:“又是這個姚文元!”
自從1965年11月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之后,彭德懷便記住了“姚文元”這個名字。發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占有如此大的版面,這姚文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彭德懷在腦海里搜索,怎么也找不到這個人的影子,但他斷定這一定是一個政治暴發戶,一個投機者。
一股怒氣直沖頭頂,他決定向這個姚文元開戰。
幾天之后,那群給他報紙的紅衛兵又來了。他們對彭德懷說:“怎么樣,你對姚文元的文章有何看法?”
彭德懷說:“沒有看法。”
這些紅衛兵一聽,生氣地說:“你真是一個花崗巖腦袋,你同周揚是穿一條褲子的吧?”
彭德懷說:“你們了解個啥?姚文元的文章我讀得不多,但大都是誹謗之詞。我與周揚根本就不熟,但從來也沒聽說他是個反革命的兩面派呀。寫文章最起碼也得實事求是吧!”
這些紅衛兵怒氣沖沖地說:“你到底寫不寫讀報心得?”
彭德懷說:“這個心得我不能寫!”
這些紅衛兵沖上來就要動武,被守衛的士兵攔住了。
彭德懷說:“你們不要強加于人,憲法上早有規定,他姚文元有寫這篇文章的自由,我彭德懷也有不寫這個心得的自由!”紅衛兵被彭德懷說得啞口無言。
過了一會兒,彭德懷說:“我還是決定要寫的,不過不是你們逼我寫的那個心得,而是另外一篇文章。你們給我拿紙來。”
彭德懷鋪開稿紙,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這是他在“文革”歲月里,唯一一封敢于直面事實,向姚文元挑戰的回信:
姚文元同志:
讀了3日《人民日報》《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大作后,紅衛兵同志要我對其中一段表態度,即“自命為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夢想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把我國拉回到資本主義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這樣宣傳有益,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實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不知是因為憤怒還是別的什么原因,寫著寫著,彭德懷握筆的手顫抖起來,額頭上浸出了汗水,太陽穴上暴起青筋。 1967年1月6日,這封信被送到了彭德懷專案組。
專案組的人看了信之后,立刻轉給康生和戚本禹。康生讀后生氣地將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扔,說道:“這個彭德懷,就愛寫信,廬山上寫了信,犯了罪,到現在都還不肯改。”
戚本禹說:“這哪是在寫信,簡直就是在翻案。看來他還沒有認罪,還得讓紅衛兵小將們來批斗他,讓他真正地低頭認罪!” 戚本禹將彭德懷寫信“攻擊”其同類姚文元的“罪行”記在心里,除了發動紅衛兵對彭德懷進行批斗外,在講話中處處將彭德懷作為修正主義的靶子來進行攻擊。
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戚本禹在北京做了長篇講話,這個講話的題目十分奇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建軍綱領》。
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這篇講話。
彭德懷看后有些哭笑不得,覺得這真有點牛頭不對馬嘴: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怎么一下子變成了建軍綱領了?
戚本禹在講話中說:“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支持下,為廬山會議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等人翻案,企圖煽動別人起來同他們一道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
彭德懷坐下來,借著囚室窗子上射進來的光亮,將那張報紙放在眼前,再次細讀起來。
這個戚本禹,他并不認識,戚怎么同那個姚文元一樣的口氣?彭德懷認定這個姓戚的家伙,一定是與姚一伙的政治投機商,是鉆進黨內來的內奸。
彭德懷繼續看下去,在文章中發現了一連串的點名,這些人是: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齊燕銘、夏衍、田漢、鄧拓……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彭德懷認識的,特別是彭真,當時的地位很高,自己到三線去工作,還是他代表毛澤東主席找自己談的話。這樣的人怎么也成了反革命?那個寫了國歌的田漢,怎么也成了壞人?
彭德懷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用筆重重地畫了一道又一道。
順著這些人的名字看下去,彭德懷終于發現了自己的名字,他被點名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了這些“黑幫”的“頭子”。
彭德懷非常氣憤:怎么能這樣不顧事實呢?自己犯了錯誤,卻一下子連累到這么多同志,有的同志他連話都沒有跟他們說過一句。特別是那些文藝界的人,自己從來沒有跟他們打過交道,竟也被自己連累了。
他用筆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畫了一道,畫完之后,將那張報紙扔到地上。
彭德懷躺回床上,用沙啞的喉嚨唱起《國際歌》,粗獷有力的歌聲沖出小小的囚室,久久回旋……
看守的士兵通過門上的小洞,一直關注著彭德懷的一舉一動。根據要求,在《看守日志》上記下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