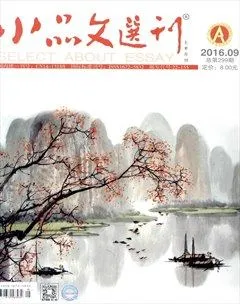河流的死亡
龔小萍
我木然地站在這條點亮過我童年和少年明麗天空的小河邊,曾經清澈的河水已不復存在,魚蝦,水草,河床,岸邊的樹木,以及沿河兩岸的稻田等等,都死于湘北寒冷的霜風中了。
這是一條在我的老家湖南北部的每個村落里都可以見到的小河。多年以前,它們以相似的長相,發源于某一個山洼處,它們的源頭和上游,都只是一泓涓涓的細流,河床與地面相差無幾,淺窄,流量不大。一路蜿蜒之后,它們便有了成了像模像樣的河流,有了長灘處,河面也逐漸變得開闊起來,水流的速度開始減緩,即便還只是小河,也是名副其實了。陽光明媚的日子,微風輕拂,波光粼粼。毫無疑問,它是村落里最美的風景。它也是村落里的血脈,養育著兩岸的莊稼,人群,以及那些活蹦亂跳的牛、豬、羊、狗、雞、鴨等牲畜。
我曾經居住在一個叫花園村的極其普通的村落里,它自北向南,長約十四五里。這條滋養順著花園村的血脈,也就順著村落的走向流向遠方,其流經處,分布著無數淺淺窄窄的河床,除了各種各樣的水草,上面散落著光滑的鵝卵石。進入秋天之后,河水慢慢變淺變清,河面逐漸平靜下來。陽光下,流水如鏡,品類繁多、無以數計的小魚小蝦,在清淺的水流中歡快地游動,看上去,仿佛懸游于鏡子的深處。
小河寬寬窄窄,狹窄的河段,一個大步,就能跨到對岸。窄處之后,便是一處比較幽深的河灣。這些河灣,又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垱。如大垱、彎垱、孫家垱。小時候,聽我奶奶說,河灣的兩岸,過去全是密密麻麻的細葉楊和木梓樹,細葉楊是農家冬天烤火的主要柴料,而木梓樹乳白色的果實,又是村民們食用油的主要原料。木梓油清香,見油,少少的一點點,菜肴便顯得油汪汪。但這些樹,最終在大煉鋼鐵時期被砍伐下來作為燃料化成了灰燼。20世紀70年代初我記事起,我就沒有再見過這些細葉楊和木梓樹的蹤影。不過我還算幸運,趕上了小河最后的美好時光,我見證了它的清澈、深邃和魚蝦的繁盛。那時,它的深水里還隱藏著能夠觸動父親漁具的大魚,甚至,我還見到了數量不菲的烏龜和水魚趴在岸邊的水草上曬太陽的情形。
在時間之上,小河發生了難以察覺卻又不可逆轉的改變。水流量逐年在減小,河岸越來越低,河床卻在不斷抬升,那些鵝卵石開始被淤泥掩埋,河床上長出了奇異的雜草。小河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土坯房,梁柱崩斷,四壁開裂,搖搖欲墜。它已經病入膏肓了。這樣的結果,最初始于人們發覺不依靠河水也能夠很好地生存,于是,他們不再珍惜河流。人們把各種垃圾收集起來,大包大包地往河里倒,垃圾在河里沉積得越來越多,河面越來越窄,渾濁的河水在里面艱難地流淌。還有一些人家,不斷地把死去的雞、狗、豬、貓等等家禽家畜,往河里丟,河面便被那些使用過的化肥農藥的塑料袋和死亡的牲畜所覆蓋。那根曾經掛在我家鄉村落光潔優美脖頸上項鏈一般的小河,在奄奄一息中,并最終以無聲又悲傷的方式死去。
河流死了,魚蝦,水鳥的家園也就沒了,父親的漁具不得不被束之高閣了,麻繩漁網上暗紅漸漸褪色,露出麻的灰暗。每年殺年豬后,總要留一瓢豬血浸染漁網的習慣,也不再延續。魚簍、罾等竹制的器具,也在歲月的塵埃中霉爛,最終成為母親灶膛里的一把火。
河流死了,倒映在河里的星光明月沒有了,鄉村的詩意棲居也沒有了。沒有水的河床裸露出來,河灘上,到處都是死魚爛蝦。沖天的臭味,伴隨一陣陣熱浪,在村莊周圍流動。成群的蒼蠅,興高采烈地在小河的上空飛涌,腐爛成為了它們集體狂歡的盛宴。裸露的河床上偶爾現出一個慘白的石塊,也仿佛河流的一個腫瘤,鋪陳在這具死亡的河流的尸體上。每看到一次,就會讓人悲傷的心流血一次。
我知道,那是如我父親母親一樣無辜而淳樸的人參與了對小河的謀殺。他們沒有預見這樣的后果,也沒有誰承擔責任。多數的人選擇了離開,年輕人遠走他鄉,有積累的能人,則選擇了將家搬到了縣城或者更大的城市里,過起了他們自認為的城里人的體面生活。而那些如我的父親母親以種地為生的留守者,日子是越過越難以維持生計了。
我在花園村生活了三十來年,我有過無數次與小伙伴們在下河里捉魚的經歷,我知道這條小河的干涸,對于整個村子里的人來說,絕對是一件嚴峻而又悲愴的事情。人們曾經如此小心翼翼地把它當做自己的孩子一般,順從它,呵護它。大家利用每年的農閑時節,以生產隊為單位,聚集在一起,對它進行疏通,人們一糞筐一糞筐地將淤泥從河道上挑上來,散落于冬季閑置的稻田之中,作為來年的肥料。但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這樣的呵護方式,對于自顧不暇的老人和小孩,已經沒有了這個能力去。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他們在異鄉打工的子女,寄錢回家,修建一個或者多個水塔,亦或是幾乎合資從鎮子上接來自來水。這樣一來,小河的死亡,就像村落的日漸凋敝一樣,跟他們的生活毫無關系。
小河的死亡,對我來說,就是家園的崩潰,小河沒了,曾經盛滿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所有歡樂沒有了,小河死了,我就像一個再也找不到自己影子的人一樣,陡然間,變得茫然無措起來。而那些沿著河岸而居的如我一樣的人們,是不是也察覺到了曾經美麗的故鄉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呢?
選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