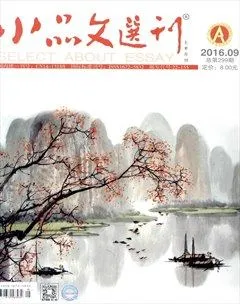一個(gè)人的故鄉(xiāng)地理
黃海
李敬澤說(shuō),祁玉江在散文寫(xiě)作中是個(gè)回憶者。我的理解是,他的散文是在不斷向后撤退的過(guò)程,他要撤退到生命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撤退到他的故鄉(xiāng)和童年,撤退到他內(nèi)心那些不為人所知的秘密。對(duì)于回憶者來(lái)說(shuō)救贖的意義大于拯救。
“回”不光是回憶,回鄉(xiāng),回是回到原處和出發(fā)地,回可能是永遠(yuǎn)無(wú)法想抵達(dá)的地方。他為什么要回到了哪個(gè)永遠(yuǎn)不可能真正回到的地方?這是所有作家要面對(duì)的問(wèn)題,就像我們從哪里來(lái),又要回到哪里去一樣。沒(méi)有人能告訴我,作家就是要回到那個(gè)不可能的故鄉(xiāng)。
祁玉江的“回鄉(xiāng)”之路它的艱難在于那個(gè)深刻存在的靈魂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而地理意義的故鄉(xiāng)已是陌生人的故鄉(xiāng)。從這兩點(diǎn)來(lái)說(shuō),“我”在文字中是個(gè)不歸路的游子,“我”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理解是游離和模糊的,而這種不可靠性多年來(lái)一直支撐著他尋找我真正故鄉(xiāng)的所在,他只能身體前傾地接近這個(gè)虛妄的事實(shí)。
這是心靈的一種無(wú)奈。
當(dāng)知識(shí)分子試圖去修補(bǔ)這種偽飾的鄉(xiāng)土的時(shí)候,祁玉江卻慢下來(lái)拷問(wèn)愚昧和貧窮的責(zé)任,他的散文不掩飾生活在底層的農(nóng)民笨拙而善良的想法,他不掩飾自己的悲傷的情懷。當(dāng)有人還沉浸在田園牧歌式的鄉(xiāng)村不能自拔時(shí),他抒寫(xiě)的是一份自己內(nèi)心的承擔(dān),我能做什么,或者說(shuō)我要做什么。他是一個(gè)敘述者,他看到的大地是親人、樹(shù)木、雜草、黃土、牲畜,他就寫(xiě)到就是親人、樹(shù)木、雜草、黃土、牲畜,他表達(dá)的方式是跟他們拉家常,他的這些美好的情愫深得大地,他構(gòu)建的是一個(gè)人自己的故鄉(xiāng)地理。
他是用心去寫(xiě)的。
他寫(xiě)他父親母親,道出的是心底最真誠(chéng)的話(huà)語(yǔ),一絲不茍地寫(xiě)著他的父親母親被時(shí)代烙下又被時(shí)間褪去的身邊的日常,他不偽飾,不雕飾他對(duì)親人的愛(ài)和懷念,他寫(xiě)故鄉(xiāng)這些勞動(dòng)的親人,是他們構(gòu)成了作者心中最好的風(fēng)景。把中國(guó)農(nóng)耕文明神圣化和神秘化是中國(guó)當(dāng)下鄉(xiāng)土寫(xiě)作的詬病,鄉(xiāng)村知道分子把自己偽裝成農(nóng)民哲學(xué)家招搖過(guò)市。祁玉江卻成了這個(gè)時(shí)代俯身下去面朝黃土的最后一個(gè)“農(nóng)民”,只不過(guò)他手中的農(nóng)具已經(jīng)換成了農(nóng)耕機(jī)械。
但無(wú)論農(nóng)具如何變化,在他的村莊,從未改變的是土地。只要土地和親人還在,他的故鄉(xiāng)從未消失。這個(gè)故鄉(xiāng)的意義是他自己心靈的,他切片一樣剝落下來(lái),擲地有聲。他像中國(guó)眾多的農(nóng)民一樣是有根的,這個(gè)根一下子就扎下去,很深。從這個(gè)意義來(lái)講,祁玉江的寫(xiě)作是向下的過(guò)程,他不是站在散文嚴(yán)格控制的自由中,他很多文字伸展出來(lái)的姿態(tài)是“有話(huà)要說(shuō)”(李敬澤語(yǔ)),他是帶著疑問(wèn)而來(lái)———是為什么而為之。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似是而非的面孔是人文慣用的方式,祁玉江不靠這些手段“征服”讀者,因?yàn)樗淖x者準(zhǔn)備的是一顆堅(jiān)強(qiáng)而善良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