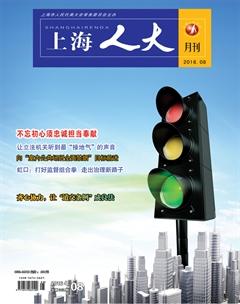從農民無證收購玉米被判刑說開去
陳嘯
近日,內蒙古一農民王力軍在未經糧食部門許可及工商機關核準的情況下,從周邊農戶手中收購玉米并陸續賣給國有糧食儲備倉庫,從中牟取差價,被當地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退繳非法所得6000元,并處罰金20000元。此事引起了網友熱議。
許多網友認為當地公檢法機關有些矯枉過正,理由一是王力軍平均每斤收購價0.94元,出售給國有糧倉的價格為1.09元,總共收購玉米40余萬公斤,扣除成本獲利僅6000元,起早摸黑賺的是辛苦錢,數額以及社會危害并不如判決書所認定的那么大;二是農民愿意把玉米賣給收購商是因為天氣寒冷且運輸比較麻煩,收購商上門收購其實是方便了農民;三是無證收購者非常多,情節比其嚴重的可能也不少,為什么偏偏就王力軍被判刑。
對照法律條款,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了非法經營罪的定義和量刑,“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其適用的是該條第四款“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而王力軍此次違反的國家規定,是指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該條例規定:申請從事小麥、稻谷、玉米、雜糧等糧食收購活動,應當向糧食行政管理部門提交書面申請,并提供資金、倉儲設施、質量檢驗和保管能力的材料證明。此外,從事糧食銷售、存儲、運輸等經營活動,還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王力軍并不具備以上資質,且其承認事先知道需要有關部門核準,從法律角度來講,該行為違法顯而易見。
輿論爭議的焦點在于是否構成犯罪,即是否構成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所規定“擾亂市場秩序且情節嚴重”的情形,如果構成,則罪名成立;如果不構成,則應該根據國務院糧食流通管理條例給予行政處罰。筆者不是法律問題專家,從一個門外漢的角度來考慮,以王力軍的非法經營行為來認定其擾亂市場秩序且情節嚴重、構成犯罪,似有些過于嚴厲。原因在于,一是從其收購的數量,以及收售的價格來看,似乎無法看出存在足以擾亂市場秩序的情況;從經營的金額來看,是否構成情節嚴重則要依照刑法的有關司法解釋,但相較于國家龐大的玉米收儲量,顯然只是滄海一粟。二是從判決本身來看,法院所依據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款是兜底條款,王力軍的行為并未在法條及其司法解釋中被明確列為構成“非法經營罪”,法院依照該條款定罪,即認定其“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但同時又給予“判一緩二”的輕判,從法理上來講,似乎又有些矛盾。
類似事件并非孤例。如2014年,河南大學生閆嘯天與其朋友王亞軍因掏了兩個鳥窩,捉幼鳥12只并販賣(該幼鳥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隼),被認定為非法獵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均被判處了有期徒刑10年。當時網絡輿論也是一片熱議,認為司法部門矯枉過正。事實上,事后有關部門公布的調查情況顯示,盡管庭審時此二人表示不知道捕捉的鳥類為國家保護動物,但在被公安機關詢問時二人承認知道捕捉的鳥類為保護動物,只是不知道捕捉并販賣的后果如此嚴重,這與二人積極販賣幼鳥牟利的行為相互驗證。
這些事件背后,筆者認為,至少明顯反映出了以下幾類情況。一是部分公民的守法意識確有待提高,尤其在通過一定的手段謀取經濟利益時,對于一些看似無關緊要卻又涉及違法的“小事”,心存僥幸。二是部分媒體在發布網絡新聞時,有時存在為博人眼球而斷章取義的情況,使用的標題可能不夠客觀、不夠準確,容易誤導受眾。三是部分單位面對網絡輿論反應滯后,即便是合理合法的司法執法行為,也可能因為未能及時公布客觀情況而陷入被動。這些都值得反思。
說到底,公眾期待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利益多元化現象,公眾越來越厭惡社會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現象,因此立法者和執法司法者更容易處在公眾的關注之中。筆者認為,這既是對社會治理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尤其對于人大而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需要與時俱進的眼光,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部分法律規定,使之更能適應人民的期待和時代的變化。